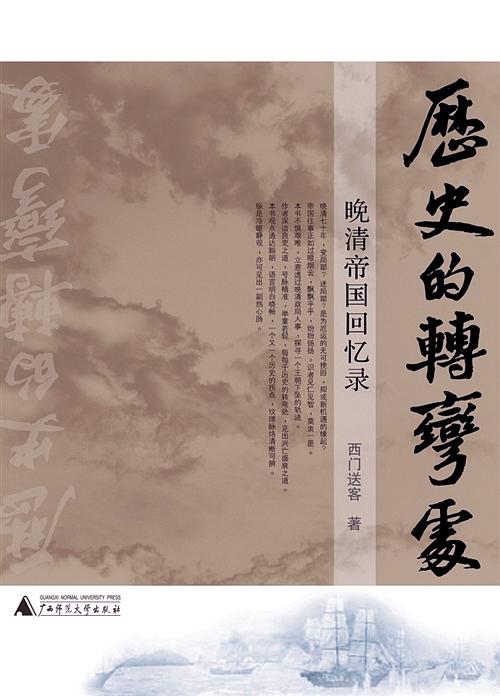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那时内部已有许多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即所谓“灰皮书”,我对这些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的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员写的《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五十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份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张显出张力,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选》,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选》我早就通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假。
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裔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极左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留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单位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聍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1978年后,除去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我的研究的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六十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篡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就笔者而言,本文集所收的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 “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个体生命和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是为序。
转自高华博客。版权归作者,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2。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news。ifeng。/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15_7316_1475326_5。shtml
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