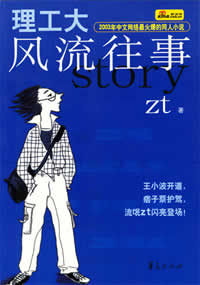大风秦楚-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一两次,因此和虞丘台打过照面。高渐离一出事,虞丘台就销声匿迹了。秦王政一直在追捕他,现在他出现在这里,这里面充满了多少变数?又有多少隐密?再者,北门晨风也有点猜度到容悯的身份,就怕自己一开口,露出破绽,惹出许多不便来,所以他正想敷衍。
“渴死了!”在堂前依案席坐下的洗心玉恰巧这时叫了起来,“黄师伯,有没有熬制好的浆饮?”
“有啊。”黄公虔正想吩咐佣妇,齐云马上说:“我来。”就走进了内室。不一会儿,就用一式金银镶嵌的堞盘和青瓷杯盛来(米巨)(米女),枣粳,糖扶于(米页)等甜点和浆饮。这时容悯和黄公虔一起进入内室。辛琪说:“黄师伯是容悯的老师呢。”
“喂,飘零子,你怎会认识黄师伯?”苦须归宾仍感到奇怪。
“苦须,你口干不干啊?喝点浆饮。”洗心玉立即打断了她的话。
北门晨风就明白,这洗心玉冰雪般聪明,她在为他掩饰。
说话间,容悯随着黄公虔出来了。
“这浆饮熬制得好,怎么配制的?”洗心玉喝出了好浆饮,欢喜得很,问走出来的黄公虔。
“看看,这丫头,就是鬼,”黄公虔指着她,对北门晨风讲,“喝出来了。”
“这浆饮好么?”苦须归宾不信,马上喝了一大口,她没喝出来。
北门晨风也没喝出来,只感到清爽不腻略甜。
还是容悯执起青釉瓷杯来(这种瓷杯在当时,不是一般人家用得起的),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小小地呷了一口,品味了一会,才说:“是不错,”她回过头来对洗心玉笑着说,“香气清雅,颜色纯正,滋味淳厚,余味不尽。”
“怎么样?”洗心玉得意洋洋地摇着头,看着北门晨风。
“我不懂浆饮,实在品不出来。”北门晨风老实地说。
“雕龙小技而已。”苦须归宾显然对此不屑。
“不,也算是一件技艺呢。”齐云说。
“何必把心思放在这等浮技末节上?”
“不也是一种情趣吗?人生有时也是需要一点情趣的。”没想到齐云竟说出了这样的话,北门晨风已经完全明白。齐云这人不大有失礼的时候,她说话做事总是那么温文得体。
“要说品浆品酒,”黄公虔叹息道“傅仰三可谓天下一品,只是可惜了。”
“傅仰三是谁?可惜什么?难道不在了?”苦须归宾问。
北门晨风想起了傅仰三的被车裂,便有了一种不忍。他把傅仰三因高渐离一案被牵连一事说了出来,但他不知道这事与虞丘台有关。黄公虔也没想到这事竟会牵涉到傅仰三,且把他害得那样惨,心中对秦王嬴政便生出一层积淀。
“那他是参与了高渐离一案?”洗心玉心地善良。
“怎么可能,他只是一个纯粹的乐师。”这结果也是北门晨风所没想到的。
“那秦王可能不知道吧?”苦须归宾似有不信。
“这不可能,”容悯说,“嬴政这人,是一个极度贪于权势之人。事无巨细,没有不过问的,怎么会不知道?这人表面上宏才大略,骨子里却是眦睚必报,又刚愎自用,甚至滥杀无辜,无所不用其极!”容悯当然对嬴政充满了仇恨,用的言语也很偏激。
“这样一个人怎能天下一统?容姑娘,你这话说得难以叫人置信。”苦须归宾不同意容悯的话。
“对,对,苦须说得对,我也觉得这人很复杂,”黄公虔插入,说,“不能简单一言以蔽之。他既懂帝王之术,也有很好的个人素质。既善于兼听,又崇尚独断,权谋机变,无一不通。工于心计而又不失大气。尤善于经国致事,知人善任,不愧为一代枭雄。但我觉得,这个人又好大喜功、专横跋扈、暴戾残忍、这也是他的天性,和他的生平有关。在他逐鹿中原时,可能会表现得天姿纵武,而一旦横扫六合,天下一统,可能就会得意忘形,无所顾忌。”
“这个人连自己的母亲也放逐,连亲弟弟也杀死,我指的是成蛟。”容悯说。
“是啊,这真太可怕了。”洗心玉不无忧虑地说,“可我们都要做他的臣民呢。”
“我想也未必,”苦须归宾以她的个性——崇拜强者。她认为,干大事业者,不必这样儿女情长,更不必在乎一两条性命……。
“人有善恶之分。”这时,黄公虔说出这样一句话。
“这倒挺有意思,黄老夫子,你是说:‘善恶是做人的标准。’可是这意思?”黄公虔这句话很有点触动北门晨风,所以他发问。
“你不这样认为?”容悯反问道,“‘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只是,仍有一问,秦王显然不是一个良善之辈,他却一统天下,结束了七国纷争,你又如何评价?”
“我仍坚持我所持的观点。”容悯说。
“难道不念苍生吗?”
“我认为,个人是个人,这与天下苍生无关。”洗心玉插了进来。她偏向容悯的观点。
“对,我说的仅仅是针对‘这一个’。”容悯说。
“这却是分不开的。”
“帝业掩饰了残暴,嬴政是韩非的信徒。你知道吗?韩非子在《韩子》中怎么说?他说‘太仁,太不忍人,慈惠’是亡国之道。你听听,不行仁义,要行严刑峻法,再加之以利禄,这把下民引向了哪里?这只会给天下带来更大的灾难!”容悯依然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以一种儒家的姿态。
“这是什么意思?简直是偏见,我不同意!”这时,苦须归宾叫了起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现在是无道无德,秦王才不得不恩威并施。”
“对,苦须说得对!”辛琪也响应道。
“《韩子》里讲严刑峻法,”苦须归宾接着说,“是说帝王之术,是说治国之道。容悯,你曲解了。何况韩非也说‘故明主厉廉耻,招仁义’,韩非子又不是不要仁义。”
“苦须子,你到底想说什么?”齐云插了进来,她的思想非常明晰。
“……”
“那只不过是块遮羞布罢了。”容悯宽和地说,“我只相信孟子的‘仁者无敌’。”
“不,不,”黄公虔想了想说,“这里面好象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别,此善恶非彼善恶也,但又是什么呢?不,不,对,好象在于:存乎于心。”
“说得太好了!”洗心玉惊叹道,“是的,在于有没有良善之心,君王应念及天下苍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我心向善,斯善至矣。再说,一心向善,难道有坏处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即使是顺应天命,也应以善行之。”
“小玉,你倒引经据典起来了,可孔子也说过‘辩者不善’啊!哈哈,不过,你们说的,也很有意思。”北门晨风略有深思般地说。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飘零子,国之荣怀,看样子就系在你一人之身了,你可要掂量着。”齐云似在打趣,却在不着痕迹地支持着容悯。
“怎么会呢?”苦须归宾坚决反驳道,“干大事业者,哪来这等儿女情长?天下汹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岂能象你们这样,太讲良善我是不赞成的,这会使人尽失阳刚之气。一个人没有阳刚之气也就罢了,但一个国家,象我华夏,假如没有了阳刚之气,那是会亡国灭种的!”
“还有这种说法?真有意思,”北门晨风说,“真没这样想过。不过阳刚之气,又是什么样子?是君子之风吗?肯定不是,君子之风实行得久了,就有了阴柔。阳刚之气似乎带有一点暴戾、专横、不计一切后果的尽情泼撒……。对,阳刚就是风暴、就是破坏!假如这就是阳刚,我又想不明白了。——不过”他接着说,“一个国家决不能没有阳刚。但按齐云的说法,我又成了历史罪人。”他宽泛地笑了起来,好象有点无可奈何。
“那你就‘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呀。”齐云又打趣起来。
“但我想,”黄公虔说,“凡事都有个‘度’,北门子说的阳刚之气,就有个‘度’的问题。象伍员,为父复仇,掘墓鞭尸,就做得太过了,以至遭到天谴。”黄公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度’的概念,他认为天地万物,各种政观世俗都应持中,不可去走极端。但他又说,持中和过正也是相对的,关键还是一个‘度’。掌握一个度,对为政者尤为要紧。这一番话,令北门晨风耳目一新。
北门晨风在几微山庄的时候,美丽居正呆在东厢房。早晨,辛琪来叫飘零子,她不好阻止,当看见北门晨风毫不犹豫地走出去之后,又感到伤心。
如今,她真的喜欢上了北门晨风。处在热恋中的人,无法清醒,尤其是如今又出来个洗心玉。北门对她好时,她不会感到满足;北门对她有所疏忽时,她就感到非常嫉恨。她恨死了这里,恨这条伤腿,也恨北门晨风。今天,她并不知道,北门晨风并没有象她想得那么多,再说北门对她的感情也确实没有她对他那么深,北门知道美丽居不认同他,因此在心中也同样没认同她。至于一夜情,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一个女人,就更算不了什么。始乱终弃,对女人是不幸,对男人则是风流韵事,说得不好听些,也许还是一种雄性的张扬和气慨。
一个人呆在东厢房,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她感到了一种残酷:假如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来关心他,在心中来记挂他,那么这个世界再大,对他都是虚空,就全无意义。现在,她就有这个感觉。她感到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感到了这个人世间的冷漠与无情。
正当她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支可天走了进来。
支可天不是不想打美丽居的主意,只是这个女人太厉害,他制服不了。今天,一夜鬼混,起来得晚了,北门晨风已不在。想起北门晨风,心中就有气。
看到支可天不快,美丽居反倒感到快意,恨不得再剌激他一下。但表面上依然不动声色,她故作惊讶状:
“北门子呢?你不和他在一起?”这是明知故问。
支可天是什么人?立即明白了美丽居的恶毒,反唇相讥:“你不也一样!”
“我可是一个动不了的人。”
“哼,好一个动不了的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能想什么?”
“千姿花,你真犯不着自己心里不痛快,拿我出气。”
“哈,”美丽居笑开了,说,“我有什么不痛快?”
“北门于我何干,对你就不同了。”
“你胡说个什么?”
“事实如此!”
支可天这人虽然见识不高,却有着这种人特有的精明。
美丽居见支可天说到点子上了,知他已猜度到自己和北门之间的事,便不好再说。于是和解般地说:“算了,算了,别疯狗似的乱咬人,我可是真心对你。北门不清楚,我难道也不明白?我们毕竟是一起的,总不至于胳膊肘往外拐,向着别人……”
美丽居这样说,自然是为了笼络,不过,这几句话,还中听。
“哦,对了,”支可天突然想起,说,“刚才找北门,转出马厩到庄后,一转两转,来到庄后西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