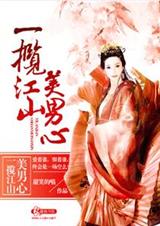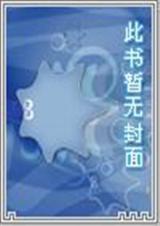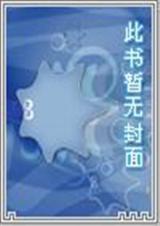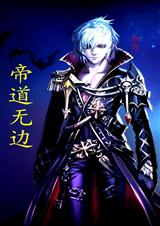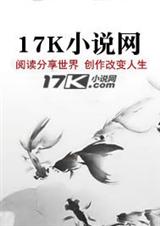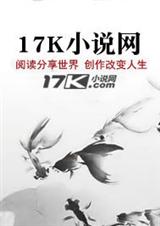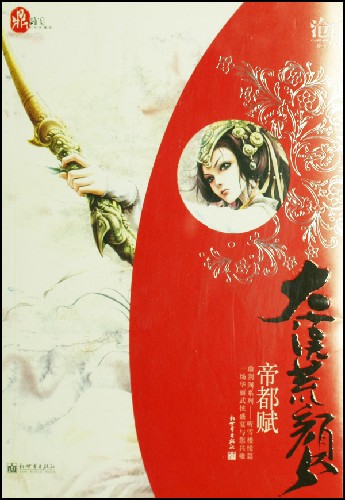清朝的皇帝-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上之役”及郑成功的再评价第五章圣祖(4)
第七首云:
旄头摧灭岂人功?太白新占应月中。
扫荡沉灰元夕火,吹残朔气早春风。
揭空铙鼓催花白,搅海鱼龙避酒红。
从此撑犁辞别号,也应飞盏贺天翁。
“旄头”之解已见前,言世祖之崩由于“天诛”。次句典出《酉阳杂俎》:“禄山反,李白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催,及禄山反,太白蚀月。”顺治十八年三月十五月食,此在前一年颁朔时即已推知,因用作世祖将死的占验。颔联上下句皆言世祖崩于元宵之夜、立春之后(按:是年阴历正月初七,为阳历二月五日,正当立春)。
项联上句,“铙鼓”本为军鼓之一,此处借用击鼓催花之鼓;“揭”训举,“揭空”谓高举,高举铙鼓催发之花,非红而白,乃描写服丧。按:此八首中第二首结句“而今建女无颜色,夺尽燕支插柰花”,兼用乐府《匈奴歌》:“失我燕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及《晋书?成慕杜后传》:“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着服,至是后崩。”两典。“建女”为建州女子之简称,言世祖之崩正为收复失土的良机。此首中的“催花白”,重申其意。
“搅海”句,钱遵王原注引用佛典,极其晦涩难解,总缘迁就韵脚,勉强成对,无甚意义。结句典出《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故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此言无端加天以“撑犁”的别号,殊嫌亵慢;今隐射世祖的“撑犁孤涂单于”既死,则“撑犁”的别号亦同归于消灭,岂不可贺?“天翁”即天公,韵脚所限,不得不用“翁”字。
第八首云:
营巢抱茧叹逶迤,凭仗春风到射陂。
日吉早时论北伐,月明今夕稳南枝。
鞍因足弱攀缘上,檄为头风指顾移。
传语故人开口笑,莫因晼晚叹西垂。
按:前七首皆写世祖之崩,从各种角度看此事,既须凑足七首,又为韵脚束缚,征典将穷,不免竭蹶,故有“搅海鱼龙避酒红”这种入于魔道的涩怪之句;结尾“从此”云云,匪夷所思,已同打油,实由无可奈何,强凑成篇。至于末首,则为起承转合之一结,理应一抒怀抱,一句一义,从容工稳,自是佳作。
首句言频年经营恢复之事。次句谓光复有望,小民生计将苏,“射陂”即射阳湖,跨扬州、淮安两府,《汉书》广陵厉王胥得罪,其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济贫民。三句勉励郑成功及早北伐,于此可知,郑成功入台,非江南遗老所望。四句仍用曹孟德临江赋诗典,非复“绕树三匝,无枝可栖”,意谓此番北伐,必能在江南建立据点。
后半首自抒怀抱,五、六言“老骥伏枥,雄心未已”,上马杀贼,力不从心;但安坐草檄,则不让陈琳,指顾可就。“传语故人”泛指志在恢复之遗老;末句足见信心,不止于事有可为的慰藉之词。
但一年以后就不同了。《后秋兴》之十二,题下自注:“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后,大临无时,啜泣而作。”此为获知永历被俘以后所作。第一首云:
滂沱老泪洒空林,谁和沧浪诉郁森?
总关沉灰论早晚,空于墨穴算晴阴。
皇天哪有重开眼,上帝初无悔乱心。
何限朔南新旧鬼,九嶷山下哭霜砧。
此为穷极呼天之语,但第六首依然寄望于郑成功,诗云:
枕戈坐甲荷元功,一柱孤擎溟渤中。
整旅鱼龙森束伍,誓师鹅鹳肃呼风。
三军缟素天容白,万骑朱殷海气红。
莫笑长江空半壁,苇间还有刺船翁。
末句“苇间”,钱遵王原注引《庄子?渔父篇》:“延缘苇间,刺船而去。”非是,实用《越绝书?越绝荆平王内传》所叙的故事,伍子胥奔吴,至江上得渔者而渡:“子胥食已而去,顾谓渔者曰:‘掩尔壶浆,无令之露。’渔者曰:‘诺。’子胥行,即覆船挟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无泄也。”牧斋以子胥期望郑成功,而以渔者自况,意谓郑成功若能复楚,则己当舍身相助,以成其志。但郑成功是辜负他的老师了。
最后八首作于康熙二年癸卯夏天,题下自注云:“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讹言繁兴,泣血感恸而作,犹冀其言之或诬也。”所谓“讹言”即永历为吴三桂所弑,新朝君臣既讳此事,兼又道远,所以钱牧斋还存着万一之想,“冀其言之或诬”。
江上之役”及郑成功的再评价第五章圣祖(5)
其第四首为郑成功而作,诗云:
自古英雄耻败棋,靴刀引决更何悲?
君臣鳌背仍同国,生死龙胡肯后时。
事去终嗟浮海误,身亡犹叹渡河迟。
关张无命今犹昔,筹笔空烦异代思!
首联言郑成功之死,啮指而亡,无异自尽,故谓“靴刀引决”。颔联据钱遵王注:“陶九成《草莽私乘》:方凤挽陆君实诗:‘祚微方拥幼,势极尚扶颠,鳌背舟中国,龙胡水底天。巩存周已晚,蜀尽汉无年,独有丹心皎,长依海日悬。’”按:陆君实即陆秀夫;此言永历与郑成功先后皆亡。项联“事去终嗟浮海误”,此无定论,足征张苍水卓识。以下用宗泽及关张典,未免溢美。
《后秋兴》另有八首,为柳如是劳军定西侯张名振所部而作:
负戴相携守故林,翻经问织意萧森。
疏疏竹叶晴窗雨,落落梧桐小院阴。
白露园林中夜泪,青灯梵呗六时心。
怜君应是齐梁女,乐府偏能赋藁砧。(其一)
丹黄狼藉鬓丝斜,廿载间关历岁华。
取次铁围同穴道,几曾银浦共仙槎。
吹残别鹤三声角,迸散栖乌半夜笳。
错记穷秋是春尽,漫天离恨搅杨花。(其二)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
破除服珥装罗汉,灭损齑盐饷佽飞。
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矟鼓音违。
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其三)
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
乍传南国长驰日,正是西窗对局时。
漏点稀忧兵势老,灯花落笑子声迟。
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其四)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
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
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
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其五)
归心共折大刀头,别泪阑干誓九秋。
皮骨久判犹贳死,容颜减尽但余愁。
摩天肯悔双黄鹄,贴水翻输两白鸥。
更有闲情搅肠肚,为余轮指算神州。(其六)
此行期奏济河功,架海梯山抵掌中。
自许挥戈回晚日,相将把酒贺春风。
墙头梅蕊疏窗白,瓮面葡萄玉盏红。
一割忍忘归隐约,少阳原是钓鱼翁。(其七)
临分执手语逶迤,白水旌心视此陂。
一别正思红豆子,双栖终向碧梧枝。
盘周四角言难罄,局定中心誓不移。
趣觐两宫应慰劳,纱灯影里泪先垂。(其八)
柳如是曾赴定海犒劳定西侯张名振所部义师,顺便渡莲花洋进香普陀,为罗汉装金,此八首七律为牧斋送别之作。张名振殁后,义师为张苍水所接统,无论士气、训练,皆较郑成功所部为优,所惜军实不足。郑成功倘真为英雄,倾心与张苍水合作,则与清朝划江,乃至划河而治,绝非不可能之事。无奈郑成功为“竖子”;自思明入海,其人即不足为重,而张苍水虽僻处孤岛,二、三门弟子以外,只养了两头小猿,充瞭望警报之任,但一身系朱明的存亡,故以张苍水之死为明亡之年,其时为康熙三年甲辰。我谈康熙,亦即由这年开始。
后记(1)
《清朝的皇帝》谈到德宗、慈禧先后崩逝,即告结束,未谈宣统的原因是:第一;宣统三年之中,溥仪本人无可谈。谈他是另一话题。详近略远,史家通则,拙作虽是闲谈,亦期不悖史例,但那一来,就会大谈民初人物,甚至还要谈日本人与英国人(庄士敦),跑野马会跑得漫无边际,不如就此打住。其次,清朝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变,庆王、袁世凯与端方等相勾结,排去瞿鸿禨、岑春煊时,爱新觉罗皇朝可说已不可救药。宣统三年不过此一皇朝的“弥留”状态,无可谈,亦不必谈了。
谈完了事实,少不得还要发点议论,犹如纪传以后的论赞。兹请先一论清朝亡国的原因,也就是解释何以丁未政变可以看出清朝已无可救药。
这就要先谈一谈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研究历史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就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这交通是广义的,包括水利在内。凡有舟楫之利,易求灌溉之益,苟获驰驿之便,何难平准之济?任何时代的交通水利都能充分反映经济情况,同时亦可看出军事态势的强弱、社会风俗的变迁。
另一个关键是,了解政治上的中心势力,看支配政治的是知识分子、贵族、外戚、宦官,还是藩镇。大致知识分子掌权,常为升平盛世;藩镇跋扈,则每成割据的局面,地方有幸有不幸;贵族干政,应视所结合的势力为何,结合知识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结合外戚或宦官,必致宫廷多故;最坏的是以阉人而操国柄,为苍生之大不幸。
以清朝而言,创业时期自太祖至世祖,大致皆为贵族结合知识分子操持国事。至康熙朝则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且无中外满汉之畛域,故能成其媲美文景之治。雍正、乾隆、嘉庆亦然,但以在上者好尚、能力之不同,因而知识分子所能发生的作用亦有差异。
有清国势之衰,肇端于乾隆末年,渐显于嘉庆中期,而大著于道光一朝。嘉庆仁厚有余,才智不足,以致雍乾两朝久受抑制的贵族渐有干政的倾向。此种倾向至道光朝益见明显,而致命伤则以宣宗资质愚下,近似崇祯,乃发生假知识分子与才足以济其恶的小人相结,排斥正统知识分子的现象。
所谓假知识分子即假道学,此辈历朝皆有,但康熙则敬远之,雍正则驱使之,乾隆则狎侮之,至嘉庆朝虽渐见尊重,而不若道光之信任曹振镛至其人既殁而犹不悟。但道光一朝,真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不甚得意,犹幸假知识分子只能“衡文唯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而不能限制“淹博才华之士”著书讲学,于是至咸丰一朝,人才蔚起。而自文宗以下,政治上对立的派系,不论恭王还是肃顺,皆知重用知识分子,故能戡平大乱,成短暂的同光中兴之治。
至光绪甲申,恭王以次全班出枢,朝局陡变,此后的政治情势渐趋复杂。就整个爱新觉罗而言,光绪甲申以前,支配政治者,不外八旗及知识分子两大中心势力的排宕结合,以知识分子为主,结合八旗势力,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其次以八旗为主,而知识分子尚有相当发言地位,即如道光末年之危,亦尚能挽救。
及至光绪甲申,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逐渐发生了基本上的变化,此即八旗势力转化为贵族、外戚两种势力。假知识分子,亦即徐桐、崇绮一派,昧于外势,实际上可说无知无识的顽固守旧派,为慈禧所扶植,以钳制真正知识分子;而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