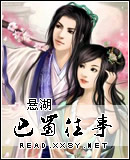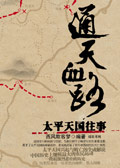两汉往事-第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做过长乐卫尉。但这二人在战场上却是两种表现。
程不识治军严谨,其部队都经过严格的纪律训练,有职责明确的层级指挥系统。部队出战时,总是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戒备状态。其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很慢,但很坚实。凡是他率军作战,前面一定有斥候,左右一定有掩护,一队一队互相呼应,互相照管,安营扎寨很有章法。并且一辈子从来没打过败仗,当然也从来没大胜过。
而李广却完全相反,部队以恩义相结,不重纪律,平日里可以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可到战场如同猛虎下山。部队以骑兵为主,善于进攻,行动迅猛、不拘一格,以机动性代替常规布阵方式。他的战法,与匈奴人对砍时,收效颇丰,经常大胜,即使兵力很少,也能以少制众,反败为胜。
当然,收入和风险是成正比的,李广的这种方式,虽然大胜的机会多,大败的机会也不少,被打成光杆司令甚至被逮的经历也有发生。李广打仗,就好比在赌场赌钱,不是大赢,就是大输。
“李广难封”,其原由和此不无关系。
这个典故让李广对后世的影响很深,也使得他的名声很响。而在汉朝,程不识的位置却排在他之前。原因其实很简单,程不识虽然没有大胜过,但从来没败过。无论处于什么危局,都能顶着压力把队伍从人家的包围圈中带出来。而李广就没这么保险了。
然而这两个人在兵士心目中的位置刚好掉个个。由于程不识治军严,而李广治军松;程不识维持不败,而李广时有大胜,因此,“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这实际上两种领导风格的探讨,至于哪种方式会更好些,就见仁见智了。
个人认为,真要打仗,如果自身实力不强的话,宁可学程不识也不能学李广。
有人曾这样总结过:效程不识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李广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但不管怎么说,两个人都算是出名了,并且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时被提拔为中郎将。
汉匈这一**战结束了。通常情况,下边的套路很简单——谈判,打仗绝不会是闲的没事干找乐子,捣鼓几十万人打群架,要不围绕着经济或政治利益说点事,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那就谈吧。
刘恒认为这一仗自己打的不错,因此多少有点不把稽粥放在眼里的想法,派了个使者过去,围绕一个命题加以阐述:继续和亲,取消“岁贡”。
这么一来稽粥很不满意。打仗前汉朝年年来送礼,自己冲动一把后,刘恒竟然不愿意串亲戚了。因此他很生气,既然不愿意串亲戚,那就连“和亲”都不用再提了。
稽粥一生气就想起了自己的老办法——骚扰。
匈奴的游击战术让汉朝烦不胜烦,最终双方各退一步:继续“岁贡”,但金额要缩减一些。采取菜市场买白菜的方式,经过反复的砍价还价,汉匈双方终于又一次坐回了谈判桌上——继续“和亲”。
达成这个共识后,刘恒又在宗室里找个远亲,扣上“公主”的名号,送去了匈奴。
稽粥这一次也没再较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了这门亲戚。
双方几十万人打了一场恶仗,就这一丁点收获。真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折腾。
至此,稽粥消停了。
四年后,公元前162年,刘恒依然余怒未消,派人给稽粥送了一封信。信得内容很长,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别让那些品质败坏、奸邪无行的小人,为贪图私利,而挑拨两主不睦。
看到这句话时,稽粥咧嘴坏笑了起来,却把中行说的脸给气绿了。
虽然中行说很不忿,但稽粥现在已没心情去和刘恒斗法了,因为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开始考虑退休问题了。
又是两年后,公元前160年,稽粥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当他闭上眼睛后,又一个能折腾的家伙蹦了出来。
不过应该承认,在稽粥最后的四年里,汉匈之间还是比较平静的。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
第十六章初开盛世—第十二节好一根搅屎棍八
事实上,此时的稽粥也清楚该结束这次旅游活动了,你现在要再给他提“消灭汉朝”这个远大理想,他会认为你是在骂他。可稽粥死要面子,让他这么灰头土脸地回家,那是痴心妄想,怎么着也得沾点便宜再走。因此,稽粥催动大军向汉营发起了连番攻击。
战马狂嘶,箭矢如蝗。这是汉匈二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肉搏。
应该说,稽粥在这场战役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因为他带来的清一色的骑兵。
在两军对垒中,骑兵占据优势,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毕竟他们跑的快。打与不打这个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上,想走就走,想来就来,高兴了搞冲锋,憋屈了就在远处观望一阵。
可步兵就没这份优越感了,短跑速度再快,也快不过战马,要让十几万人全部练成飞毛腿好像也不现实。如此一来,步兵一旦被围,通常情况下是原地不动的,摆个阵型,给对方的骑兵当靶子。如果你够硬,够结实,并且箭矢够用,也许能多抵抗一阵,否则会很快玩完。
幸运的是,这次被围在中间的是程不识。如果稽粥晓得程不识随后几十年的看家本领的话,或许早就撤出了战斗。
说白了,程不识这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搞防守,他的军队也一直以步兵为主,行军很慢,但很坚实。凡是他率军作战,左右掩护、前后呼应等等一系列招数都要用上,并且安营扎寨也很有章法。行动起来,全军一起动;扎下营来,敌人冲不动。他和匈奴人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败过,匈奴人从没在他身上讨到便宜。不过我告诉你,他也从来没有大胜过。
他的这种打法的确不可能大胜,因为他最擅长的不是进攻,而是防守。靠防守要想大胜匈奴,简直就没天理了。
但这种打法并非程不识首创。事实上,曾经存活上百年的秦朝铁骑靠的就是这种打法。
秦军之所以擅长防守,是与他们装备分不开的。秦军的武器装备极为厚重,盾戟铠甲都很有分量,总重量要在六七十斤以上。防守起来,盾牌在前,长戟在后,抗击打能力很强;但冲击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毕竟背着如此分量的东西跑起来不会太洒脱。
如此一来,秦军行动相对比较缓慢,但步步为营,极其结实。无论是阵前防御还是攻城略地,都一步一个脚印,走的比较扎实。这个特点,对付东方列国很有用。因为列国都是一城一池的划分地盘,秦军打掉一个就赖着不走,并且还不容易被别人抢去。就这样一步步蚕食,各路诸侯的地盘全部划到了秦国的名下。
有优点自然就有弊端。秦军的这种打法对付匈奴人却收效甚微。因为匈奴人没有城池地域之分,你来了我就走,你走了我重来,你想追到我还不容易,毕竟你们都是负重长跑。想靠赛跑打胜仗,秦军似乎不占优势。
秦军对付匈奴的办法就是防守,甚至不惜投入大本钱修建万里长城。
实际上,早在列国纷争时,秦军的这个短板就暴露无遗。赵武灵王赵雍经“胡服骑射”后,模仿匈奴人练就一支勇猛无比的骑兵,甚至亲自率军出塞,赶的匈奴人四处乱跑,长驱千里。途径秦国地盘时,秦兵在城内鼓掌呐喊,极其艳羡,可就是没勇气出来帮忙。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没那个速度,出来参加长跑只会被别人笑话。
秦军也清楚自己的短板,为降低这个短板带来的危险,不遗余力地研究战术战法、阵营阵型,研究的多了,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
这套理论被程不识继承了下来,为他的亮相开了个好头。
只能说,汉军这次是幸运的,如果董赫没采纳程不识的建议,一窝蜂地冲出来,也许这场战役就是另外一个局面。
眼前的程不识让稽粥很无奈,就在他准备和汉军再耗一阵时,几路探马先后送来三道消息。
陇西周灶军已至安定,上郡卢卿军正由东向西移动,夸张的是还有一支汉军已经绕到了身后。
几条消息让稽粥大吃一惊。
这仗不能再打了,再这样弄下去,能不能顺顺利利回家都成了问题。
稽粥连忙下令各路大军,慢慢撤出战斗,开始向北退缩。
而正面的汉军也没敢太过纠缠,还是摆了一个玄襄阵型,让步兵在前缓缓推进,大有不把稽粥送回老家誓不罢休的味道。
就在匈奴大军撒开腿准备回家时,前边提到的那个魏速终于赶到了。虽然没把包围圈做好,但毕竟和匈奴人碰了面。既然碰了面,不问候一下这些不速之客好像说不过去。
魏速拔出了马刀,可还没顾上说话,身边一个年轻人已率先冲了出去。那啥也别说了,打吧。
年轻人带着一支小分队,一头扎进匈奴大军。这种愣头青行为让魏速大吃一惊。完了完了,魏速的本意是吓唬吓唬稽粥,把他顺顺利利送回老家就行了,可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如此卖力,不管不顾地冲了进去,焉有命在?
然而,令他惊奇地是,年轻人冲进后没一会功夫竟然又打了出来。过分的是,这个家伙跑出来后,扯着嗓子吼了两声,又带人冲了进去。几处几进,竟然浑然无事。这表现真是太扎眼了。
正在撤退的稽粥突然遇到这么个愣头青,一时半会没弄明白,也没考虑对方到底有多少人,撒腿就往老家跑。
稽粥前边跑,汉军在后边追,这让稽粥很抓狂,他做梦也没想到,打了一辈子仗,从没见过汉军里边有这么疯狂的人。自己组织这次旅游活动,一直都顺顺利利的,可临了却以这种方式收场。
不管怎么说,稽粥还是带着大军安全返回了老家。不过那个对着他三番五次搞冲锋的年轻人从此出了名,这个人叫李广。
第十六章初开盛世—第十一节好一根搅屎棍七
汉军陆陆续续抵达了目的地。
前边提到过,刘恒为这一仗,先后派了四支大军北上,却有三个目的地。
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开地图看看。
北地在长安西北,距离很近,这也是稽粥此次南下会选这条路的缘由了。
上郡在北地东北,离长安稍远。但相对北地而言,却如悬其头上的一把利刃;
陇西在北地西南,离长安最远,却像暗插在北地腹部的一把尖刀。
稽粥此次选择了离长安最近的路线——北地。距离近了,但弊端也相应多了。
因为这个地方几乎已深入汉朝腹地,若匈奴以闪电战高歌猛进的话,很快就能赶到长安,刘恒的布局将被搅乱。可一旦陷入僵局,身处北地将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若上郡一军挥师向西,一时三刻就能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