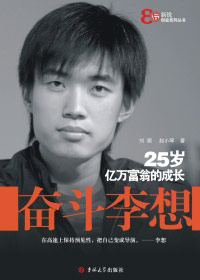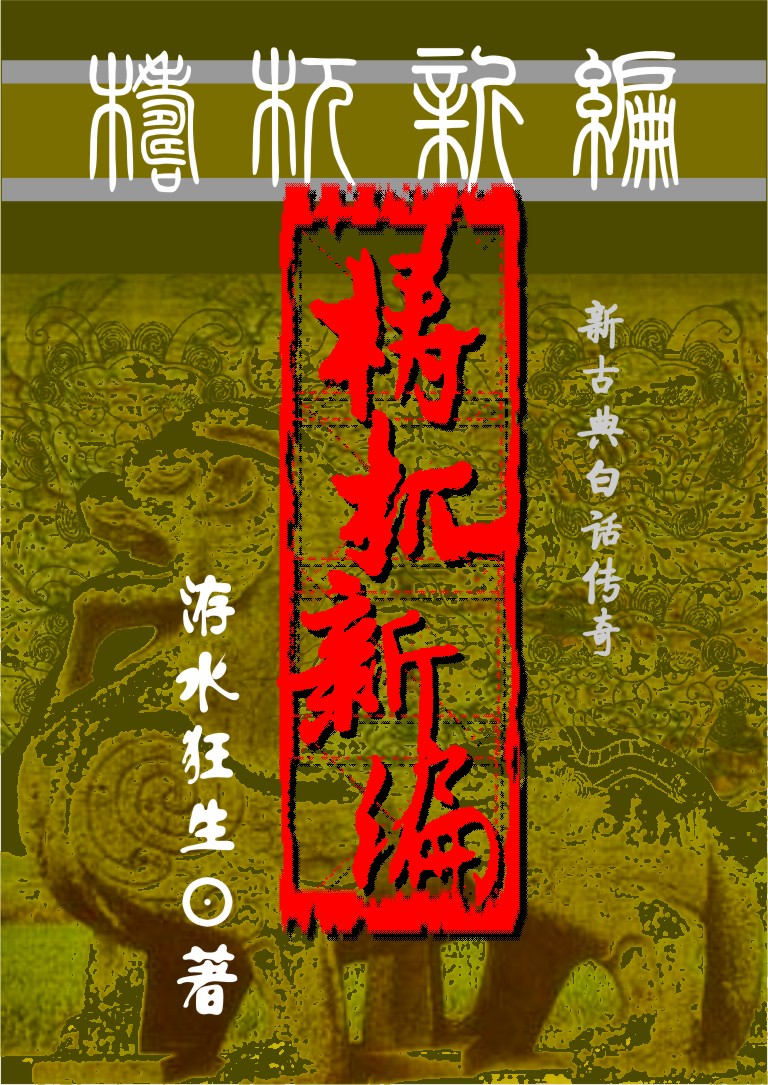陈香梅传奇:她在东西方的奋斗-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灯光照见了长尾巴物,是一只死老鼠。
店主抓起老鼠尾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一只死老鼠嘛。”
毕尔和波贝也跑了进来。香梅指着被垛:“你瞧,还在动。”
毕尔摊开盖被,乖乖,竟有一窝蠕蠕动的小鼠仔!
女孩们又尖叫着双手蒙住眼睛。
店主却像得了宝似地欢喜:“让我来让我来,这窝鼠仔浸到清油里,是治刀伤火烫的灵丹妙药呢。”他将桐油灯挂在板壁的铁钉上,一手提着死鼠,一手托着鼠仔们,欢天喜地出去,嘴里却嘘着:“女人!你们这些女人,坏事的女人!”
静宜皱着眉头说:“要是鼠疫,可就糟了。”
鼠疫倒是没有。第二天起来时,她们只是被虱子跳蚤臭虫咬得遍体鳞伤,就是脸蛋也一片红肿,奇痒无比。揭开脏兮兮的被单,木板上成千上万只虱子在爬动,用手摁去,只只饱满,一摁一滴血。她们太累太困了,让虱蚤臭虫饱餐了一夜。
黎明即上路,不论晴雨。黧黑精瘦的向导阴郁地说:“雨天若不走,住店,不要说我耽搁不起,你们赔得起吗?每天像是逼着你们赶路,不赶行吗?天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天黑地,不要说你们身子骨受不住,遇上强人,小命就没了。”一行人只有默不作声跟着他在雨地里走,雨鞋踩在泥泞的小路上,叽呱叽呱作响,再提不起精神谈李白杜甫李清照了,倒是波贝有时会骂出声:“妈妈的!乞丐不像乞丐,充军不像充军,我厌烦透了!”
吃饭从无定时,饥一顿饱一餐。遇上小饭馆,便涌进去狼吞虎咽一回;有时候走了一天,什么也吃不上。毕尔心细,路过小村,只有农家有甘薯、鸡蛋和蔬菜水果什么的,再贵他也买下来,战时农村粮食奇缺。在路远迢迢饥肠辘辘时,一只茶叶蛋半只石榴便让气息奄奄的小香桃又活转过来,让姊妹们牵扯着又继续前行。
香梅最担心的就是小香桃,生怕有个闪失香桃病倒。没想到,她自己成了第一个病倒的。
起初是头痛发烧,以为是淋雨感冒了,也不吱声,硬撑着跟大家一块走,渐渐地烧得难受,脚下像踩着棉花,毕尔顾不得许多,握住她的手,竟像燃得正旺的炭火般灼人,毕尔说:“停一停,香梅病了。”毕尔家在香港开一爿中药店,这回上路带了万金油、正红花油等药品,一路住宿蚊叮虫咬多亏他的万金油涂抹。这时他又从行装中掏出万金油、正红花油,涂抹在她的太阳穴和人中上。静宜用手试着香梅额上的热度,忧心忡忡地:“怕是重感冒。”向导却斜睨着冷冷甩过一句:“打摆子。要有奎宁才好。”毕尔翻遍行囊,那小瓶奎宁却不见了。不幸言中。这是难民群的流行病,花蚊子怎么偏偏叮香梅呢?高烧过后,不一会浑身发冷,哆嗦着,非得毕尔架着她奔跑不可。向导又不阴不阳甩过一句:“边跑边喊:躲摆子!躲摆子!”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流亡三千里(5)
毕尔言听计从,大声喊着:“躲摆子!躲摆子!”他满心懊恼,那小瓶奎宁在哪丢了呢?
黎明即起,仍要赶路。他们不能没有向导。
陈香梅不知自己是怎样行走的,毕尔一直架着她;静宜和香莲要换他,他坚决摇摇头。江南才子的文弱潇洒的风貌消失殆尽,二十几天的流亡生涯,日晒雨淋、奔走操劳,他又黑又瘦,长发乱蓬蓬,胡子拉碴,因为焦虑目光灼灼,如果腰间别支枪,他怕更像草莽豪杰了。
陈香梅什么也不知道,脚下飘忽忽,灵魂出了窍。那路旁的新鲜的红土黄土草草垒就的孤坟,掩埋的是哪城哪乡的人物?那旷野上水沟里或新鲜或腐烂的尸体,倒毙前夕该有多少冤屈苦痛没有诉说?她很快也要成为异乡异地无家可归的野鬼么?
“我要死了……要死了……”她呻吟着。
“你死不了。有我在。”他咬牙切齿地说。战争和爱情让他脱胎换骨?不再是一个文弱缠绵的少爷?
三天三夜,他们抵达了广州湾。
从澳门到广州湾,他们走了整整半个月。这半个月,却让这七个女子阅尽人间沧桑,历经了人生的苦乐四季,她们的心过早地苍老了。所幸的是,苍老的心田还残存着温柔的一隅,那是爱的清泉在滋润着,无论对体验者还是旁观者。
那是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燠热的空气蒸腾着人和垃圾的异昧,街头巷尾到处挤满了难民,没有一家客店不挂出“客满”的睥子。向导阴沉着脸说:“鬼子离这很近了,明天天一亮从这出发。”说完甩手就走。
毕尔喊道:“等一等!”
向导阴沉地站着:“什么事?”
毕尔急切地说:“是这样的,香梅病得这样重,今天又拉起肚子来了,无论如何,得在这里休整一两天,我父亲有个朋友在这里开爆竹店,我想找找他,要点药。”
向导歪嘴一笑,朝那十位难民涸道:“你们呢?愿意不?”
死一样的沉默。毕竟死生与共地走了十五天。
好一会,一个男子嗫嚅着说:“鬼子就要来了,若是为了一个女子,叫大家……”
波贝忽然学起店主的腔调,嘴里嘘出:“女人!你们这些女人!坏事的女人!”
毕尔愤怒地冲上去,一把揪住波贝的衬衣前胸,吼叫着:“你这自私鬼!你要走你尽管滚!”
静宜掰开他俩,哭声哭调地说:“我们再商量商量吧。要不,租顶轿子抬着她走?”
向导不露声色地说:“那你们再商量吧。明天天亮在这给我个准信。”走了几步,又回头:“这小女子,怕是活不长了。”
毕尔又疯了般冲上去:“你胡说!”
吓得静宜和爱莲慌不迭地拉住他。
他甩开膀子去寻找那家爆竹店,气势汹汹像是上门打劫的匪徒。
他找着了那家店。爆竹店早做了旅店,难民已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店主问清情由后,说他在镇外倒有间爆竹仓库,眼下爆竹倒没有,只是简陋荒僻些,他们愿住多久就住多久。
毕尔领着女子们去郊野的仓库房,波贝垂着头竟也一声不吭地跟着去了。
一间铁皮小屋孤零零地立在荒野中。屋顶墙壁地面都是锈迹斑斑的铁皮,没有窗。在六月烈日炙烤一天后,打开铁皮门,小屋像烧红了的烙铁般灼人,可又不能打开门,要不,荒野中嗡嗡作响的蚊子大军将浩浩荡荡飞进。呆到后半夜,气温降了,铁皮屋回归为冷如铁!他们何罪之有?竟下十八层地狱受火烤冰冻的惩罚?
陈香梅昏昏沉沉,冷热对她都已是麻木了。
“老鼠……老鼠……妈……”那是仰光领事馆,母亲给她们放下蚊帐时说:“呵呵,让我们一块勇敢地面对这一切,也许还有更糟糕的东西呢。”
母亲飘然而至,还是那么漂亮又憔悴,她说:勇敢点,这个家还靠你照顾呢。
“米饼……米饼……二叔婆……”那是二叔婆家的大厅堂,石磨嗡嗡响着,女人们的手揉搓着雪白的米粉,二叔婆指挥若定:“就要开仗了!每家每户至少要做30斤米饼!”
二叔婆铿锵作响地走来,还是那么矮胖却精神抖擞。她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还有几天就是她17岁的生日,可是生命已行到尽头,迷蒙的回忆像筛子,留下的是这样一柔一刚的两个女性,如果她能生还,是否已铸就成一个刚柔相济的女子呢?
也有清醒的时候,她挣扎起来,又要泻肚子,不,是拉痢。四野没有茅坑,静宜、香莲、爱莲扶着她架着她拉着她,到远处的山坡旁解决,夜风中她们因恐怖而颤抖不已,仿佛间似乎在阴曹地府游荡。
回到铁皮小屋,香梅还在颤栗,但这一刻她头脑非常清醒:“哦,就要天亮了。大姐,你们先走吧。我……我是不行了……总梦见妈……想是妈来接我了……”
流亡三千里(6)
静宜搂住她:“不许你胡说!妈只会护佑你好起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毕尔沉静地说:“静宜,我仔细想过了,你们还是先走吧,我陪着香梅,相信我,也相信波贝会照顾你们的,那个向导倒是靠得住的。”
静宜打断他:“不,毕尔,我决不能让你们俩留下,兵荒马乱的,说不定今生今世就见不着了。”说着已泣不成声。
几个妹妹和爱莲已哭成一团,波贝懒懒地坐了起来:“唉,女人们,别哭啦,不走还不成?”
又一个黎明来到了,毕尔悄悄出了铁皮屋,静宜也悄然跟上。
毕尔说:“今天我一定要弄到奎宁,还有治痢疾的药,要不,她会没命的。”
静宜说:“我把钱带上了,只是所剩不多。”
蛋青色的晨曦中,向导和10个难民正等着他们。
向导仍阴沉沉地问:“死了?那我们等一天。”
毕尔真想兜脸给他一拳,静宜拉住他:“请你别说不吉利的话,我妹妹还活着,我们去给她买药。”
向导没心没肝地说:“那我们可等不起,她那病可不是三天两天能好的。”
毕尔拉走静宜:“让他走吧,这种人早叫钱黑了心。”
向导忽地打了声口哨,追上他俩:“等等。黑心钱我不赚。这点钱退给你们。”钱塞到毕尔手中。
毕尔怔住了:“不是议好了嘛,我们中途停歇不走,钱不归坏呀。”
向导说:“我看你是条汉子。愿老天保佑你们。我们得走了。”
为了香梅,毕尔攥紧了手中的钱。
爆竹商就像他经营的爆竹,面如重枣,性情急躁,一点就着,很是慷慨助人。他很快弄到了治痢疾的草药,又几经周折,找到了贩卖药物的黑市商人,市场奇缺奎宁,奎宁成了救命药,价钱也贵得惊人,将静宜手中和向导退的钱全给还不够,静宜轻声说:“我们还有点首饰,得去铁皮屋拿。”
话音未落,毕尔已拿出了自己的戒指交给黑市商人。
静宜拦阻着:“哦,不行,这是你家祖传下来的呵。不行。”
那只分量颇重的方章形金戒上,凸出一个“仁”字。毕尔双手一摊:“不错,是祖传的,你别忘了,我们家世代开中药店,祖传两个字;仁慈。我这样做,有朝一日将无愧地加入仁慈祖先的行列。”
然而,奎宁吃了下去,煎熬的草药汤也灌了下去,香梅的病却一天比一天见沉。毕尔和静宜急得没法,便由热心的爆竹商张罗,请了个乡间巫婆来念咒驱邪。
是一个闷热的黄昏。团团乌云在天际翻滚,荒野中成群的蜻蜓低飞着,突兀而起的是上千只蛤蟆的鼓噪,热气蒸人的铁皮屋弥漫起诡谲神秘。巫婆包着黑头巾,穿着黑大襟衫裤,脸和手都像千年老树皮,寿斑团团块块,没有牙的扁嘴开开阖阖,就像乡间燃着柴火的灶口。她念念有词:“东边的鬼东边去西边的鬼西边去南边的鬼南边去北边的鬼北边去”,霎时她像婆娑起舞的少女般,在香梅的身上腾空跳跃,浑浊的老眼变得炯炯有神,嘴里发出“嘘嘘”的呼啸声。雷声隆隆由远而近,夜幕沉沉笼罩一切,条条豁闪如狂舞的金蛇,读书郎读书妹全给震住了,傻痴痴地跪在锈迹斑斑的铁皮上,动弹不得。
陈香梅仍在昏迷中。
是爆竹商想起了点亮蜡烛,摇曳的烛光中,人们恐惧得痉挛。
大汗淋淋的巫婆和爆竹商走了,巫婆叮咛:“让她躺三天,不准叫她的姓名,也不准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