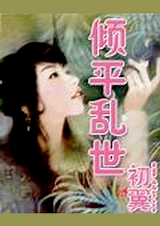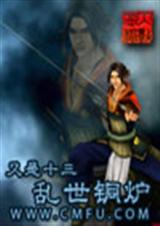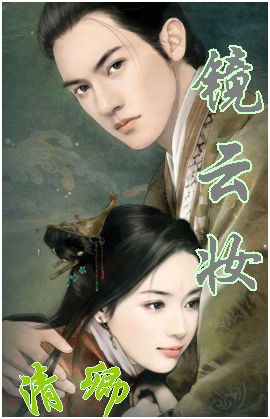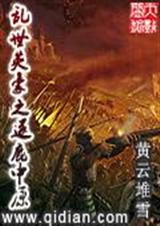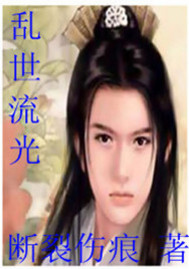��������:�ڶ����й�����Ҵ���-��1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Ǩ��˵������������ʱ��Ӧ���Ľ�����֮ǰ�����ڡ����Ҳ��Ϊ³���䣬ֱ������ʮ�������˵�����Ľ�˽ͨ���������ڻ��������У�Ҳ��������፹�Υ�����ʹ��������Ľ���³�ɻ����ʵ����϶��Dz����������ȥ�͵�Ե�ʡ��ɼ������������������Լ�����Ĩ�ڵ���Ů��˽�飬��������úܡ����������Ľ���ȥ�������һ���������Ů�������̽�ס�
����ֱ��ʮ�����³����ʮ���꣩���Ľ��������ɷ�һ��ص��˾ñ���������ʱ��፹����ţ�����������������幫������һ�������ˣ����Ľ��أ���Ȼ�������������ӣ��������ǹɳ�����������ζ��Ҳʹ������һ��Ů���ˡ������ҡҷ��һɲ�Ƕ����У����Ƕ����ף���λ��������Ҳ�ϲ����ˡ�
�������ǣ��幫����������Ľ��Ľ�ڣ����������˺�����Ҳû���κ��ϰ��������£����˾��鸴�㡣��³�����أ�ȴ�����ڹ���ı���������Щ���Է��
�������ǣ����Ľ����洺ɫ�س����ڻ�����ǰʱ�����߳�ŭ������Ҳ�˲��������˼ҵĵ��̣�һ��������ȥ��û����Լ�����ñ�ӣ�ȴ������Լ���������
�������幫��֪��й��ɱ�����֣�������������³������
�������������£����ò���ͷ������ֻ��ǿ������ͷŭ��ȥ���磬�������ô������ڻس��б����������۶��߹Ƕ�����
������֪���Ľ��Ƿ��ϵ����ֽ�֣�Ҳ���������������˵�������ֻ�����������취�����Լ��ı�һ�´������ѡ��Ͼ���ʮ����ķ����ˣ����������ɰ��Ķ��ӣ���һ���������ɷ���������ġ���������ô˵�����ֱ��ѵĺ�������µģ�Ҳ����ȫ������ĺ��ġ�
��������߱���¼��Ĵ�������ʵ�����ף����ǰ������׳��������˵������ǰ����������������ɱ���������������Ϊ�����ȴ�������Ƶ��ҵ�ͷ�ϡ������ض���Ϊ������ȡ�����������幫��������������ҽ�Ц����
�������Ľ��أ�Ҳ���ǻ��ŶԻ��������Σ�Ҳ���������������幫��ᣬ���ع��������е���³֮�������ʱ��������Ҳ�����ˣ�˵��������ط����벻³���������ҵļҡ�������³ׯ��ֻ������������һ��������Ľ�ס���������أ���Ҳ���Ա߸���һ���й������ⲻ��������
������������ʵ֤��������û�л�ͷ·�����û�м�ǿ������������Ҳ���Գ�Ϊһ��ϰ�ߡ��Ľ���Ϊ³������Тһ�����Ҳ�Ͳ�ס��į����³ׯ�����궬��������������˺��Ľ�����������ᣬֱ��ׯ���������Ϊ������֪��߱��
������ʱ���ɷ�û�ˣ����Ҳû�ˣ����������أ�������֮ǰ������ʮ���꣩��û�ˡ��Ľ�������յ����ģ�������������˼�����Լ�������·�����ʵ����ϣ���Ҳ���ڹ�¥�ϣ�ĬĬ������ҹ�������������Լ��������������ǡ�
�����ڼ�������ʱ�����������һ�������˷������ʣ���һ�Ÿ����أ�
�ڶ�ʮ���¡�����˭��������
��˵֣ׯ��ް�����Ӻ���λΪ�ѹ���ʹ����Ƹ�Σ��������ͻ֮�䡣���ϣ��ι�������ͻ�����λ���˾�ִ���٣�в������ͻ�������ι��������ڣ�Ҫ����ٽ�δ����Ů�������ͻ��ĸ��Ӻ��֮��Ӻ����ǿ������Ӻ����֣�����ף������Դ��ְ֮�����������£����ò���ͷ���������Σ�ֻ�á����Σ������ˡ������ǹ�����������ͻ֮�¡�������ӵ��֮��������ר֣Ȩ��
��������֪�������������ͳƣ����Ǵ��е�###������ר֣ȨҲ��û�˸�������������������������Ҳ���Ҳ��������ӡ�
���������������Ͼ���һ��֮������Ȼ�����϶Լ��������ƴӣ�����ȴʮ���ֵIJ����⡣�����������Լ���ֱ������е�С��������硪������Ƶ�����������ܡ�������������ȫ���������ˣ��Լ���Ϊ������ȴ��Ҫʱʱ����������ƥ�����˼���¡����������������������ֲ��ò������ò��Ĵ������࣬�������̲�ס���еķ�ŭ������Ҫȥ����ǰ������ϰ��ˡ�
����������������Լ��ٷǾ弴�����Լ�����Ҳ�����˼��ٵĶ�Ŀ����������ֻ��һ�����У�������ⷴ�ɡ���ô����������˭��æ�أ�
����һ���������ڵ����磬�������Ʋ��ֵش���Ӻ���ں���ɢ����Ӻ�������Ӷ��ŷ�����Ȼ��̾������æ���е�����Ե�ɡ�������Ȼ������������һֻ���簡��Ӻ��������������˼����æ�����ĵ�������˵�����̸�Ҳ��������Ҳ���������ӵIJ���Ϊ�����ǣ��Ǿ��Dz�Т��Ϊ���ӵIJ���Ϊ�������ѣ��Ǿ��Dz��ҡ����������Ϊ��ֵ�����Σ������齻���ң���һ���߾�ȫ���������ǣ�
�������������Դʿ��У�������̽��������Ǽ��ٵİ����ء�Ӻ��˵��������Ů�����٣�ȴ̸���ϡ������֡�����Ů�����ң���ȫ���ξ����ȣ����dz������ı��⡣��ƽ���ڼ��ᵽ�ɾ��ѹ���ʱ���ܻ���¶������������ɫ��ֻ�Dz�����ǿ��֮����ˡ��������ô��ԣ�֪��Ӻ������һ�ã�����˵����������ܹ�ɱ������ƥ������ְλ�����ˣ�ֻ�Dz�֪�����к���ƣ�
����Ӻ��������������Ϊ�ι��ֻ������������δ�������������ɼ���ǰ��������ο�����Ҿ����������磬���ƿ������
��������������������һЩϸ�ڣ�����������������������ҷ��ģ������¹غ����Ҷ�������������һ��Ҫע�Ᵽ�ܣ�ϸ�����·��ɡ�Ӻ����Ӧ�������������ģ��ұ�֤����һʧ��
����������������ѷ��������벻����Ů����Ȼ��첲�������գ�Ҫ��ͬ������С��������Լ����Һ�Ů�������������Լ������һ��������
������Ȼ��Ҳ��Ӻ�������������������������������ŷ�������˿������
����Ҳ���ǵ�һ�θ����������Ե�ɰɣ������й��㲻��������һ���������ˡ����Ӻ���ؼҺ�������ϣ����ϱ㲻���ֳ�������֮ɫ������
�����ɴ˿ɼ���Ҫ������Ц��ص���Ҳ������ô���ס���Ӻ����������ǰ�ƺ����г���ᶨ���ƣ�����Ҫ�Ը��ıϾ����Լ����������ˣ������ӵĸ��ס��������Լ����Dz���������֮�飬��ʹ��̰ͼ�����˵Ĺ�λ����ɱ����������������˵�ġ������ɣ������λ���ڶ�������Ҳ�����������������Ӽ��ϣ���Ӧ�����з�֮��ġ�������Լ���ʱ����������Ȼ���е���ҡ�
����ϸ�ĵļ��ϣ������ɷ�����쳣����ȻҪ�ʸ�ˮ��ʯ���������Ļ�˵�����ǡ��δ�����ԣ��ȹ���ɫ�����ճ��У���������֮������ͬ�壬����С��檵���֪����δ�������ȹ���ɫ��֤����Ůʵ���Ǻܴϻ۵ģ�������ͬ�塱һ�䣬���dz��飬�����������ȴ���˶�Ӻ���������ջ�Ҳ�����������桰�ڶ�������Ҳ������߽��
������ʱ��Ӻ����δ��ȫ��е������ȥ���ơ���֮������ı��ֻ˵�Լ���������ڶ���������ǰȥ����������������������������ɻ�Ů�������������õ����ڽ���ô���������֮��Ȼ������˯���ʣ���������ɱ���٣�����֮Ү�������ǣ�������Ӻ���İ��ΰ���֮���ס�
���������Ѱ��Ů�ӣ�����Ҫôһ�������ϵ���Ҫô��ͳ�ҹ�ܻ���Ҹ���ȥ�ˡ����Ǽ���֪���������Ļ���������Ӻ���϶���ı����⣬��ȻҲ��������������ı���������ǿ϶���������µIJ�����ʱ����ͺ��ѿ����ˡ����⣬���ɷ����֮�䣬�Լ������뵽��Ӧ�÷�����һ�ߣ�����Ҳ���ò������⣬ֻ�����ȶ�һ����̬��˵������������������ʱƽ���ض�Ӻ��˵��������������Ѿ�֪���ˣ�����������Լ������ҵġ����漦���湷����Ȼ���Ѽ����㣬��ͬ�壬���DZ���һ�������ϵ������ˡ��Ҹ�������ֹ������ȥ����ο�ʾ����ʱ������һ�����ң���������ʱ�����ɡ���
����һ����˵��Ӻ�����´����ż��������������ж��ò���������������ҵĺ����ţ����������ɹ��������������ҵ�һ��Ҳ�����һ�밡�����İɣ�������һ�������㣡
�������ٳ���ǰһ�գ����Ϲ�Ȼ������ҡ�
����һ���Ǹ��ף�һ�����ɷ����Լ�����������ˣ��������ƻ����Ǵٳɣ�����װ�Ų�֪������ı���Լ�����ʧȥ���е�һ�����ˡ���ô��˵���Dz�˵��
��������Ϊ�������СŮ�ӣ������ҿ��������й�־�����һ��ĸŮ�Ի���
����Ů�������������ף�
����ĸ�����ס�
��������������������
����ĸ�������ڷ�
����Ů����Ҳ��
����ĸ��δ��֮Ů�����������ж����Ѽ�֮Ů�����ټ���������������ˣ��������죬�ñ��ڸ��գ�
����Ů���������Ϊ�������ܸ��˷��ӣ���
������ĸ������֮�ԣ������ü������������˴������ѵ�һ��������
�������ǣ�������Ӻ������ı��¶�����ٽ��ƾͼƣ�ɱ����������ӭ�ѹ���λ��
�����������˸��߳����ڲ̹���������ʧ��ֻ��Ӻ�����²��ء���������������Ҵ��£�ı�����ˣ��������ӣ�
������ʵ���⻰��������Щί����Ӻ���ͼ��ϡ�
�������ޱ���ͬ������������Ů�ӷ���ôӺ�������ܸ�����Ҳûʲô��ֵġ�ֻ�����߹����Լ����������϶����ϻ���Լ�ͬ���ˣ�û�뵽�����������ĸ���һ����ǰ��˲���һ������Ȼ�����Ǵ���������ģ������Ĵ��������ڡ�ı�����ˡ�����Ȼ��������������Ҳһ��ɱ�ˣ�Ҳ����˵����������Ż��и��飬��ô�������Ͳ�Ӧ�������������֮������˻�ˮ����ϧ�Դ�ֻ��һ��֮����������̰�������߳����Ȿ�����ߵ�һ����
���������أ������������Ҳ̫�������ˡ�վ����������������Ȼ��˵���˳��²���������ࡣ�����Թ��ߵ��۹⣬���������˵�����£���游�������£�����������������ô�����е���Ҳ�����⡣
��������������ôһ��ʵ�飬��ʦ��һλŮʿ��һ�ݺ��Լ��й�ϵ���������ﱣ��һ����������Ҫ���ˡ������һ�����ػ�ȥ����λŮʿ����������ɷ������Ľ����Ҳ�õ��˺ܶ�Ů�Ե���ͬ����Ȼ�����Ĺ��̺�ʹ�ࡣ������λŮʿ��˵������ȥ��ĸ����ʱ������Ը�����Լ�������֪������λŮʿ���ٵĻ�ֻ��������龳���ɼ�����Եģ��Dzп����ʵ��Ҳ����˵���������ܵ�ʹ��Ҫ����λŮʿ��öࡣ��Ȼ������λŮʿ������ͬ�ߵĿ��������ϵ��������������ˡ�
�������ǣ����ϴ�����Ҳû����������˵�����Ƕ�ĸŮ�Ի�ȫ����������Ȼ��δ�����ڷ���Ҳδ�����ڸ������ٱϾ������ĸ��ף����ԣ���Ȼ���������־�����Ҳ���⡰˫����������
������Ȼ�����ϻ�����һ��·���ߡ������ѹ�Ҳ����ʲô�ö������Ǿ�Ȱ˵�ɷ���ϰ�ͬ�һ������ѹ���С�ӡ���ϧ��Ҳ���ǹ������ң���˴ϻ۵�Ů��ȴû���뵽����취���������ֻ�������������龳�����ᡣ
������ʵ���������ѵľ������ۻ�˭Ҳ�Dz�Ը���ġ����������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