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战争内阁史-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为更吻合(也更符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和入侵阿富汗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苏联人的行为),”沃尔福威茨说。
“B组”的做法创造了重要的先例。自那时起,只要国会议员认为中情局在尽量掩盖某个外交政策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便要求成立一个“B组”,重新研究情报并进行独立评估。90年代中期,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派成立了一个“B组”式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研究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对情报重新审查之后,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得出结论:导弹攻击的危险远大于美国情报界的报告。该导弹防御委员会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牵头,主要成员之一是保罗·沃尔福威茨。
。。
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0)
沃尔福威茨在“B组”的工作似乎对其思想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自那时起,美国情报部门的不健全便成为沃尔福威茨经常谈论的主题。他个人认为,情报部门缺乏怀疑精神;它太容易满足于获得能够证实其预想的情报。批评者对他提出相反的指责;有人抱怨他太想获得符合他自己保守观点的情报。
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逐步走向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开战,沃尔福威茨是布什政府中向美国情报界施加压力、要他们拿出更有说服力的情报来证明伊拉克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官员之一。在五角大楼里,沃尔福威茨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来进行独立分析,并根据有关伊拉克的情报,得出自己的结论;该小组由老资格的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牵头,他是沃尔福威茨在康奈尔和芝加哥大学的同窗好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沃尔福威茨在建立自己的内部“B组”。
到70年代中期,沃尔福威茨不仅对基辛格的苏联政策,而且对他更广泛的假设、他的世界观和他对历史的理解都产生了疑问。沃尔福威茨年纪还轻,他的观点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是,他的观点代表着政治右翼正在形成的对基辛格的挑战。
在1976年夏季里,沃尔福威茨继续在军控局工作,他邀请了两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去给他做实习生。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一天晚上,沃尔福威茨在家里一边吃晚饭,一边为实习生们分析基辛格写的学术著作《重建的世界》,这本书怀着崇敬的心情,描述了19世纪初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在欧洲建立了持久的均势的经历。沃尔福威茨告诉学生们,这是部好书,是基辛格的杰作,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点:这段历史的英雄人物不是现实主义者梅特涅,而是极力主张对拿破仑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因为亚历山大一世代表的是道德和宗教原则。
基辛格显然认为自己与梅特涅相似,他赞同他在主要大国间建立稳定的平衡的目标。基辛格追求对苏联的缓和,基础似乎就是这种模式。在《重建的世界》里,他以厌恶的口吻论及了对道德的关切。“道德的种种主张涉及对绝对事物的追求,对细微差别的否定,对历史的摒弃,”基辛格争辩道。
相比之下,在沃尔福威茨看来,道德原则比稳定或者国家利益更重要。“我记得他说过,基辛格错就错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国家,不懂这个国家信奉着某些普遍的原则,”福山回忆道。
比起维持现有的力量均衡,沃尔福威茨更重视的是政治自由。他是有可能愉快地接受里根派提出的“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纲要点的。许多年后,在小布什政府内,沃尔福威茨把这种重价值观和轻政治稳定的态度用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上。他的道理是,如果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会打乱中东现有的力量平衡,那又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追求他心中的价值观。
基辛格在他关于福特年代的回忆录里,对于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把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美国在斗争各个阶段的使命,是帮助击败挑战和平秩序的邪恶敌人……威尔逊主义反对通过力量的平衡来实现和平,赞成通过道德上的共识取得和平”的美国人颇有微词。这番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沃尔福威茨从福特政府起直到小布什政府的观点。与共和党外交政策层级结构中所有其他人相比,沃尔福威茨自认为是基辛格的反对者,是基辛格在思想范畴内的对手。
除掉基辛格和制止缓和,这代表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美国内部,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和辩论的焦点,正在发生着迅速和根本的变化。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沃尔福威茨均在这些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些变化后来亦在他们的生涯中影响着他们。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战期间,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特别是美军——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力量。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民主党的自由派强调的是美国在海外驻军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主要斗争是在尼克松和乔治·麦戈文的势力之间展开的。
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1)
在福特年代里,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转向了由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的新问题。其根本问题,是美国的实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说,越战对国家的总体军事和经济力量产生了多大影响。美国在军事失败之后是否在衰落?美国是否不得不减少在海外的卷入程度?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放弃反对共产主义,并且不得不接受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上的。他认为,在越战之后,美国必然要缩减力量、向莫斯科妥协。“他觉得,美国受到越战的削弱,这个国家的情绪是赞成军控和缓和,”弗雷德·埃克雷说道。批评他的人认为,基辛格对美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过于悲观;一些人拿他与悲观的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相比。“基辛格是斯宾格勒主义者,”在卡特政府里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说,“他认为美国正在衰退,苏联正在取得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之签订对他们的崛起有约束作用的协议。”
基辛格驳斥了这些指控,不过,从某些方面看,这种批评是公正的。他可能并未认定苏联真的会取胜,但是他的确似乎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77年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基辛格最亲密的助手温斯顿·洛德说,基辛格认为美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基辛格的另一位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基辛格认为,美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独自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基辛格本人则认为,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公众根本不会支持与苏联对抗。
这种观点似乎符合了70年代中期的政治气氛,当时,国会正试图大幅度削减美国的国防预算,并且对美国的情报工作进行前所未有的仔细审查。然而,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共和党的保守派和民主党的新保守派批驳了基辛格的悲观观点。他们都在转向一种既不同于基辛格派、也有别于民主党的麦戈文派的世界观。据此观点,美国并没有衰退;不应该小视美国的力量,也用不着对苏联做出新的妥协。
在福特年代里出现的哲学分歧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2002年,小布什政府在讨论是否入侵伊拉克时,一群共和党内的批评者告诫说,美国必须谨慎,要承认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这些持批评态度的人中,为首的是基辛格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而军事行动的主要倡导者则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
注释
① Richard Nixon: R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② 1996年12月6日对理查德·切尼的采访。
③ Memo to the president from Henry A。 Kissinger re NSC Meeting; Saturday August 10; 1974;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NSC Meeting File; box 1; folder “NSC Meeting; August 10; 1974;” Gerald R。 Ford Library。
④ 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326。
⑤ Robert T。 Hartmann; Palace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⑥ 对2001年12月13日罗伯特·T。埃尔斯沃思的采访。
⑦ “Gerald R。 Fords Remarks on Taking the Oath of Office as President;” Gerald R。 Ford Library。
⑧ Ron Nessen; It Sure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Inside (Chicago: Playboy Paperbacks; 1978年);
⑨ Michael Medved; The Shadow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⑩ Files of Jerry H。 Jones; 1974—1977; box 10; Richard Cheney; Gerald R。 Ford Library。
Ibid。
Cheney interview with Stephen Wayne; Hyde and Wayne collection; Gerald R。 Ford Library。
Handwritten notes from Richard Cheney; May 29;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6; folder〃Intelligence…New York Times Articles by Seymour Hersh (1);〃 Gerald R。 Ford Library。
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12)
John Hersey; The Presid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5); 121。
Nessen; op。 cit。;
John Osborne; White House Watch: The Ford Years (New York: New Republic Books; 1977); 143。
Hartmann; op。 cit。 323; Nessen; op。 cit。; 1089;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535。
Nessen; op。 cit。; 113。
Kissinger; op。 cit。; 99。
Ibid。;
Ibid。;
Hartmann; op。 cit。;
Memorandum for Don Rumsfeld from Dick Cheney; July 8; 1975; in Richard Cheney files; box 10; folder 〃Solzhenitsyn; Alexander;〃 Gerald R。 Ford Library。
Callaway memo to Cheney; November 3; 1975; in Callaway papers; box 5; Gerald R。 Ford Library。
1996年12月11日对温斯顿·洛德的采访;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
Osborne; op。 cit。;
Ford; A Time To He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327。
Medved; op。 cit。;
Osborne; op。 cit。;
Ibid。; xxv。
2001年12月12日对莫顿·阿布拉莫维茨的采访。
2002年6月6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2001年12月10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Kissinger; op。 cit。;
Ford; op。 cit。; 357358; Raymond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Washington;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543。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Military Balance;〃 by Donald Rumsfeld; James E。 Connor files; box 1; folder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3);〃 Gerald R。 Ford Library。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resident Ford; D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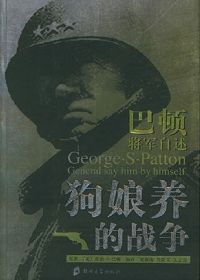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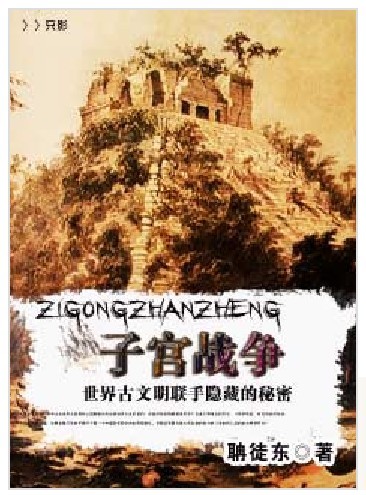


![(综漫同人)[夏目友人帐+兄弟战争]三日暖洋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3/31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