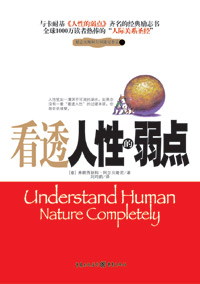走向决定性的时刻(零时)-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只全身湿淋淋的小狗和一个他新交的朋友——十三岁的黛安娜·布灵顿小姐打断了他的思绪。
“噢,走开,唐。走开。臭死了,它在沙滩上压到了死鱼或是什么的。你远远的就可以闻到它身上的臭味,真是臭死了。”
马克怀特的鼻子闻到了臭味。
“一条腐烂的死鱼在石头缝里,”布灵顿小姐说,“我把它带进海里,想把臭味洗掉,可是好像不怎么管用。”
马克怀特有同感。唐,一只亲切可爱的蜷毛狗,因它的朋友坚决不让它太靠近他们而露出一副受伤害的样子。
“海水不管用,”马克怀特说,“热水加肥皂才是惟一的办法。”
“我知道,可是这在旅馆里可不怎么容易办到,我们又没有私人浴室。”
后来马克怀特和黛安娜悄悄地从边门溜进去,偷偷地把唐弄进马克怀特的浴室里,大肆清洗一番,搞得马克怀特和黛安娜也是全身湿淋淋的。清洗完毕,唐非常悲伤。又是讨厌的肥皂味道——就在它好不容易才弄到足以令其他的狗羡慕的味道时。唉,算了,人类总是一样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味道才是高尚美好的。
这个小小的事件令马克怀特开心了不少。他搭公车到沙尔丁敦去取回他送洗的一套西装。
那家二十四小时交件的洗衣店里负责的女孩茫然地看着他。
“你是说马克怀特?恐怕还没有好。”
“应该已经好了。”他们答应过他昨天把那套西装交给他,就算是昨天交给他也已经是送洗四十八小时而不只二十四小时了。换作是女人家也许会这样抱怨,但是马克怀特只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时间还没有到。”那女孩漠然一笑说。
“胡说。”
女孩止住了笑容。她吼了一声。
“不管怎么样,还没好就是还没好。”她说。
“那我这就拿回去。”马克怀特说。
“根本还没动过。”女孩警告他说。
“我还是要带回去。”
“也许明天我们就洗好了——特别为你服务。”
“我不习惯要人家特别服务。只要把那套西装还给我就行了。”
女孩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走进内室。她回来时把胡乱包扎的一包东西往柜台上一丢。
马克怀特拿了就走。
相当荒谬的是,他感到有如打了场胜仗一般。实际上是,这样一来,他就得把那套西装送往别处去清洗!
回到旅馆之后,他把那包衣服往床上一丢,心烦地看着。或许他可以叫旅馆的人帮他擦拭一下,烫一烫。那套西装并不真的有多糟糕——也许实际上并不需要洗清?
他打开包裹,露出烦扰不悦的表情。那家二十四小时交件的洗衣店真是没有效率到无话可说。这根本不是他的西装,甚至颜色也不对!他送给他们洗的是一套深蓝色的。真是胡搞。
他愤慨地看看上面的标签,是写着马克怀特没错。另一个叫马克怀特的人的?或者是糊里糊涂把标签弄错了。
他困扰地看着那皱巴巴的一堆,突然抽动起鼻子。
他当然熟悉那味道——特别难闻的味道——跟狗有关的味道。对了,就是那个味道。黛安娜和她的小狗,千真万确的死鱼臭味!
他俯身翻寻着。就在这里,西装上衣的肩头有一疤污点。在肩头上——
马克怀特心想,这可真是非常奇怪……
无论如何,他明天可要好好的对那家二十四小时交件的洗衣店里的女孩说几句重话。简直是胡搞!
14
吃过晚饭之后,他漫步走出旅馆,朝着往渡口的路上走去。这是个清澈的夜晚,不过令人感到寒冷,颇有早冬的味道。夏天已经过去。
马克怀特搭上渡船,到盐浦那边去。这是他二度重访断崖头。这个地方对他具有蛊惑力。他缓步上山,路过“宫廷”旅馆,再来是一幢坐落在断崖顶上的巨宅。“鸥岬”——他看到漆门上的标示写着。对了,这就是那个老夫人被人谋害的地方。旅馆里很多人都在谈论,负责他房间的女佣缠着他把一切告诉他,报纸上也以头条新闻刊出,令一向宁可看些世界性新闻,对罪案没有兴趣的马克怀特感到烦扰不安。
他继续往前走,走下山坡,沿着一处小沙滩和一些古今合璧的渔民小屋外缘前进。然后再度拾级上山,一直来到路的尽头,换上通往断崖头的小径。
断崖头阴森恐怖。马克怀特站在断崖边俯视大海。那天晚上他也是这样站着。他试着捕捉他当时的感受——沮丧、愤怒、厌倦——渴望脱离一切。可是如今一切已成过去,他已捕捉不到那些感受。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冷冷的愤怒感。被树钩住,被海岸巡逻队员救起,在医院里像个顽皮的小孩一样扰攘,一连串的屈辱。为什么别人就不能不要管他?他宁可一死百了,脱离一切。现在他仍旧有这种感觉。唯一欠缺的是必要的原动力。
那时他一想到梦娜就有多么地痛苦!而如今他可以冷静地想她。她一向就有点愚蠢。禁不起人家几句甜言蜜语就跟人家跑了,或是自认为她自己不同凡响。她是非常漂亮,不错,是非常漂亮——但是没有头脑,不是他梦寐以求的那种女人。不过,那是种美,当然——一幅隐隐约约的景象浮现在他眼前,一个女人飞过夜空,身后白衣随风飘曳……像是船头的装饰人像——只是没有那么显眼……那么坚硬……
然后,刹那之间,不可思议的事有如戏剧般地发生了!——一个人影从夜色中飞奔出来。它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一条奔跑中的白色人影——奔跑着——冲向断崖边缘。一个美丽而绝望的女人,被复仇女神追赶驱向毁灭之途!不顾死活地绝望奔跑……他了解那种奋不顾身的绝望。他了解个中意味。
他一个箭步从阴影中蹿出来,就在她正要冲下断崖时拦住了她!
他粗暴地说:
“不行,你不能……”
他就像抓住一只小鸟一般。她挣扎着——默默地挣扎着,然后像只小鸟一般,突然一动也不动。
他情急地说:
“不要跳崖!不值得这样做。不值得!即使你极为不快乐。”
她发出一声声响,有如鬼一般的笑声。
他厉声说;
“你并不是不快乐?那么是为了什么?”
她立即以低如呼吸一般的声音回答:
“恐惧。”
“恐惧?”他惊愕得放开她,退后一步站着,以便看清楚她。
他了解了她的意思。是恐惧令她没命奔跑。是恐惧令她聪慧白皙的小脸变得空洞、愚昧。她的两只大眼因恐惧而扩张。
他难以置信地说:
“你怕什么?”
她的回答声音低到他几乎听不到。
“我怕吊死……”
不错,她正是这样说的。他一再睁眼凝视。他看看她,又看看断崖边缘。
“原来就因为这?”
“是的。不如快快死——”她闭上眼睛,打起颤抖。她一直颤抖着。
马克怀特在脑海里以逻辑思考把一件件事情串连起来。
他终于说:
“崔西莲夫人?被杀害的那个老夫人。”然后,他责难地说:
“你是史春吉太太——第一任史春吉太太。”
她点点头,仍旧颤抖着。
马克怀特试着回想他所听说的一切。谣传与事实结合。他以他低沉谨慎的声音继续说:
“他们拘留了你丈夫——是不是?很多证据对他不利——后来他们发现是某人故意安排那些证据想要陷害他……”
他停下来,看着她。她不再颤抖。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个温顺的小孩,看着他。他发现她的态度影响到他。
他继续说:
“我明白……是的,我明白那是怎么样的感受……他为了另一个女人而离开你,不是吗?而你爱他……因此——”他中断下来。他说,“我了解。我太太为了另一个男人而离开我。”
她摊摊双臂。她开始无助地支支吾吾说道:
“不——不是——不——不是这——这样。根本不——不是——这样——”
他打断她的话。他的声音坚定而权威。
“回家去!你不用再害怕了。你听到没有?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你吊死!”
15
玛丽·欧丁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头痛而且觉得全身疲累。
调查庭昨天举行,在正式对证之后,延期一个星期。
崔西莲夫人的葬礼将在明天举行。奥德莉和凯伊开车去沙尔丁敦买些黑色丧服。泰德·拉提莫跟她们一道去。奈维尔和汤玛士·罗伊迪出去散步,因此除了佣人不算,玛丽可以说是单独一个人在家。
巴陀督察长和利奇督察今天不在这里,这也是叫人大大松一口气的事。对玛丽来说,他们不在就等于去掉了一层阴影。他们是彬彬有礼,相当和善,可是问不完的问题,平静含蓄的刺探,件件都令人难以消受。现在那木雕脸的督察长该已知道了过去十天中这里发生的每一件大小事情,每个人所讲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动作手势。
现在,他们一走,一切就都平静下来了。玛丽让自己放轻松下来。她要忘掉一切——一切。就只是躺在那里休息。
“对不起,太太——”
哈士托站在走道上,一脸歉意。
“什么事,哈士托?”
“有一位男士想见你。我请他到书房去了。”
玛丽有点惊愕不安地看看他。
“是谁?”
“他说他是马克怀特先生,小姐。”
“我没听说过他。”
“是的,小姐。”
“一定是个新闻记者。你不应该让他进来,哈士托。”
哈士托轻咳—声。
“我不认为他是记者,小姐。我想他是奥德莉小姐的朋友。”
“噢,那就不同了。”
玛丽理理头发,厌倦地走过大厅,进入小书房。当那站在窗前的高大男子转过身来时,她有点感到惊讶。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会是奥德莉的朋友。
然而她还是和和气气地说:
“抱歉,史春吉太太出去了。你想要见她?”
他深思地看着她。
“你是欧丁小姐?”他说。
“是的。”
“也许你也一样可以帮我。我想要找一点绳子。”
“绳子?”玛丽好笑地说。
“是的。绳子。你们可能把绳子摆在什么地方?”
后来玛丽心想她是半受到催眠了。如果这位陌生男子自动提出任何解释,她也许会拒绝他。可是安德鲁·马克怀特,在想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之下,非常明智地决定不作任何解释。他只是相当简单直率地说出他想要的东西。她发觉自己在半昏眩状态下,带着马克怀特去寻找绳子。
“什么样的绳子?”她问。
他回答:
“任何绳子都可以。”
她怀疑地说:
“也许花棚里有——”
她带路前去。那里有麻绳和一截绳子,可是马克怀特摇摇头。
他要的是一整捆的绳子。
“贮藏室。”玛丽犹豫着说。
“啊,可能那里有。”
他们走回屋子里,上楼去。玛丽推开贮藏室的门。马克怀特站在走道上,朝里头望。他满意地叹了一口气。
“有了。”他说。
一大捆的绳子就在门内一个木箱子里,跟老旧的钓鱼器具和一些被虫咬破的椅垫放在一起。他一手搁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