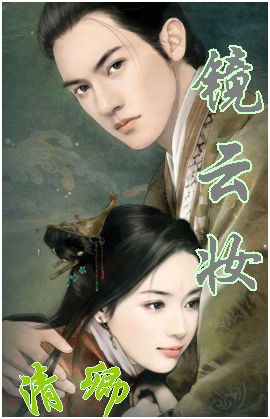乱世明音-第7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觉得好笑,便低头一笑,说:“您不是也有气坏他的时候么。”
高欢听了,呵呵笑了两声,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直咳得满脸通红,憋成了猪肝色。一个侍女连忙走上前去,喂他喝水,又轻轻地顺着他的背。这样过了一会儿,他才缓过来。
他真的老了,目光浑浊,声音沙哑。但是看人的眼神却依然精明干练虎视眈眈。他就那样看着我,一直看到我心中发毛,这才重重叹了口气。
“唉!多年以前,宇文泰还在贺拔岳帐下。贺拔岳派他来晋阳试探我。他当时才二十出头,身长八尺,面有紫气,雄异之相。跟他谈了一会儿我就极为欣赏他,要他来我帐下效命,许他出人头地。他说此行是为贺拔岳而来,要先回关中去复命。我一时糊涂,便放他走了。等到我派兵去杀他,已经追不上了。——我亲手放走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否则,大概我早已统一北方了。”
我在心里默默算着,那时哪一年,我又身在何处。
想到一个人,心思生生打住。
高欢继续说:“我原本以为,五十岁还正当壮年。玉壁之战后,我却一夜间老了。自己都未察觉,等到想再动,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他抬起已然浑浊的双目向梁上看去,叹了口气:“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我恨死了宇文泰!恨不得抓住他生吞活剥!!”
他逼视着我,目光凶狠,令人生畏:“我听他们说,宇文泰最喜欢你。又听说,你们成婚多年一直恩爱如初。你说,如今孤要如何处置你,才能气死宇文泰?”
他如此在意宇文泰,我不愿显得怯懦,白白丢了宇文泰的脸面。于是强打精神,同他对视着:“他一世英雄,不会为一个女人折了志气。”
他看着我,看着看着,突然露出疑惑的目光,仔仔细细打量着我,说:“孤从前见过你。”
我的心猛的一跳,顿生不好的预感。
他探下身子端详着我,问:“武泰元年,你是不是在定州?那间花楼下,你同独孤信在一起。”
我的心啪地一下摔了下去,摔得粉碎。
这才想起,他曾是尔朱兆的手下。难道那晚他也在场?
高欢突然间哈哈大笑,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精神都突然好了三分,说:“黑獭竟然抢了独孤信的女人?!难怪多次听到传言,说他们俩不合,原来关窍在这里!”
被逼到角落无处可藏,只能强打起精神否认:“我不认识独孤信。”
高欢却得意洋洋,好整以暇地抱臂看着我,说:“啧啧,真是薄情的女人。那晚独孤信为了你孤身一人和尔朱兆的队伍拔剑相向,连命都不要。当真是英雄出少年,斩剑为红颜。你都忘了吗?”
那晚他果然也在场。
我的心中苦痛又澎湃,仿佛有一只手,在上上下下反复写着两个字。反反复复写着,印在心上,滴水穿石。
这无情的记忆。
高欢一下子来了精神,从榻上站了起来,来回踱了两步,说:“我有个绝佳的主意。”他看着我,只奸诈地笑着,说:“独孤信跟着孝武帝西奔之后,父母一直滞留在山东。如今他父亲已经去世,只有一个老母孤苦度日。你既同他有旧,不如我派人将他老母接到晋阳来,由你来照顾如何?也算是让你尽一点故人之谊。”
第七十七章大统十五年(公元549年)-秋()
没几天就要入七月,高欢遣人将独孤公子的母亲费连氏接到了晋阳,送进了我住的小宅。
他真是险恶,明知道宇文泰和独孤信早有芥蒂,还要火上添油,加深他们之间的间隙。只怕很快,我在晋阳侍奉独孤信母亲的消息就会传到宇文泰的耳朵里。
然而费连夫人已经白发苍苍,又生着病。人在眼前,我不能见死不管。
她见着我倒是有几分高兴。像是孤独了许久的人终于遇到故人一般,拉着我的手说:“你可不就是那一年如愿带回武川的女子吗?可是你么?叫”她眯起眼睛,似在搜肠刮肚的仔细回忆,想了很久,舒展眉头笑起来,对我说:“我忘记你的名字了。已经过了太久了。”
她已经过于苍老,苍老到完全失去了锐气,如一支将要燃尽的蜡烛。那一年,她若也用这样的眼神看我、用这样的语气同我说话,那还会有后面那么多悲伤的故事。
“我叫莫离。”我轻轻说。
已经过了太久了,其实我也早已不是莫离了。
“对!对!”她笑起来,苍老的脸上布满的那些褶子堆在一起,分外生动。“如愿那时很喜欢你的。他如今在哪里?是他要你来照顾我的吗?他什么时候能来让我看看?”
我心中酸楚。我在她的心中还是昨天的样子。然而已经那么多年过去。
流年已被偷换,只剩满目的物是人非。
如果日子可以从头再来,我会怎样选择?如果不曾去看花灯,如果不曾跟如愿走,如果。
可人贩子拉住我。如愿拉住我。宇文泰拉住我。几乎泫然。这一生竟半分不由自己做主。
我强忍住眼底涌出的潮湿,笑了一下,说:“公子一直很挂念您。”
她叹了口气,闭上眼:“他离家那么多年了。我这个阿母,竟然都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模样了”拉住我的手,浑浊苍老的眼中泛起泪花,问:“他如今什么模样了?家中几个孩子?他生于景明四年,近年也四十六岁了,可显老了么?”
我张口结舌回答不出。他如今什么模样了?
大统九年在栎阳最后一次见到他,匆匆一面就过去了。连一眼都来不及深看,怎知他今日风华?
只得勉力敷衍:“他没怎么变过。总是那样清俊,弘雅。”
“你同他有几个孩子了?”她看着我。
我躲着她的目光,低头说:“我同他没有孩子。”
“啊”她的目光中露出同情的神色。难怪孤身被他遣来东边侍奉老母,原来是因为多年无出,失了宠爱。
“可怜的孩子。”她轻拍着我的手安慰我,“没孩子也没什么。你瞧,我有个儿子,可又怎么样呢?有子莫如无。”
费连夫人沉沉在榻上躺下,半睁着眼睛看着头顶上暗沉沉的梁,自言自语:“我当初为什么要让他出去呢?我要他求取功名做什么?快要死了儿子都不在身边。有子莫如无啊”
她反反复复念叨着这句话,渐渐闭上眼,沉沉睡去。
我轻轻走出去。外面明媚的阳光一下子晃了我的眼。我眯起眼去看那头顶上的苍翠。时节已经入秋,葱翠的叶子已经露出泛黄的迹象。
又一年春去秋来。
蓦地就涌出眼泪。
我想念着宇文泰,也想念年幼的孩子们。这种想念如此坚实而深刻,满满当当地铺陈在心底,压过一切模糊不清的追忆和怅惘。
那是我的夫君和孩子。
在被悲伤的回忆折磨着的时候,只有他们能给我温暖的安慰。
他们此刻在做着什么?长安的阳光也如晋阳这般明媚招摇吗?
也不知道高欢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费连夫人的身体原本就已很差,到了晋阳之后,亦是一日不如一日。请来的大夫都悄悄对我说,该准备下寿材了。
这天是七月初六,费连夫人将我叫到身边,挣扎着从榻上起来,在枕下摸出一枚漂亮的绣囊递给我。挤着满脸的皱纹笑着,神秘又小声地对我说:“拿着。”
我不知何意,接过来。这种绣囊我亦有一些。都是二品以上品级才能用的金缕兽爪囊。而手中这个,只是五彩丝线绣成,并无兽爪图案,只绣了两朵并蒂海棠。
她笑着说:“明天就是乞巧节了。可不是你们汉人女子过的节日么?拿这个去对月乞巧吧。如愿他会回心转意的。”
啊,她竟是为我准备的。在她的理解里,我和如愿的故事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我打开那绣囊的口。里面整齐地插着两枚银针,团着几团五彩的丝线。
我有些不知所措。竟笑出声来,看着她那张似乎被风干的脸,俄而却泪如珠下。
她依旧笑眯眯地安慰我:“没事的。你还年轻,又陪伴他多年,如愿他心里肯定还念着你的好处的。”
她不再是多年前纳姬的仪式上因为听说我的出身而错愕莫名出言尖刻的妇人。她衰朽而慈悲,想要帮助我挽回她儿子的心。
她不知道,多年的离散已经挽救不回了。
只以为触动我被冷落的伤心事,安慰说:“我的绣囊很灵的。当年,我就是学着那些汉女,用这个绣囊里的针线对月乞巧。如愿他阿父一生都没有纳过其他女人。”
说着脸上露出自得又幸福的笑。
我也忍不住微笑,默默将绣囊紧紧攥在手里。
世间女子的心愿果然都是如此。她最大的成就,就是夫君一生只守了她这一个女人。
到了次日晚上,月光如水,银辉满地。深黑色天空中一丝云翳也无。月光太亮,照得周围星光黯淡。
费连夫人让人将她的榻抬到院子里。她要看着我对月乞巧。
我便找了一处没有树荫遮挡的地方,先对月焚香跪拜,然后取出绣囊里的针线,对着那清朗月光正要穿针引线,宅院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我回头去看,整个人立刻如被一张巨网紧紧缚住,动弹不得。
他一身皂衫,皂色小冠,乌靴上满是尘土。这一刻在我眼中太不真实,可他风尘仆仆地来了。
身后跟着同样风尘仆仆的贺楼齐。
我看着他,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再无法控制地上下起伏。可是身体动弹不了;手里举着银针,却忘记了该如何放下。
他未见到藏身在庭院一隅的月光里的我,只注视着正对庭院大门半躺在榻上的费连夫人,一步步走过去,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唤了声:“阿母,如愿不孝!”
声音颤抖,无限愧疚。
当初只身离乡从军去闯功名,也不过为了光耀门楣让爹娘有个祥和晚年吧。怎么竟失散了这么多年不得相见。
事与愿违,处处欺人。
费连夫人亦睁大了双眼,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她颤抖着手,抚着那已经不再年轻光洁的脸庞。那是她的儿子,记忆里一直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年少风流。怎想到岁月凉薄,他也经不住摧残,人到中年。
我看到费连夫人的脸上有眼泪滑落的闪光。她一把紧紧将他揽进自己怀中:“如愿!”
母子多年未见,他仿佛又成了慈母膝下一个垂手聆训的少年,脸上露出和年龄不相称的温顺与乖觉。
半晌,费连夫人伸手打了他一下,骂道:“这个小畜生,终于肯亲自过来接她了!”
独孤公子的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谁?”
呀,苦心隐瞒多日的实情眼看就要被揭穿了。
费连夫人却未察觉,伸手擦了一把眼泪,笑骂道:“来就来了,还装什么?自己的女人,还放不下面子么?”
说罢伸手一指。
他朝我看过来。
他的脸上在一瞬间露出疑惑的表情,随即便是震惊。他睁大了眼,难以置信地朝我走来:“莫离?”
贺楼齐也讶异地瞪大了眼睛:“莫离娘子!”
“公子。”我唤他,手突然松动,银针狠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