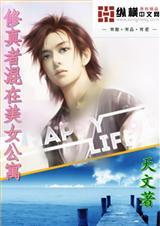混在北京-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去串门子了?”
“啊,人家俩保姆。一个管做饭,一个管看孩子,真舒坦。明天,要坐着小汽
车儿去大海边上住,上海里泡澡去。”
“有什么新鲜,你们全家人不是天天在河里泡澡。”
“河跟海不一样么。”
“你还有完没完?让你干什么来了?一出去就小半天,你舅妈死了都没人管,
你还有脸说呢!”
翠兰不说话了,撅起了嘴。
“以后不许乱串,尽学坏。”
“人家比你家好么,怎么叫学坏?”翠兰又顶一句。沙新想说“人家好你去人
家”,可嘴一软没说出,只说:“表舅很快就要搬到那样的大楼里去了。”
“还坐小汽车儿去海边泡澡?”
“泡!”
“也雇俩?”
“仨我也雇得起。”
“那得让我管她们,我当大的。”
龟儿子哟, 当你妈个X。沙新心里骂着,“行,你当大的,好好儿干吧,你瞧
表舅写的书,写一本就能买辆汽车。等我攒足了,一块儿买,房子、车、电器,啊!”
翠兰两眼放光,“先买房子吧,买十八层上的,越高越好,让我住有阳台的,
人家保姆听说我跟舅舅住一间,都笑话哩。”
“笑什么?舅舅就跟爸爸一样。你跟你爸在一块儿,你爸光着屁股淘金砂,谁
笑话了?”
“我爸还和我妈光着屁股闹哩,往妈肚里尿,妈高兴死了。”
“别说了。”张艳丽红着脸。
“真的,过路的后生也往我肚里尿哩,头一回疼,二一回就好了,三一回,想
这个都把人想死了。舅,你咋不往我肚里尿?”
“天啊,翠兰,你让撑船的后生白尿过了?”
“啊,老尿哩,让我好想哩。”
“你!”沙新脸都白了,人一下子就瘫了。
“艳丽,快好好儿问问她,这个月来那个没有。天啊,别在我这儿大了肚子,
那可就洗不清了。快去小屋里问问去,我的天,龟儿子哟。”
张艳丽慌慌张张拉着翠兰进了组合柜那一头,欢天喜地地出来告诉沙新没事儿,
翠兰月月二十五准来红。沙新这才大喘一口气站了起来。
第二章 人生代代无穷已
从前门站密个透风的人肉堆中钻入车厢中另一堆人肉之中,那些个老老少少大
铺盖卷把他和小雷死死顶在门口动弹不得,一车厢的酸臭汗味,铺盖卷上露着黑汗
淋漓目光滞钝含辛茹苦的脸,大包小裹中散发出霉腥味。
浙义理跟大伙儿扫水筑坝,出了一身汗,倒觉得自己那习惯性背痛轻多了。这
病,只要不写字不弹琴,就一点痛都感觉不到。“这是诗人的职业病。”义理为自
己发现了这个真理感到无比自豪。
随后又烦。这一身臭汗,还得上那间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去洗。没办法,只好趟
着臭水进去,冲了凉,再进乌烟瘴气的厨房里去冲脚。厨房里,“天下第一俗女人”
滕柏菊正和门晓刚两口子一起大呼小叫着用开水浇蟑螂,看着都恶心。煤气灶上煮
着几锅开水,三个人用勺子舀了向成群的蟑螂泼去,赶得黑压压的蟑螂满墙爬。他
们就满墙浇。厨房地上已经成了河,冒着腾腾热气,热水中蟑螂在作垂死挣扎。晚
饭刚做完。人们留下一地的菜帮子、菜叶子、肉皮、鸡蛋壳,陆续有人又吃完了西
瓜,一堆堆的西瓜皮又扔进来了。昨天就轮到冒守财值日,这小子没做,想攒两天
一起做,可昨天的垃圾早已臭不可闻了。冒守财又说今天厕所发大水,等水退了再
说。人们一个个走进走出,骂骂咧咧,都说冒守财不好。门晓刚最损,说:“冒守
财穷根儿改不了,他家住窑洞,肯定是窑里吃窑里拉。”一听这让人不中听的话,
“天下第一俗女人”立即表示反对,要他“少糟改农村人,再胡吣小心这楼上的农
村人联合起来揍你!”门晓刚赶紧吐舌头告饶。
其实滕柏菊从山里来,她最“种族歧视”,最不爱和农村来的人打交道,老想
和小门、小沙、小季和义理这号城里出身的套近乎。她尤其爱散布冒守财的坏话,
借以博得大伙儿一笑,于是感觉自己一下子就不土气了。可攻击归攻击,她攻击小
冒行,别人就不能嘲笑小冒的苦出身,因为当她的面笑话小冒土,就等于是在说她。
滕大姐一走,门晓刚“呸”一声,大笑起来,对义理说:“义理,我刚发现一个真
理。你说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内不爱国,一出了门比着劲儿爱国?我全明白了,咱们
全他妈是滕柏菊的干活。咱们自个儿怎么骂中国落后愚昧都行,一到外国,就是不
许洋鬼子骂中国。因为骂中国就是骂咱们自己。”义理正在油乎乎的洗菜池子里用
香皂搓自己雪白的脚,越搓越觉得脏,洗干净了脚,小腿肚子又让池沿儿上的油泥
给蹭黑了,干脆抓过小门手中的勺子,接了水往腿上泼。
“这丫的也是人住的地方!”义理骂着。听小门一说,忙点头称是。“就是啊,
这道理多明白。可是写歌儿时就不能这么写了,得写成‘长相思/长别离/相见别离
我怀念你/无论我走到哪里/我们永远不能分离’。妈的,我上次写一首歌词给毙了,
就是你那个思路的。”
“唱唱,怎么写的?”难得义理这么有兴致,竟屑于跟门晓刚这号小人物说这
么长的话,小门赶紧得寸进尺。
义理很忧伤地念起来:“黄皮肤啊黄土地/中国/你的命运刻在我深深的皱纹里
/唉/你挣不脱的黄皮肤/唉/我挣不脱的黄土地。这歌儿谱成那种沧桑味儿的,让一
男一女两个粗嗓子的大腕儿唱,就像唱《意大利之夏》似的,准震倒北京。愣让审
节目的给毙了。思维方式简单透了,一根线式的,不会拐个弯。这歌儿多爱国,比
什么‘长相思’感染吧?”
小门一个劲儿点头:“就是,就是,比你所有的爱情诗都好。”
“啧,搭得上吗?我说的是那种在中国不爱国一出国比着劲儿爱国的意思,是
为一个归国留学生晚会写的主题歌。他们都说盖了,在国外就这种感受。一张黄脸
皮,张口中国话,你想不爱国都不行。想爱美国,人家得让你爱呀。”
“哟,义理今天怎么了,上厨房做诗来了?”进来的是胡义,现今小有名气的
青年翻译家。他看厨房脏成这样,干脆不进门,一脚在里一脚在外,“哗”把一堆
西瓜皮天女散花般扔进来,西瓜皮纷纷落水,红红绿绿漂起来,“真像小时在水洼
里玩纸船。义理,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哎。就咱这黄脸干儿,出去受人白眼儿。反正
我不出去。我那帮同学开着‘皇冠’天天在外国忧国,心情老沉重,像是替全体中
国人受难的耶稣似的。可是回来受受呀。住这楼里爱国那才不容易。话又说回来了,
国家也不需要咱们这号穷酸爱国者。”
义理打心里恨透了这种扔东西的架式,还他妈念外国文学的呢,一点公德不讲。
这种人与其住破楼里爱国,倒不如出国打工去,瞧他那自在样儿,闲疯了。但义理
想利用胡义,就热情邀他去自己家唱卡拉OK去,说是镭射盘。
义理自打出了名,就跟穷弟兄们格格不入起来。有他自以为是的原因,也有别
人妒忌的原因。反正是木秀于林,不是风吹就是招风,总不如混在杂树里头。可混
在万人坑里的滋味也不好受,挤挤插插也受挤对,说不定哪天让人家给踏在脚下呢,
倒不如像现在这样秀于林,让他们恨着去。不过义理对胡义很瞧得起,主要是胡义
会两国外语,而义理只会中文。胡义这人好就好在不强出头秀于林,但绝不会让人
踏在脚下。总比众人高那么一丁点儿,让人妒忌也妒忌不起来,因为有义理和沙新
这样的出大风头的人把他给挡住了。最后落个清高自好,受人尊重不对人构成威胁。
学外国文学的那伙子人都这样,对中国的事儿不那么上心,对外国知道得多了也不
热衷于吹捧外国月亮圆,跟哪儿都隔一层儿。好像中国没他们也行,有他们也不觉
得起什么大作用。
可义理现在最用得上胡义。那次记者采访义理,问他今后打算。义理一高兴就
说:“我的诗红透中国了,下一步该译成外文与国际接轨了。”并发誓赶紧学英文,
自个儿译。可真拣起大学时念过的《新概念》英文就头发炸,死活念不进去,别说
译什么诗了。这才想起胡义来。
胡义是北京外语学院英文系的高才生,英文水平之高自不待言,连那满嗓子眼
儿冒泡儿的法文也念得大气不喘。他老婆是德文系的,现在某部国际司当翻译。若
能说动这两口子给译成英文德文和法文卖出去,没准儿就能在40岁前得诺贝尔奖呢。
中国一直没人得过这个奖。林语堂获得过提名,主要因为林语堂有十几本书是用英
文写的,评委能看懂。泰戈尔获奖,也是因为他能用英文写诗。在这个西洋人把持
评奖的时代,亚洲人想得奖没有足够的外文译本怎么行?
当然义理一开始并没有先想到胡义两口子。他一夜间红得发紫,报上纷纷赞美,
电视台也播访谈,各大学请他去给诗社讲课,有点像“文革”时代全中国只一个作
家似的。他那时是想等全中国十几个大语种的翻译家主动找上门来。等了几个月竟
没人来。这才想起屈尊去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找专家。先找了一个研究菲茨杰拉
德的老干巴瘦研究员,这人说话连表情都没有,只说:“我只研究菲氏,别的人一
概不管,我不相信还有比菲氏更伟大的作家值得我译。”又找了几个都差不多。
社科院的遭遇倒挺让义理长见识:这些个什么研究员五六儿的,一个人一辈子
只啃一个外国作家,就成权威了。啧啧,一个人一辈子只干一件事,为一个外国死
人耗费生命,不值得。不过这些人日子挺好过,每日看看书,翻译翻译,写写文章
而已。这样的专家似乎不难当,只要有恒心搭日子就行。于是义理开始看不上他们
了。
然后去找燕京师大外文系的年轻教师。没想到他们一点不感兴趣,也不为他这
样的校友光临感到光荣。说到译他的诗,一个个懒洋洋的。义理算看透了,这些青
年教师毕业几年了,什么事都不做,就一门心思准备考“托福”和GRE,考出国去。
这批没良心的,他心中狠狠地骂,国家培养你们念几年外文,就是为了让你们学会
外文上外国去打工么?
义理真生气,但又想给它们留点面子,不好说他们胸无大志。于是提出经济条
件,问他们想要多少钱。一听钱,人们全来精神,说反正你出了好几本诗,讲课也
收费,又会写歌词,是文人中第一大款。我们也不讹诈你,英、法、德文本,一本
你出一万好了,一本10万字。我们保证10天内招集强兵壮马交稿。义理几乎要气晕
过去。这他妈也是大学教师!都穷疯了。黑心肠的狗东西们!一千字一百块,我成
冤大头了。啊——呸!
义理一气之下打算出五千块搞一个英译本,找到了北大一个五十年代归国留美
博士。这位博士的英文比中文还好,平时几乎不说中国话。听说义理找过社科院的
人了,不屑一顾地说你干嘛找他们?他们不是不想译,是不会译,他们只会英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