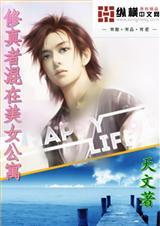混在北京-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他的诗集走红后立即遭到一批骂派批评家的围剿,被说成是“媚俗小曲”,其
中一个叫“金林”的人文章写得最为辛辣。浙义理多方打听,才知是沙新写的。金
林,金林,原来是紧邻的意思。义理对此等暗枪黑弹早已无所谓,嗤之以鼻。文人
相轻,不难解释。连梁实秋这样的大文人不是也恶毒地骂鲁迅吗?沙新又怎能免俗?
不过是西南什么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而已,比义理的燕京师大又低了点档次。当初
他二人也算朋友,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虽然并不互利心里也不认为与对
方平等——义理对沙新的硕士学位很不当一回事,因为那是非重点大学的学位,肯
定是瞎混出来的;沙新又自以为是批评家,不拿义理这永远写不出头的潜诗人当回
事。可某一日灵魂深处爆发新词儿,义理认清了形势,不再写纯诗,而是翻出当年
穷困潦倒几近自戕时的自勉诗和失恋诗向《贴心大姐》这样的青少年报刊猛投一气,
居然几十首同时在南北方炸响,成了所谓“最后一个童贞诗人”。这自然招人嫉恨。
肯定头一个嫉恨他的就是“紧邻”沙新。可能最大的嫉恨还是来自浙义理大把大把
的进项儿。这年头,文人虽然不算最穷,但绝对富不起来,一个个不过水没脖根儿
混着。沙新这号儿批评家更是穷对付着过的主儿,加上生儿育女,就更惨了。玩不
出大部头力作,小打小闹写点儿,他们眼瞅着他几大件儿一夜之间凑齐了,整天晚
会聚会出入大饭店,能不生气吗?再下来就该买汽车买房子了。你们生气的日子还
在后头呢。对了,还有,他们最嫉恨他身淑女如云,尤其是那么些小姑娘跑办公室
来讨教,在书店里蜂拥抢他签名最让他们嫉恨。人比人气死人,想到此,浙义理内
心平静了,只心里说:走你的路,让他们说去吧!然后绰起笤帚,悠悠大度地加入
了扫屎汤的行列。
冒守财早端来些土,用砖头在自己门口垒起一个小坝。然后他号召说:“反正
这水止不住了,总不能一夜都在这儿扫。再垒一道坝,拦住水,让它往一楼流,从
一楼流到长安街上去,要正赶上明天有外国首脑来,今晚就会有人来修。”
小冒这个人一点没有楼上人们期待的黄土高原人的厚道样儿,可又不会耍大聪
明,只会耍小心眼儿,自私得让人一眼就看穿。这样的人不知怎么上大学时还入了
党,进“向导”社后又不知怎么看不上当编辑进总编办公室干上了主任助理。他招
某些领导喜欢,可在这座楼里的平民堆里却最不招人待见。虽说平时自私专爱干眼
朝上翻的事儿,可这个建议却很能打动人心,算是“扩大了私字”,是站在全楼立
场上说的公道话。也是,这破楼一直就没人管,出了毛病全靠楼民们自力更生。出
版社似乎有意锤炼这些年轻人,连消火栓也不给他们发一个。他们也不知道楼会着
火,没人去要。出版社的人管这楼叫“移民楼”,因为楼民们全是外地来京的大学
生,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移民。听了小冒的话,立即有人揭发说长安街上挂满了彩
旗,肯定要来哪个非洲的元首。臭水一上街,公安部门非找出版社算账,社头儿就
该关心移民楼了。于是去院子里铲土找碎砖头,不一会儿就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
大坝,足有十几公分高。随后纷纷洗手冲澡,凉凉快快地准备吃晚饭看电视了。
沙新冲了凉,一拐达一拐达地回到屋里,歪在床上烂泥一样瘫着,只有大喘气
的份儿了。老婆忙下地去找来万花油给他抹头抹背,又扯了一贴“天然麝香虎骨膏”
捂在肿起的脚腕上。还不放心,又让他用酒服了一小撮儿云南白药,说是化淤血的。
床上太热,他就地铺一张草席,滚上去想打个盹儿,这一下午连续作战,累得
他放平了身子就迷糊过去了。他着了,女儿哇哇大哭起来,又饿了。只好强打起精
神挣扎起来去煮牛奶。厨房里十几个煤气火眼儿烈焰熊熊地煮炒着一家家的晚饭,
人们正挥汗如雨做饭洗菜,油烟呛得一个个咳着喷着,影影绰绰在烟雾中战斗。沙
新忙等候在滕大姐身边,待她炒完一个鸡蛋西红柿连声感谢着夹塞儿坐上小奶锅。
煮好牛奶出来,光赤的上身已经油腻腻布满了小油珠,抓了干毛巾一抹,毛巾立即
油黑一片。该喂奶了,这才想起家中还有一个小保姆,天都黑了还不见回来。
“翠兰这妹子真成姑奶奶了,上咱家养老来了不成?你也不说说她!”
“我怎么好说,那是你家的亲戚。我充其量算她个舅妈,还是表的,八杆子打
不着。”
“我也不敢说!像请上帝一样请来的。就咱这破筒子楼,谁肯来这里当保姆?
住这里的人自己倒像保姆。惹不起,由着她吧,能帮把手就不错了。”
沙新又躺到地上去,仰天看着这房子,倒像不认识似的。平常站着看,这十几
平米的面积让大组合柜一隔成两间,觉着挤插插的。可躺下来,立时觉出天地宽广。
翠兰住柜子那一边,拉个帘算个独立世界了,也真难为了这大巴山里的女子。就凭
沾点亲,才敢这么住,不知道的还当是讨了二房呢。那天派出所来查户口,发现这
楼上四五家这样混居的,逼着他们一个个写了证明,证明是远房近房亲戚关系,并
声言要去出版社交涉,让出版社专腾出一间保姆房来。“天下第一俗女人”腾柏菊
家更令人无法忍受,她生了孩子,她奶奶妈妈姑姑小叔子弟妹带着孩子全从山沟来
“伺候月子”,男男女女九口人横七竖八睡一地。那几个女人午睡也要脱光膀子,
敞着门通着风,光明正大地睡,让全楼的人大饱眼福。那天中午让查户口的警察撞
见,竟一个个木然相觑,连衣服也不披。气得滕大姐这个文化人大骂,她一生气就
满口家乡土话。惹得奶奶妈妈当场大哭,说滕大姐“变心了”。小警察们户口也不
查了,哧哧笑着走了。这笑话传回出版社,弄得人灰溜溜的。社长在安全会议上点
了移民楼的名,倒像楼里家家大敞辕门裸睡似的。从此人人不给滕大姐好脸色看,
躲瘟疫似地躲她。
有这个前车之鉴,当初沙新死活不敢从山里招这个表外甥女来,生怕她二百五
出点丑闻,他沙新就成滕柏菊之第二了,就自己骑车到东便门立交桥下的保姆自由
市场去找。那一片黑压压的外地小姑娘,全抱着行李在等人招雇。沙新心头大喜,
先侦察了一番,盯准几个衣着漂亮,人也水灵灵的安徽女子,打算引入竞争机制,
让她们相互砍价儿,谁的报价中了他的标就领谁回去。这二年的时价是月薪一百,
管吃管住。妈哟,一个月工资发回来转手就得给保姆,我他妈成了过路财神。保姆
不但要跟老婆一起吃月子饭,还得搭进一百去。这几年的存款稿费就全搭上罢,只
要能让我安心上班安心出差组搞开笔会就行。沙新打定了主意凑上去开始招标。话
一出口,毫无反响,几个漂亮女子爱答不理地拿眼斜他。那天正是三伏天,他干巴
瘦的小人儿,套件褪色的蓝背心,一条大肥佬裤衩子把两根细腿罩住看着像独腿似
的,一辆稀松咣荡的自行车,他自己倒像个进城谋生的小工儿。若不是那双扶着车
把的白白细细的秀手,根本看不出是个劳心者。半晌终于姑娘们的代表美丽地凑过
来嗲声问:“你家几口人?几间房?电器全吗?抽油烟机可不能没有。我们要一人
住一间,要有彩电电扇。要是又有老又有小,你得雇两个,一个管做饭洗衣服,一
个只管看孩子……”后边的话他再也听不清了,觉得像外语,红着脸推车走了。这
下学聪明了,不敢再贸然亮标,先躲一边看看行市再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不知什么时候,他这个文艺理论硕士研究生,堂堂正正小有名气的青年批评家早已
沦为贫困小户,根本没资格进保姆市场请保姆。这几年发了家的人们使唤保姆,有
充足的房子,满屋的家电,不少人是坐着公家的小车来的,也有自己开车骑摩托来
的。眼看着人家一下车就很内行地叫价儿:“住单间儿,有彩电,一月一百二,伺
候瘫老人外加五十,哪个来,快着点。”这样的阔少儿来一个引起一阵风起云涌人
心所向,小姑娘们争相笑出最高历史水平,像朵朵葵花向阳开放,紧紧围绕在一腿
在车上一腿在车下的阔少爷娇小姐身旁。然后是一阵东扒拉西挑拣,像骡马市上选
牲口一样,认准最优秀的拉上几个上车,说是回去让老爷子老太太过目口试。这只
是预选热身赛,还有淘汰在后头,照样人头攒动欣欣向荣。那阵势算是让沙新真服
了, 承认自己是傻X了。他银行里那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一万块存款在这儿根本擦屁
股纸不如。当年上学时看不上眼的那几个研究西方当代哲学和经济学的同学,几年
下来写了不少批判的论文却是在批判“西马”的观点,其实根本没弄清资本主义怎
么回事。现如今却混政府里当上了领导的笔杆子写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章。政
府部门房源充足,他们当然早有房住了。学外文的几个驻外了,或飞越大洋念书挣
美元去了。最不行的一个也进了国家旅游局,要房有房要钱有钱。他这个中文系大
才子,学的是当代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到头来跟资和产全无关系,倒沦为无产者了。
那天和老婆一对,存款够一万了,心都快跳出来,妈呀,咱是万元户了。以为凭这
一万养活将出生的儿子(生出来却是女儿)足足够了,很为自己一支钢笔一张纸活
脱脱变出一万元感到一种白手创业的自豪。却原来自己蹦几年还是穷光蛋,一个连
那些小保姆都懒得理的傻小子。最终只得从万水千山之外的大巴山里请来这么个二
百五亲戚。
那天下火车倒汽车走旱路又坐船到山里去接翠兰,正赶上她一家人在河里淘金。
男男女女赤条条泡在水里一折腾就是一上午。那山是真绿,山里的天是真蓝,从灰
蒙蒙的城里进了山,眼睛都让那天光水色刺得睁不开。那儿的人很淳朴,赤着身体
很自然地劳作着,有过路的船驶过,他们就停下手上的活计,手搭凉棚冲你欢叫,
那山那水那人,收进镜头里显得很健康美好。沙新无法想象自己的外婆是如何从这
里逃荒出山嫁到成都的。外婆若不出来,就会跟淘金砂的人没什么两样。说不上那
是好还是坏,反正人人有自己的命。沙新在翠兰家船上吃了一顿盐水煮鱼,翠兰穿
上一身翠蓝翠绿的衣服就跟他上北京来了。想着想着,沙新觉得心里发堵,早有两
串眼泪淌下来流了一脖子。赶忙去抹干,不想让老婆看见自己哭。
老婆听他这边有了动静,问:“醒了?才睡这么一会儿?背还疼不?”
“抹了油,好多了。龟儿子红烧鱼哟,烫死我了。”
“你也真冒失,见了那女人躲还躲不及呢。你不知道她有病啊!”
“我吓唬吓唬她,”沙新笑道。
“你故意的?那妄想狂咱可招惹不起。”
“嘘,小声点,咱们是紧邻,嘻。我是太气不过了。你说,都一个单位的,啊,
说起来一个个都是编辑什么的,也算知识分子了,怎么就那么自私自利?”
“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