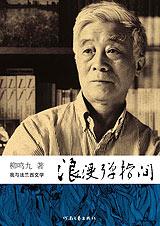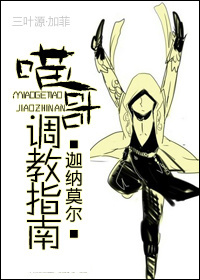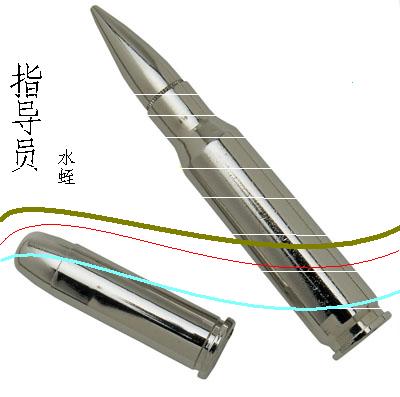第六只手指-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挤进去,亚利桑拿州立大学曾经有意聘请王国祥,但他却拒绝了。当年国祥在台大选择理论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鼓励。后来他选柏克莱,曾跟随名师,当时柏克莱物理系竟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师,对自己的研究当然也就期许甚高。当他发觉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无法达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就断然放弃物理,转行到高科技去了。当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实现,这一直是他的一个隐痛。后来他在洛杉矶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卫星。波斯湾战争,美国军队用的人造卫星就是“休斯”制造的。
那几年王国祥有假期常常来圣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头一件事便要到园中去察看我们当年种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阵子来,看到后院那三株意大利柏树,就不禁惊叹:“哇,又长高了好多!”柏树每年升高十几尺,几年间,便标到了顶,成为六七十尺的巍峨大树。三棵中又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要高出两侧一大截,成了一个山字形。山谷中,湿度高,柏树出落得苍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辉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我的花园终于春意盎然起来。
柏树无故枯亡
一九八九,岁属马斗,那是个凶年。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来。起先我以为暑天干热,植物不耐旱,没料到才是几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尺的大树,如遭天火雷击,骤然间通体枯焦而亡。那些针叶,一触便纷纷断落,如此孤标傲世风华正茂的常青树,数日之间竟至完全坏死。奇怪的是,两侧的柏树却好端端的依旧青苍无恙,只是中间赫然竖起槁木一柱,令人触目惊心,我只好教人来把枯树砍掉拖走。从此,我后院的两侧,便出现了一道缺口。柏树无故枯亡,使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心中总感到不祥,似乎有什么奇祸即将降临一般。没有多久,王国祥便生病了。
那年夏天,国祥一直咳嗽不止,他到美国二十多年,身体一向健康,连伤风感冒也属罕有。他去看医生检查,验血出来,发觉他的血红素竟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公升只有六克多。接着医生替他抽骨髓化验,结果出来后,国祥打电话给我:“我的旧病又复发了,医生说,是‘再生不良性贫血’。”国祥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镇定,他一向临危不乱,有科学家的理性与冷静,可是我听到那个长长的奇怪病名,就不由得心中一寒,一连串可怕的记忆,又涌了回来。
第5节 树犹如此(2)
再生不良性贫血
许多年前,一九六的夏天,一个清晨,我独自赶到台北中心诊所的血液科去等候化验结果,血液科主任黄天赐大夫出来告诉我:“你的朋友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病名。黄大夫大概看见我满面茫然,接着对我详细解说了一番“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理病因。这是一种罕有的贫血症,骨髓造血机能失调,无法制造足够的血细胞,所以红血球、血小板、血红素等统统偏低。这种血液病的起因也很复杂,物理、化学、病毒各种因素皆有可能。最后黄大夫十分严肃的告诉我:“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贫血症。”的确,这种棘手的血液病,迄至今日,医学突飞猛进,仍旧没有发明可以根除的特效药,一般治疗只能用激素刺激骨髓造血的机能。另外一种治疗法便是骨髓移植,但是台湾那个年代,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那天我走出中心诊所,心情当然异常沉重,但当时年轻无知,对这种症病的严重性并不真正了解,以为只要不是绝症,总还有希望治疗。事实上,“再生不良性贫血”患者的治愈率,是极低极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会莫名其妙自己复原。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在台大物理系正要上三年级,这样一来只好休学,而这一休便是两年。国祥的病势开始相当险恶,每个月都需到医院去输血,每次起码五百CC。由于血小板过低,凝血能力不佳,经常牙龈出血,甚至眼球也充血,视线受到障碍。王国祥的个性中,最突出的便是他争强好胜、永远不肯服输的憨直脾气,是他倔强的意志力,帮他暂时抵挡住排山倒海而来的病灾。那时我只能在一旁帮他加油打气,给他精神支持。他的家已迁往台中,他一个人寄居在台北亲戚家养病,因为看医生方便。常常下课后,我便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他。那时我刚与班上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正处在士气高昂的奋亢状态,我跟国祥谈论的,当然也就是我办杂志的点点滴滴。国祥看见我兴致勃勃,他也是高兴的,病中还替《现代文学》拉了两个订户,而且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事实上王国祥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不小,这本赔钱杂志时常有经济危机,我初到加州大学当讲师那几年,因为薪水有限,为筹杂志的印刷费,经常捉襟见肘。国祥在柏克莱念博士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一个月有四百多块生活费。他知道我的困境后,每月都会省下一两百块美金寄给我接济《现代文学》,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家境不算富裕,在当时,那是很不小的一笔数目。如果没有他长期的“经援”,《现代文学》恐怕早已停刊。
妖魔突然醒
我与王国祥十七岁结识,那时我们都在建国中学念高二,一开始我们之间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高中毕业,本来我有保送台大的机会,因为要念水利,梦想日后到长江三峡去筑水坝,而且又等不及要离开家,追寻自由,于是便申请保送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只有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国祥也有这个念头,他是他们班上的高材生,考台大,应该不成问题,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电机系。我们在学校附近一个军眷村里租房子住,过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后来因为兴趣不合,我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台北。国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发觉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论科学,工程并非所好,于是他便报考台大的转学试,转物理系。当年转学、转系又转院,难如登天,尤其是台大,王国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录取了他一名。我们正在庆幸,两人懵懵懂懂,一番折腾,幸好最后都考上与自己兴趣相符的校系。可是这时王国祥却偏偏遭罹不幸,患了这种极为罕有的血液病。
西医治疗一年多,王国祥的病情并无起色,而治疗费用的昂贵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渐陷入困境,正当他的亲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刻,国祥却遇到了救星。他的亲戚打听到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一位韩国侨生,同样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病况还要严重,西医已放弃了,却被奚大夫治愈。我从小看西医,对中医不免偏见。奚大夫开给国祥的药方里,许多味草药中,竟有一剂犀牛角,当时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药的凉血要素,不禁啧啧称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价值不菲。但国祥服用奚大夫的药后,竟然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已不需输血。很多年后,我跟王国祥在美国,有一次到加州圣地亚哥世界闻名的动物园去观览百兽,园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只,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这种神奇的野兽,我没想到近距离观看,犀牛的体积如此庞大,而且皮之坚厚,披甲带铠,鼻端一角耸然,如利斧朝天,很是神态威武。大概因为犀牛角曾治疗过国祥的病,我对那一群看来凶猛异常的野兽,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在栏前盘桓良久才离去。
我跟王国祥都太乐观了,以为“再生不良性贫血”早已成为过去的梦魇,国祥是属于那百分之五的幸运少数。万没料到,这种顽强的疾病,竟会潜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苏醒,张牙舞爪反扑过来。而国祥毕竟已年过五十,身体抵抗力,比起少年时,自然相差许多,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自此,我与王国祥便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时间漏斗无穷尽
鉴于第一次王国祥的病是中西医合治医好的,这一次我们当然也就依照旧法。国祥把二十多年前奚复一大夫的那张药方找了出来,并托台北亲友拿去给奚大夫鉴定,奚大夫更动了几样药,并加重分量:黄芪、生熟地、党参、当归、首乌等都是一些补血调气的草药,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亏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的中药行这些药都买得到。有一家依旧还叫“德成行”的老字号,是香港人开的,货色齐全,价钱公道。那几年,我替国祥去捡药,进进出出,“德成行”的老板伙计也都熟了。因为犀牛属于受保护的稀有动物,在美国犀牛角是禁卖的。开始“德成行”的伙计还不肯拿出来,我们恳求了半天,才从一只上锁的小铁匣中取出一块犀牛角来磨成粉卖给我们。但经过二十多年,国祥的病况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湾,没能让大夫把脉,药方的改动,自然无从掌握。这一次,服中药并无速效。但三年中,国祥并未停用过草药,因为西医也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还是跟从前一样,使用各种激素。我们跟医生曾讨论过骨髓移植的可能,但医生认为,五十岁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风险太大,而且寻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赠者,难如海底捞针。
那三年,王国祥全靠输血维持生命,有时一个月得输两次。我们的心情也就跟着他血红素的数字上下而阴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红素维持在9以上,我们就稍宽心,但是一旦降到6,就得准备,那个周末,又要进医院去输血了。王国祥的保险属于凯撒公司(KaiserPermanente),是美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凯撒在洛杉矶城中心的总部是一连串延绵数条街的庞然大物,那间医院如同一座迷宫,进去后,转几个弯,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进出那家医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闯进完全陌生地带,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为医院每栋建筑的外表都一模一样,一整排的玻璃门窗在反映着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现代建筑物,进到里面,好像误入外星。
因为输血可能有反应,所以大多数时间王国祥去医院,都是由我开车接送。幸好每次输血时间定在周末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课后开车下洛杉矶国祥住处,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输血早上八点钟开始,五百CC输完要到下午四、五点钟了,因此早上六点多就要离开家。洛杉矶大得可怕,随便到哪里,高速公路上开一个钟头车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时间,10号公路塞车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矶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鱼似的公路网上。由于早起,我陪着王国祥输血时,耐不住要打个盹,但无论睡去多久,一张开眼,看见的总是架子上悬挂着的那一袋血浆,殷红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塑料管往下流,注入国祥臂弯的静脉里去。那点点血浆,像时间漏斗的水滴,无穷无尽,永远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国祥躺在床上却安安静静的接受那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