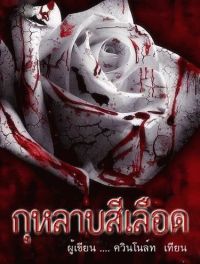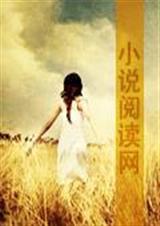玫瑰绽放的年代-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突然发现,他们都有白头发了。
柳秋莎就说:老邱,有时我也真想回老家,过几天宁静的日子。
邱云飞没有说话。
柳秋莎又说:咱们都快老了,还没有过几天清静的日子呢。
邱云飞还是不说话。
柳秋莎还说:以前,我可从来没想过,要过现在的日子。那时我想,在靠山屯,有两间房,一头牛,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我就知足。
柳秋莎神往着,这一阵子,她真的很想“家”,想靠山屯,那里埋着父母,还有她童年的记忆。有时,她在梦里回了老家,站在夏日的山冈上,那里满山都开满了野花,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满山追逐着蝴蝶,还留下了一串串童稚的笑声。有时,她在梦境里醒了过来,会长时间地睡不着,就那么呆呆地望着黑暗,想象着靠山屯的日子。如果,自己和邱云飞去过那样的日子会怎么样呢?现实让她无法去想象。
结果,就在这时,邱云飞出事了。
他写了一份真情告白书,告白书的题目是《我党我军要往何处去》。在告白书里,他真情实感地为党和军队担忧,为国家担忧,当然,他对当下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提出了深深的质疑。
他先是把这封告白书交到了学院的党委,接下来他就没事似的回到了办公室,他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反倒落得一身轻松。他知道,他再也不会为每天写检查而绞尽脑汁了。
那天下班回来,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柳秋莎在厨房里做饭,他还吹着口哨到厨房里站了站。
柳秋莎不明真相地问:你的检查过关了?
他没说什么,只是笑一笑。
结果,事情就弄大了。学院“革委会”火速把那份“真情告白”上报到军区革命委员会。后果,便可想而知了。处理邱云飞的文件一层一层地传达下来——邱云飞现在的觉悟和认识,不可能在部队工作了,他对革命很迷惘,甚至当了革命的逃兵。逃兵,部队是绝不能容忍的。于是,文件上说:开除邱云飞的党籍、军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柳秋莎得到这一消息时,她傻了似的坐在那里,嘴里一遍遍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结果确实是这样。
接下来,领导便开始找她谈话,谈话的人是胡一百,军区的胡参谋长。柳秋莎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胡一百了,他也老了,斑白的头发已经显而易见了。
柳秋莎坐在沙发上,胡参谋长背着手一趟又一趟在她面前走,走了半晌,又走了半晌,然后叹着气说:邱云飞糊涂,他真糊涂!
柳秋莎就说:参谋长,事都出了,就啥也别说了。
胡一百就跺着脚说:他简直不像咱们延安出来的人,说啥不好,偏说那些,那些事是他能说的吗?
柳秋莎就说:那是他的真实想法,不让他说,他会憋疯的。
胡一百就叹口气,恨铁不成钢地说:作为一个革命老同志,太没有耐心了,难道别人就不那么想吗,别人怎么不说?他偏说,嗯……
胡参谋长说到这儿,自知说漏了嘴,忙改口说:咱们党是讲原则的,是可以畅所欲言的,但嘴是不能不有个把门的呀!我看,都是他看书,把脑子看坏了。
柳秋莎站了起来,盯着胡参谋长说:老邱出了这事,我不后悔。组织上看咋处理我吧。
胡参谋长就深深地望了眼柳秋莎,低下声音说:我知道你们的感情,现在要保住你自己,看来,你不得不和邱云飞分开了。
柳秋莎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她惊惧地问:咋,让我和他离婚?
胡一百说:小柳呀,你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当年在延安,不说这些了,看来,只有这条路了。
柳秋莎连想也没想地说:我不,我坚决不离开邱云飞!这时候我跟他离婚,我成啥人了?
这回轮到胡一百震惊了。他认真地看着她,半晌,又是半晌,他才说:看来,我没看错人,邱云飞也没看错人。
柳秋莎就说:参谋长,你跟“革委会”那帮人说,我柳秋莎不会离婚,就是让邱云飞去监狱,我也跟着他。现在医院让“造反派”掌了权,我也没事干。老胡,你要真心为我好,就别让老邱去干校,你跟他们说说,让老邱和我一起回靠山屯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胡一百声音哽咽了,他想说什么,却只说了一声:小柳——便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背过身去,冲柳秋莎挥了挥手。
柳秋莎没有回单位,而是直接回到了家里。邱云飞没了领章、帽徽,正在收拾东西,属于自己的东西。柳秋莎回到家,一下子就把柜门打开了,把属于自己的东西都翻腾出来了。
邱云飞惊怔地问:秋莎,你这是干什么?
柳秋莎说:我要跟你一起走。
邱云飞听了这话,一屁股坐在了那里,他颤抖着说:秋莎,你不能。
柳秋莎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有啥能不能的。
说到这儿,停下了手,一字一字地冲邱云飞说:别忘了,我是你老婆。
邱云飞突然手捂着脸哭了,哽哽咽咽的。
柳秋莎就说:这有啥好哭的,老邱把手拿下来,别忘了,你是个男人。
邱云飞听了这话,果然把手从脸上拿了下来。
他说:咱们走了,那小东呢?
柳秋莎说:当然跟着咱们走,回老家,回靠山屯。
后来,“革委会”对柳秋莎的处理结果是:保留军籍、党籍,和邱云飞一起回乡接受改造、锻炼。
当然是胡参谋长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胡参谋长的努力,她的命运也不会比邱云飞好到哪里去。
二十九
柳秋莎一家三口回到靠山屯时,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全屯的乡亲迎出了二里地,敲锣打鼓地欢迎他们。
队长刘二蛋站在队伍的前面,他先握了柳秋莎的手说:芍药,你是靠山屯走出去的人,今天,你回来了,乡亲们敲锣打鼓地欢迎你。
然后又握住了邱云飞的手道:你是靠山屯的女婿,从今以后,咱们便是一家人了。
刘二蛋还要试图去握邱柳东的手,邱柳东冷冷地站在那里,双手插在裤兜里,梗着脖子,没有和刘二蛋握手的意思。刘二蛋就收回了手,在头上挥了挥说:总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我们全屯子人吃干的,就不让你们喝稀的。
刘二蛋代表全屯,这话就算讲完了。唢呐和锣鼓家什就劈头盖脑地响了起来,社员们吹《大海航行靠舵手》,还吹《社员都是向阳花》。曲调欢快而又明朗,真诚而又热烈。
柳秋莎抹了一把脸上的泪花,一手拉着邱云飞,一手拉着柳东,一遍遍地说:到家了,咱们到家了!
他们来得突然,村子里没什么准备。他们就暂时住在于三叔家里,于三叔显然是经过准备的,东屋腾了出来,墙又裱糊过了,还贴上了崭新的年画和毛主席挥手的伟人画像,一切都是崭新的。
队长刘二蛋就很爽快地说:等过一阵农忙完了,就给你们盖房子,让你们一家老小住上新房,你们一家是咱们靠山屯的客人。
柳秋莎没有把自己当成靠山屯的客人,她早就想好了,这回回到靠山屯,就不走了,他们全家要在这里扎根了,和所有的村人一样,在靠山屯里过日子。
对于他们三口的到来,于三叔和三婶是最高兴的人。他们情真意切地把柳秋莎一家请到炕上,东北人招待客人最隆重的礼节就是让客人上炕,而且还要睡在炕头,只有这样才显示出客人和自家人是一样的。于是柳秋莎一家坐在炕上,柳秋莎已经不习惯坐炕上了,她的腿都盘不上了,于三叔就说:闺女,慢慢来,等你习惯靠山屯的生活,你的腿就盘上了。
于三婶也说:闺女,你们想吃点啥好嚼咕?三婶给你们包饺子。
于是三婶就张罗去了。
在最初回靠山屯的日子,所有的屯人真的把他们当成客人了,三天两头就会有人拿着一些大米、白面什么的给柳秋莎一家送过来。
柳秋莎知道,大米、白面对乡亲们来说也是稀罕物,只有过年过节,家里来客人了,主人才会做上一顿两顿细粮饭。
她每次都要和这些送细粮的人推让一阵子,她哽着声音说:大姑,我们以后就不是客人了,千万别这样。
她又说:大姨,我们以后不走了,你们吃啥我就吃啥。
大姑或大姨就说:芍药,你们城里人吃惯细粮了,可不比我们乡下人,你们不吃好咋行呢?
柳秋莎就流泪了,面对着淳朴的乡亲,她不知如何感谢他们才好。
又忙了一阵子,在队长刘二蛋的带领下,村人找来了木料,做好了土坯,轰轰烈烈地在柳秋莎一家老房场的地方,盖起了一座崭新的房子。
上梁那一天,按着乡俗,在梁上系上了一块红绸子,还燃了一挂鞭,鞭炮热烈炸响的一瞬间,刘二蛋喊了一声:芍药回家了!乡亲们也跟着喊:芍药回家了!
那一刻,柳秋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流泪了。这就是乡亲们,她十五岁离开靠山屯,三十多年后,她又回来了,乡亲们这么厚待他们一家,她被深深地感动了。
邱云飞也被感动了,他背过身去不停地擦眼泪。
只有柳东无动于衷,他陌生而又新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只几天的时间,房子就盖好了。一家人住进了新房。这是一套三间房,典型的东北房屋的格局。东西两间是住人的,中间一间是厨房。夜晚的时候,柳秋莎和邱云飞躺在炕上,俩人一时都没有睡意,窗外是月亮,明晃晃地照耀着。
邱云飞就说:秋莎,咱们现在真像延安那会儿。
这里的情境和月亮,让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延安的岁月。
柳秋莎的心情更加复杂一些,三十多年前,就是在这里,父母被日本人杀害了,最后她走投无路,投奔了“抗联”游击队。那是怎样的场景呀!大雪封山,父母惨死在雪地里的情景仍在眼前。三十多年后,她又回来了,她在心里喊了一声:爹,娘——心里便潮涌般地荡漾了。
也就是从那以后,柳秋莎和邱云飞一起,拿着下地的农具,一把锄头或铁锹,在队长刘二蛋的钟声召唤下,和所有村人一起,自动地走到村头大柳树下集合,然后听候刘二蛋派工,实打实地干起了农活儿。
柳秋莎和邱云飞已经是靠山屯的一员了。
邱柳东在公社中学接着读高中。这里的学校不比城里的学校停课闹“革命”,这里的课还是照上。村人们有一个意识,那就是命不管怎么革,孩子还是要学习文化的。因此,这里的中学还是一派学习的景象。
早晨,邱柳东吃过早饭,便背着书包,走到五公里外的中学去上课。邱云飞和柳秋莎便下地做农活了。他们有在延安大生产的底子,对这里的农活并不陌生,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中午回来,柳秋莎和邱云飞一起忙着做饭,吃过饭,还可睡会儿午觉,下午的钟声一响,他们又出工了。
夕阳西下时分,屯里又开始炊烟袅袅、鸡啼、狗吠,做了一天活儿的村人们赶着牛呀、马呀的,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每一户人推开院门走进灶间,村里的上空便会多一缕炊烟。这时的柳秋莎家,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柳东坐在院子里,面前摆着饭桌,他在那里写作业。
邱云飞抱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