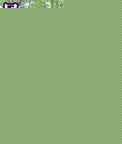倦天下-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中之凤,指的自然是萧凤仪。我却偏不信这些,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天命,即使有,谁又能猜测得了天命究竟何所指。
再次见到萧云衣,还是在夏苗时的逐鹿围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那年应该已满十三岁。
比第一次见她时略高了些,脸上渐渐脱掉了稚嫩的圆润,现出少女清晰的轮廊。所有的人都在说,她的样子比不过她的姐姐萧凤仪,因为在萧凤仪的脸上没人能挑出任何的瑕疵。我却并不以为然,在大明朝美女并不稀罕,就说皇上的后宫,哪个不是闭月羞花。可那又能如何?除了殆误朝政之外并无任何建树。
样子虽有变化,她的性子可丝毫不差。当皇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暗示她曾经对我念念不忘的时候,她对着我像是要呲出的牙让我忍笑忍到几乎内伤了。
那年的夏苗,除了皇上规定的狩猎外,我差不多每天都与萧家的三兄妹泡在一起。一半是为了接近静言,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她。我陪她上树掏鸟窝,陪她下河摸鱼,陪她与萧若衡打赌看谁的猎物最多,总之有她在的地方就永远不愁没事干,她无时无刻不带给我惊讶的感觉。她喜欢玩的都是被称之为“野孩子”的活动。她为了怕萧太傅责骂,总会给活动取上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比如爬树,她会说她要去“登高消暑”,可是她每次都爬不到顶端就挂在树干上等着我把她“摘”下来,或是“提”上去。
她下河摸鱼的时候,会说去“临水观鱼”,可观鱼到最后总是以一身湿淋淋告终,不过萧太傅却不会发现,因为她会在草坪上躺个大字把自己晒干。她会边晒干自己边讲些不着边际的故事,我记的最清楚的,是她讲的小人鱼的故事。只是她没有告诉我结局,那人鱼公主决定不杀她所爱的人之后,她有没有变成海底的泡沫。
她参与打猎的时候,总是要与萧若衡打赌看谁猎的多,还制作了什么“体育彩票”,逼着我们一众人等拿银子下赌来购买哪个会赢。她根本不记得自己即不会射箭也不会用刀剑。不过不要紧,反正有我在,偶尔静言也会被逼的帮她,这让她在与萧若衡的打猎比赛中永远是赢家。
只有在一个地方她才会少有的保持沉默,那个地方被她称为蝴蝶泉。我却并不知道这蝴蝶泉究竟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离她越近,就越看不清楚她。
她明明只有十三岁,可有时说出的话却让人误以为她涉世很深。说她涉世很深,可有时她做出的事却又让人哭笑不得。
就拿打猎来说,她的规矩是看起来可爱的动物不能猎,可每次有烤兔烤鹿的时候她却吃的比谁都香。她还向围场借了一只肥得像猪一样的小狗,美其名曰是她的猎犬,取名叫金刚。她试着训练金刚去叼回我射到的小型猎物,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那金刚只要放出去就会跑得无影无踪,害得她边找边发誓一定要吃了不听话的金刚。
结果自然是没吃成,直到夏苗结束的时候,金刚仍旧没成为合格的猎犬。围场的管事见她如此喜欢金刚,便想干脆送给她带回京城。她却并不要,我问她原因,她有些落寞的说金刚的狗爹娘都在围场生活,她不想带走金刚让它成为孤狗。
看得出来,她对家庭的概念极深,即使她与萧若衡吵得再凶,可那份对萧若衡浓浓的眷恋依旧看得我眼热不已。
萧云衣,快点长大吧,从那次夏苗开始,我在心里有了隐约的企盼。直觉告诉我,长大后的她会更让我觉得精彩吧。
父候提醒我,是时候选个夫人了,我将自己对她的想法禀给了父候,父候劝我三思,并说如果那传说是真的,我留意的人应该是萧凤仪才对。
我淡笑着拒绝。
我并不是什么天命真龙,如果将来真的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也是靠父候和我用命打拼出来的,与天命无关。
即然无关,何必去在意个什么天命凤。
当我成为了天,我的意便是天意。
我以为父亲认可了我的话,却没想到不是……
我向萧府提亲,很快便被接受。
可我却越发觉得不安,还是因为云衣。
我面对她总像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可她对我却仍旧并无任何不同,没有脸红,没有羞涩,没有期待,没有甜蜜。这些寻常姑娘最常见的表情她一概没有。
到底是我并没有走进她的心底,还是她毕竟是与寻常的姑娘家不同?
奉阳节的灯会上,我举着莲花灯照着她的脸,第一次对她说出心里话,可她脸上若有似无的恍惚却让我心里一沉。
不安的感觉,一直持续到看见那个蝴蝶泉的灯展。
蝴蝶泉边木蝴蝶,飞入谁家庭院。
我知道云衣的脖子上一直戴着个木蝴蝶,那是她的宝贝,来历神秘的宝贝。当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心中的怀疑让手都些微颤抖了。我看向云衣,她的脸上有着我从没见过的神采和喜悦,最奇怪的是,她在强烈克制着那种喜悦。她的眼光直直的落在那排字上,有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之后又开始四处搜寻着什么,未果,脸上闪过的失望刺的我心疼。
她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的反常,而事实上,注意到的不止是我,还有静言。
静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每个人都会有些秘密,不是吗?”
我强迫自己回应给他一如平常的笑容,并猜测着静言想表达的意思。
他这样说,是知道什么还是在故弄玄虚?
自从看了那蝴蝶泉的灯展,云衣就像在神游一样心事重重。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怀疑什么,也不要去证明什么。可是,在我帮她猜灯谜的时候,她却离奇失踪了……
她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生气,多疯狂地找了她整晚。
第二天,萧府派人来通知我,她回府了,只是受了些风寒。
只是受了些风寒吗?
父候的探子回报说,那晚,静言对北安候宁铮下了手,却意外的撞见宁铮与萧二小姐在一起。并且,宁铮拼了命也要保得萧二小姐的安全,显然是交情匪浅。
什么叫交情匪浅,宁铮又凭什么与我的未婚妻子交情匪浅。难道在云衣的生命中,遇到他比我还要早吗?交情匪浅这四个字,割得我慌张的痛。看来那木蝴蝶,的确是和宁铮有关。
政局一天天混乱,谁才是有野心的人彻底暴露了出来。这大明天下成了三大诸候眼中的肥肉,人人都想来咬一口,除了那个回了北安的宁铮。
按照原本的计划,父候派大量士兵守住京城入口。
我与静言之间的关系瞬间微妙了起来,与萧府的关系也有了变化。
不用说,凤仪一定是要进宫的,静言并不是省油的灯。我不相信他看不出我和父候的计划,那么萧府夹在中间,竟是进退两难了。
我并不想让云衣为难,也不想为难萧太傅这个典型的文人。可萧若衡跟随段老元帅,手中持有大量的兵权成了东阳一方的大患。
云衣,如果我将来做了什么,不要怪我。
父候的意思,是将已经成为皇帝的静言“请”到东阳,让他成为一个傀儡。可却不知另三方诸候中哪个在到处散播西、南诸候即将攻破京城的消息。我本以为云衣在宫里会暂时安全无忧,却没想到散布谣言之人做的更绝,直接将暴民引入了皇宫。静言通知我去东宫门口接萧家二姐妹,父候却在紧急时候命我去守宗室太庙。我知道父候并不是在意那宗祠是否被毁,他关心的应是存放在那里的传国之宝:玉玺。
我安排一队精壮的士兵和马车去东宫门接萧氏姐妹,以为会万无一失。可没想到父候调回了所有的士兵,竟只安排了一个普通的车夫。
我第一次对父候怒而失态,父候却依如平时的冷静,他说只派一个车夫便已仁至义尽,如果萧氏二姐妹安全回到军营,他无话好说。如果被暴民冲散,便劝我从此断了念想,他不想我成为如明昭帝那样的为色误江山的昏庸之人。
结果正如他所希望的,萧凤仪被送到了城外军营,云衣回了萧府。
我带兵赶到萧府的时候,萧府已燃为灰烬。
我马不停蹄的追着,追上了几个被冲散的静言的守卫和受了重伤的萧太傅和玲珑。原来云衣竟是被静言带走,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见到萧若衡的时候有云衣做个筹码吗?我很怀疑。
愈怀疑便愈嫉妒,愈嫉妒便愈愤怒。于是,当我终于在清晨找到静言的马队时,一箭射死了最先看到的马,代表着正式向静言宣战。
我们不再是君臣,只是对手。
静言仍旧没有丢下云衣,他与云衣共乘一骑。
当他们被逼到瀑布河之时,终于回过头来面对我。
那是云衣吗?从没有过的狼狈和憔悴。她最在意的萧府一夜之间消失,她的大娘被辱自尽,父亲和姐姐落入敌手,哥哥留在战场前途难测,她受得了吗?
看着她带着怯意和不明白的眼神,我本来有的怒气轰然散去,留下的只有心疼,只想把她从静言的马上带走。
静言很快就做出了选择和判断,云衣在此时当然是他的累赘。我看着云衣对他恋恋不舍的眼神,咬着牙把她提上马来,前所未有的粗暴。我环住她,让她呆在我的怀里,拉满了弓对着静言。
这不是围场,这次她订的规矩不再管用。我必须要让她知道,死亡是可怕的事情,让她以后都不敢再背叛我!
她果然不会老老实实的任我摆布,她用力的踢着马腹,干扰了我射向静言的那一箭。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一踢,不止救了静言,更加救了我。
原来我东阳一方的亲信士兵,竟是无耻的叛徒。我回头看过去,记住了那张脸,那张阴笑着的脸。
马拉着我和云衣冲入了瀑布河中,翻滚着碰撞着。我心里再也没有别的念头,只是担心着云衣是否受得了?
滑落瀑布的那一刹,我用力的抱紧了她,用毕生的力气抱紧了她,我用后背,用身体挡住了不断挂擦到的石块和巨大的水流。也许,那是我与她最后的亲密,也是我唯一能再保护她的办法。
云衣,如果你能活下去,请一定要知道,我向你提亲不是听命于父候,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你……
离睿紧紧的抱住了我,将我的头护在他的怀里。大大的减少了我的害怕,只是随着他不断的下坠、下坠,终于澎的一声落在了瀑布下的寒潭中。
说实话,这么高的落差掉下来的几乎相当于是掉在硬地上,虽有离睿的保护,我的身上仍旧被水流“砸”的痛楚难耐,可却不敢开口呻吟只怕腹中进水。只好憋住气息,在水底努力的挣开了离睿的怀抱,却惊讶的发现离睿紧闭着眼睛一点一点的往上方浮去。他晕了吗?还是死了?好在我游泳技术不差,连忙拉着他的身体一直往上浮着,很快便浮出了水面。按照现代的救生方法,我扳着离睿的下巴奋力朝潭边游去。这潭虽深但却是个斜形,潭里的水仍旧不断的朝下游泄着,可水势却明显减了不少,以至于我能够带着离睿拼了力气游上岸。安全了吗?不会有人再追上来了吗?我惊恐的看向瀑布上方却什么也看不清,弥漫着的水雾升腾着,挡住了我的视线。
“离睿,离睿!”我回过头来,喘息着将耳朵贴近离睿的胸口,还好仍能感觉到他微弱的心跳。他的脸色惨白,眉头紧皱在一起,头顶上有个很大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