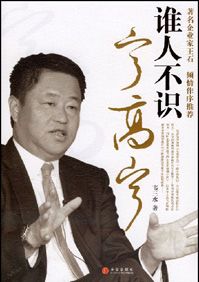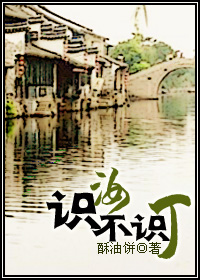细絮飘零不识归-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沈晓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说的话,良久,吃吃道:“你……要杀我?”语气中的置疑清晰可闻。
舒扬淡淡道:“刚才那一剑,你应该也知道你是赢不了我的。我拼着受伤,能杀了你,也值得。”
沈晓完全被惊呆了,不知如何回答。他喃喃着:“我以为我们是好兄弟……”
舒扬厉声喝断:“四年前我们就已恩断义绝!你还有脸说?!”
沈晓面色刷白,梗滞难言。
舒扬冷笑道:“你大可不必担心寂寞,黄泉路上,你有十几个‘好兄弟’等着你呢!”话音未必,人剑合一,如电似火疾射向沈晓。
沈晓原地怔忪着,痴醉了。他闭上了眼,心满意足般等待着心口凉意的降临……没人知道他等到的是什么……
17
二月初,春意复兴,树叶枝条抽出嫩芽,令人心胸畅快的绿色,很快就要将压抑沉郁了整个冬天的冷灰驱逐开去。势单力薄的倒春寒,夺不走人们心中逐渐苏醒的希冀。
清晨,淡灰薄雾笼罩下的城中,弥漫在空气里的豆腐脑的甜香,伴随着小贩的吆喝声,透过围墙传入各家各户(巨烦人的说~)。即使再多的绵绵细雨,再多的潮湿阴暗,在此等清氛中醒来的一天,不枉了好勤力。
这江南的大郡,在润如油水的春雨的滋润下,比往年更繁华热闹了。明日是二月初三,对于寻常百姓来说,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却是宇竭门难得的吉日。
宇竭门自四年前易主以来,并未像新门主上任时承诺的那般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反而因为几次大规模的清剿叛党而日渐人才凋零。从前简炎手下的老人,不但是被杀被囚,还有不少因遭受疑忌而心灰意冷请辞,因害怕株连而心惊胆战告老。
有人看不过眼,劝阻越谈,得到的回应是:当年简炎不也这么做,不照样好好的?自然不会有人告诉他,当年的简门主决不会以叛党之名诛杀“叛党”一家老小,且谓言之:“肃清整纪”。
人心惶惶。动乱四起。
这四年来,宇竭门内部出的事,恐怕比前百年加起来的还多。不仅如此,近一年来,宇竭门在外的生意越来越差劲,从前控制着江南三大郡的布、运两大行业,如今早已是昨日黄花,哪儿有半分威风可言。
除此之外,米、盐更是离奇的滞销,凡是归属宇竭门所有的铺行,不论多精细的货品,就是乏人问津;碍于行规又不能压价,当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贫贱之家百事哀!
越谈猜到其中必有蹊跷,分派各分堂彻查自己所属地盘,他们便懒懒散散,推三阻四。越谈除了勃然大怒,把自己气个半死,别无法子。去年底青龙堂辖属的米行竟在一个月内倒了三家,叫他们交上账本,又是磨磨蹭蹭,直拖了半个多月,越谈忍无可忍,派了心腹亲卫沈晓亲往青龙堂跑一趟。不料,十多天了,沈晓竟也不见踪影,音讯全无,叫他如何不恼!
米行倒闭之事他掩得甚紧,本无太多人知晓,却不知何人将此事传出,于是,宇竭门将垮的流言再度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当此时,宇竭门内部很需要些喜庆之事,冲开这郁抑惶惑的气氛,至少和喜气拉点交情,沾点边。
最后,拣来挑去,最近的喜事只有左护法裴迹的四十生辰了。裴迹今年其实是三十九,只是按着当地的风俗,“男近女满”,男人的整寿提前一年做,女人才是当年做。越谈也不理会当事人意愿如何,硬是下令五堂正副堂主并香主,总坛七航有职衔之人俱得出席寿筵,否则以抗命罪论处。
这一来,苦的却是裴迹。他向来烦厌此类繁冗缛节,简炎为门主时,他能推的宴席尽量都推掉,简炎也不来勉强。可这越谈刚愎自用,不由分说的就把他卖了出去。本来还想二月初三那天找上几个从前白虎堂里的兄弟出去喝几杯,醉一醉便罢,谁知……唉……
他烦归烦,还是只能听命行事。越谈近来疑心极重,若人稍有异议,他便要横加猜疑,搞得门里人人自危,互相畏忌。即若简炎在位时门内兄弟关系称不上相亲相爱,总也比如今这乌烟瘴气要好得多。
“宇竭门已是风雨摇曳,岌岌可危了……”只是万事有合必有分,有始必有终,又何曾有过永垂不朽?
*
裴迹站在自家的院落外的台阶上僵硬的维持着微笑,机械的一次次和源源不断的来人躬背拱手问好接礼,他分明是寿星佬,却比宾客还累。托越谈的福,来参加他四十“大”寿的人,全是门里的头面人物,没一个能得罪的。
他虽是左护法,由于不擅钻营,门里实无甚亲近之人。孤掌难鸣,众人也不太把他放在眼里。今次若非越谈严令,他这四十“大”寿怕会如往年般过得冷冷清清。
并不宽敞的院子里拥挤的摆了十余桌,各位堂主、香主、航主连同他们的侍从护卫共有百余人,申末酉初,乱糟糟的众人总算是到齐坐定喝上茶了。越谈还没来。
已近吉时,阿才请示了几次是否开席,裴迹无奈的苦笑叫再等等。这寿筵与其说是为他办的,不如说是越谈的亲下之策。越谈这主角不到,他这跑龙套的慌个什么劲儿。
正心焦无措间,一个家丁捧着个红色的礼盒疾步冲入后堂,裴迹见到他略现慌乱的神色,心中一凛。那家丁递上礼盒,声音有些抖,道:“公子,这东西在大门口发现的,大伙儿眼睛没眨过,吓人得很,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
裴迹不去打开,问道:“何时的事?”那家丁迷惑的想想,道:“就是……刚刚吧。”裴迹嗯了声,皱眉沉吟半晌,大笑道:“这是哪位前辈和咱们开玩笑呢。你把这礼盒和其他礼品放一块儿去。”那家丁犹疑着,裴迹已不再理会,他只得悻悻照办,心中却是不以为然,暗想:万一这里面是什么毒虫恶蛊,岂不糟糕?一时越想越怕,端盒子的手不免失礼的颤了起来。
裴迹待那家丁出了后堂,唤来阿才,沉声吩咐道:“你和阿海带上几个人去屋外周围仔细搜一搜,别惊动了客人。自己小心些。”阿才看到裴迹阴郁的神色,不敢多问,迅速答应退了出去。
裴迹不是神仙,他不知道盒子里是什么,可是凭着直觉,他感到对方来意不善。不开盒子,尚有转圜的余地;一打开,就戳破了那张欲盖弥彰的薄纸,失了良机。他是否应该派人通知越谈不要前来呢?不管有无危险,总是谨慎些为好。
边想着,裴迹边往前院走去,毫无头绪的猜测着那送盒之人的真意,是恶作剧?是故弄玄虚?还是威胁暗示……
甫入前堂,便有人高喊:“喂——寿星公来了——”众人随之起哄,裴迹暗自苦笑,缓缓走过去,却是提高了十二分警惕,运气至五官,耳目霎时清明,周围的事物声音都清晰起来。
四处并无异样,裴迹不由得松了口气,正要回几句客套话,一声似有还无的轻笑霹雳般闪蹿入脑中。他断然回身,几乎是下意识的朝着大门走去。心随着脚步越跳越急,恨不能从胸膛里蹦出来。
远远的似乎听到熟悉的口音,闻到相识的气味,应该是幻觉吧?“……小的这可不敢做主,请您稍待,小的这便去请示……”恍恍惚惚的绕过照壁,正对上那殷殷笑语,亲切得无害:“那就烦劳小哥了。这是我的名贴——”
他抬目斜睇,触到照壁前呆立的裴迹,眼中一亮,粲然笑道:“啊,裴兄!你好!”裴迹许久没能从他的笑容中脱出,料峭夜风拂过,裴迹倏凛,收摄心神,冷冷道:“那礼盒是你的?”简炎似笑非笑的神情令他莫名的着恼。
简炎无视他的敌意泰然迈入大门,指指身后道:“是我和——他合送的。”裴迹顺着他的指引向他身后望去,微一怔后,雄躯剧震,眼眶登红。那一直垂着头,浑身散发着浓烈杀意的褐衫人,唇角边虽蓄着淡青的胡须,可那轮廓、那眉眼在在让他忆起——
“舒扬……”
裴迹喉中生生哽住,目中已是模糊不清。他伸手欲握舒扬,却遭后者嫌恶的摔袖避过。舒扬倨傲的昂着头,紧抿薄唇,不发一言。简炎漫不经心的道:“徒儿不得无礼,裴‘前辈’在和你说话呢。”
裴迹顾不得惊异舒扬的出现以及何以成了简炎的徒弟,他听到简炎咬重了“前辈”二字,显是听到了适才他在后堂所说的话。他,是有备而来的!
裴迹身形一晃,移位到怡然自得步入厅堂的简炎身前,低声喝问:“你到底所为何来?”简炎笑看他一眼,身子倾前,贴着他的耳际,吹气道:“探望故人。”裴迹不知是因他呼吸的潮暖,还是他侧目触到舒扬的冷冽目光,而颤了颤。
舒扬的怨恨愈深了……那天一个懦弱的决定害了舒扬,也害了他。不论舒扬是否他的儿子,他绝不该将他拱手送出的。他悔得心裂肠断,也是徒劳……他活该被舒扬——自己的儿子——恨上一辈子,是他活该……
他勉强定定神,扯住简炎,沉声警告道:“你不要命了吗?里面全是越谈的部下,你二人……”
简炎浅笑打断:“我是来祝寿的,又不是来打架的,再说——”他将裴迹上下打量——“你不是最盼着我死的一个吗?”说着又向内走了几步。
裴迹脸现怒气,贴身上拦,未及说话,舒扬已踏步而前,袖中隐闪着刀刃银光。简炎斥着“不得无礼!”转向裴迹道:“越谈转瞬即至,我是来和他了结些旧账的,裴兄可不——”
“越门主到——”唱名的小厮洪亮的声音传遍整个院落,纠缠的二人一惊恐一坦然的望向大门方向。惊恐的是裴迹,坦然的是简炎。面无表情的是舒扬。
裴迹头回感到人的脚步声有杀死人的效果,越谈那微不可闻的步伐一声声木桩般打在心头,激得人心绪纷乱。回看简炎,他却是漫不经心,而舒扬更是满面的不以为然。
“人都到齐了么?裴护法呢——”回廊那端传来的声音戛然而止。一身憔悴灰衣的人目光投落在十丈外含笑而视的简炎身上。越谈目光触到他一旁峭然而立的裴迹,寒光显迸,面上闪过青影,转而长笑道:“稀客,稀客!裴护法,既有远客驾临,何以不早些知会与本座?”他表现得甚是轻松,但那声笑许是转得急了而听来有些生硬。
越谈举步上前,看似平常的步法中隐含着玄门至道,气贯奇经八脉,将五脏六腑护得严密。他立定在简炎身外一丈处,右手背后,颇亲和的道:“简兄,好久不见。”他身后的两人却是张牙舞爪,像随时要冲过来。
简炎只如不见,笑道:“确是很久没见了。不过,越兄倒是丝毫未改。在下是来祝寿的,身上没捆火药,越兄何必拒人于千里外?”
越谈有些尴尬,背在身后的右手放下身侧,一会又背了回去,冷笑数声不答。裴迹暗叹,张臂道:“请。”简炎向越谈颇有意味的笑着,偏让开身,道:“越兄请。”
越谈的目光在简炎和裴迹身上转了几圈,冷冷一哼,倏然举步,两个随从狠瞪简炎一眼,跟了上去。简炎走在他后面,凑到裴迹耳边快速压低声道:“这小子比从前还跋扈呢!”裴迹只会苦笑,他身为主人本因领客,可他一看到舒扬心中即时烦乱忧痴,哪顾得上那许多礼数。
舒扬低垂着头一声不吭的跟在简炎身后,陶褐色的劲服配着青黑的束腰,简易的线条勾勒出年轻挺拔的身躯。发髻精神的绑在脑后,梳得纹丝不乱,全身上下透着股干净的少年人气质。唯有……一脸显而易见长久不曾打理的淡青色胡须,使之打了个折扣。
裴迹心中伤感,一叹,自语般道:“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