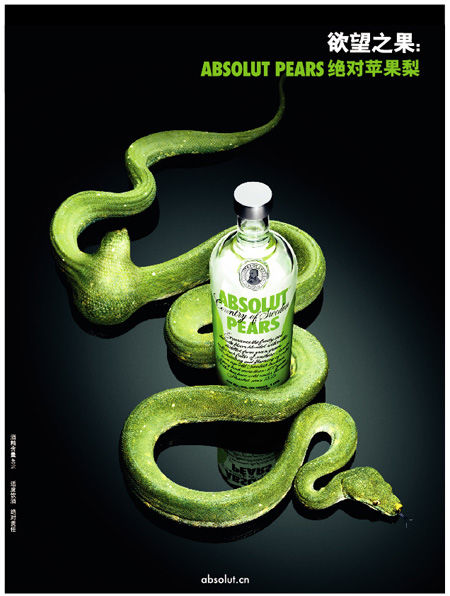苹果-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一转身,我看到夜香港的红色三角裤和黑色乳罩挂在洗手间里,就像两面向我挑战的旗帜用这两样东西向孤独而忧伤的男人挑战,那他妈的真是致命的武器。
夜香港自从上次在我这里乱搞了一夜之后,就没有来过了。
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下面被我弄破了,走路都痛,还流了不少血。
说完后就小声哭起来了。
夜香港暂时从我的生活里消逝了。
每天我去报社上班,坐在豪华考究的主编办公室里,为明星们的绯闻艳史签发〃同意刊发〃的字样。
其实大部分时候,我连那些稿件看都懒得看,只是偶尔把标题改得更露骨一些,更刺激一些,更能让明星们愤怒一些。而我手下的那些娱记们往往会被我几个字的改动,惊得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用夜香港的小学同学、娱记高佬七的吹捧话说是:〃哇噻!胡主编简直成了娱乐圈的教父啦!〃
晚上报社的专车把我送回来。每天吃完报社那精致的晚餐,我打着饱嗝,坐在油光闪亮的桑塔纳里,翻着一大叠花花绿绿的香港娱乐报纸。
有一次,我在车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司机老王小心翼翼把我叫醒时,我还毫无道理地发了一通脾气。
或许在老王眼里,我他妈的只是一个年轻的混蛋。
每天回到寓所,孤独就像一条忠实的狗也跟着我回来了。
我一进门,把皮鞋往一边一甩,光着一双臭脚,打开冰箱门,拿出一筒啤酒,〃嘭〃地扯开拉盖,一通猛灌,一筒喝完还不解渴,然后又拿出一筒,喝完两筒,我这才感觉肚子发胀,头脑昏沉沉的,脸上微微有些热气。
当我从广州的凉气中惊醒时,我发现我躺在地板上,胸口上一片潮湿,我用手一摸,发现那全是汗水。我手上还握着一只啤酒筒。他妈的我只喝了两筒珠江啤酒,就醉卧在地板上一夜吗?我越来越没出息了。是的,我可能是太疲惫,太孤独了。
更令我惊讶的是,我还发现夜香港躺在我身后。她睡得正香,嘴角带着莫名其妙的微笑,两片薄薄的嘴唇鲜红,一轮广州的圆月正照在她的上身。
这家伙简直是满身香气,但又不是那种随处可闻的庸俗不堪的粉脂气,我弄不懂夜香港为什么会有这种香气?
这绝对是一种纯粹的、具有勃勃生机的香气。我简直要晕倒了。
我在琢磨,她的香气来自于她微微张开的嘴唇?瓷一样发光的牙齿?呼气均匀的鼻孔?还是修长的大腿、紧绷绷的臀部和神秘的黑黑的阴部?
我靠近她。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她的脸,她脸上的潮红。抚摸她的手臂上淡淡的绒毛。抚摸她的耳朵,她耳朵上小小的洞孔。抚摸她乳罩的吊带,黑色的丝绸的吊带。抚摸她的腹部,柔软的腹部上幽深的肚脐眼。抚摸她的臀部,臀部上蝴蝶一样美丽的胎记。
我像一个疯子似的抱紧她,她突然惊醒,身体微微发抖。我感觉到她的骨骼在吱吱作响,这种嵌入式的拥抱仿佛要以牺牲一个人为代价。
我们在麓湖的凉气里开始做爱。
鸟声、雨声、呻吟声一齐响起,广州的夜潮湿而温柔,我们越弄越激烈,我就像王八蛋齐天大圣一样,在她的身体里用金箍棒搅起了波涛。
我们越弄越响,我们狂野的响声盖过了风声、鸟声、雨声,盖过了广州一切声音。
她的脸和脖子在左右晃动,乌黑的长发把脸和脖子遮盖了三分之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是的,我们向一个天堂般的仙境狂奔而去。像一对心急火燎的逃犯。
真是世事如烟,难以捉摸。
我们正在呻呻唧唧的兴头上时,麓湖边那位神秘的女子悲悲切切的哭声顿起。
一小会儿后,她发现我居然阳痿,惊得目瞪口呆。
我抱着瑟瑟发抖的夜香港,灯也不敢开,我们在朦胧的月光下摸到窗台边。
麓湖边那位神秘女子的哭泣让我们内心发毛,双腿打颤。
她的哭声湿淋淋的,阴惨惨的。
我真怀疑她是窦娥阴魂转世。
我抱着瑟瑟发抖的夜香港,她的皮肤上起了一层粗糙的鸡皮疙瘩,她的牙齿也在上下打颤。
看样子,这女孩被吓得不轻。
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我们已经一点性欲也没有了。为此我得出结论,性欲是最经不起吓唬的东西。
朦胧的月色中麓湖像一个正来月经的女人,散发出一股莫名其妙的腥气,但又透出成熟女人的肉欲气息。
〃这个姑娘哭得好伤心。〃夜香港自言自语。
我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我透过她丰满的乳房也能感觉到她心跳加快。
我想,这个哭泣的怀春不遇的傻姑娘,不是一个二奶,不是一个被人抛弃的打工妹,也不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妓女。
我想,她是一个冤死的女鬼。
她是一个上吊的厌世者?她是一个割腕自杀的痴情少女?她是一个被人强奸的白领?她是一个不愿堕胎而被男友掐死的好姑娘?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死法,但她也只能选其中的一种。所以我在此对她胡乱猜测,实在毫无意义。
总之,她是一个女鬼。
小时候我曾被根据张宝瑞先生的小说《一只绣花鞋》改编的电影吓得尿裤子,那只美丽而可怕的绣花鞋已经永远留在了我的童年记忆里。
还有蒲松龄先生的鬼故事把少年的我吓得一惊一乍的;尤其是老蒲所热衷的女鬼故事,还掺和着送上门来的爱情,穷光蛋读书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和漂亮的女鬼尽情乱搞。
这种好事也只有老蒲才想得出。
我一边搂着夜香港,一边胡思乱想。
想着想着,我眼前出现了幻觉:那只张宝瑞先生的绣花鞋猛地出现在我眼前,老蒲的妖媚女鬼也仿佛要随时降临到我的床上。
更可怕的是,我开始怀疑怀里的夜香港也是女鬼变的。
她为什么这么漂亮?这样光滑如绸缎的皮肤也只有女鬼才有吧?她身上奇怪的香气是不是老蒲所描述的那种?她左乳下那个美丽的黑痣是不是鬼的标志?
我仿佛进入了老蒲的境界。
我晕头转向,五迷三道,心中乱成一团麻。
但这一切都只是年发生的故事。
后来,后来,一切都改变了本来面目,这就是我的青春,我们的青春。
整个秋天,麓湖边那个女子好像都在嘤嘤哭泣,躲在麓湖的月色里莫名其妙地哭泣。
或许她只是偶尔哭一哭,是我出现了幻觉而已。有一天夜里,月色稀薄,夜雾散尽,她又在那里哭。我似乎不再怕她了,她如果是鬼也是我最熟悉的鬼了,她如果是被谁伤害的姑娘,那可能就是我心目中的好姑娘了。
我披上外衣,穿着拖鞋,溜出房间,穿过楼下乱七八糟的自行车和一排私家轿车,从小区后墙的一个破洞里翻过,来到了麓湖边。
麓湖很安静,水汪汪的,像一个淑女偷偷袒露出的肌肤,冰凉、光滑,让我怦然心动。
麓湖边的野草很深,带着甜甜的露水刺得我的脚生疼。
我很兴奋,心跳加快。
我在想,我终于可以见到你了,我的女鬼,我亲爱的女鬼,我可怜的小妹妹,躲在夜色里引诱我的女鬼,我要见到你,如果你像仙女一样漂亮,我可要与你相爱,如果你衰老不堪,满面痛苦,我就拉着你的手,听你痛苦的倾诉。
女鬼啊,你这折磨我的人,我在向你靠近,向你毫不犹豫地靠近,一个尘世里热爱美女的男子向你走来。
女鬼啊,让我们不要询问彼此的身世,让我把你抱紧,什么也不要说。
我发现我他妈的着了魔,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像一个痴情者去与自己最心爱的人约会。
但我知道,即将与我相见的人多半是个女鬼。
我在湖边的杂草里走了十几分钟,双腿冰凉,头冒虚汗。
那个女人一直没有出现,好像离我总有那么一点点,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哭泣,但只要我往她靠近,她就后退。
她像在与我捉迷藏似的。
我紧紧追随着她若隐若现的哭声,我仿佛吃了迷魂药,我渴望与她相见。
湖上空星光迷乱,湖面静悄悄的,紫气升腾,唯有那神秘女子的哭泣和我那粗重的喘息声。
我完全被这悲伤女子弄得晕头转向,不禁发出叹息:〃我的女鬼啊,你到底在哪里?你要把我引向何方……你不要羞涩,你不要害怕我……〃
突然我一抬头,看到一双脚从湖边的栏杆上垂下来,正在湖水里濯洗,那双脚水淋淋的,是一双妙龄女子的美脚,纤细、洁白、光滑而修长。
我被眼前这一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差点晕眩。这真是人生的奇异景象,它是美的,但又是极为恐惧的,让你魂飞魄散,而又忍不住一阵窃喜。这是多么漂亮的脚啊。
那双脚在湖水上晃动,轻轻拍打水面,溅起一小片水花。
我被那双脚迷住了。
但接着让我浑身发抖的是,拥有如此美脚的人却没有头,这是一个无头女鬼?
我的心一下子窜到了嗓子眼里。
我呆在那里至少有三分钟,四肢都不听使唤了,头脑一片空白。
我知道我他娘的真正来到了老蒲的《聊斋志异》和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的现场了。
我反应过来后尖叫了一声,转身就跑。
〃不要跑……既然来啦就见我一面吧。〃那个无头女鬼的声音传来,确实是异常温柔的声音。
我站住,但不敢回头。
那个声音又传来:〃你是个男人,怎么会怕我一个女鬼呢?〃
我已吓得大气不敢出,他妈的我真与鬼对上话了。
〃我也有爱情,我也有情欲,我也有痛苦,当然我现在只感觉到痛苦。快乐就像夜空中的星光,已经离我的生命非常遥远了,我知道你也有爱情,但比你的情欲少,你的情欲像我脚下的湖水一样多,一样晃荡不安。你和我一样,并没有什么人生的快乐,人生是一场骗局,爱情只是一场交易,情欲的交易。你不要如此慌张,不要如此气喘吁吁。我陌生的朋友,你可以转过身来,好好看看我是谁。你完全可以转过身来,转过身来与我拥抱,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与我长吻。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啊!不!不只是一个秋天,我等你已经有一千年。你这样的花花公子非常好,你好色,你一辈子都逃不过女人的手掌。你不要以为你是在玩弄女人,其实是女人玩弄了你。不过,谁玩弄谁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你快乐吗?你爽吗?你释放了你的痛苦吗?你空虚吗?你无聊吗?想一想,我的朋友,你与那么多的女人乱搞,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只要想一想,就会痛苦不堪,就会为自己浪费那么多的激情,而更加难受。告诉你,我人世的朋友,这就是可恶的人生。〃
说到这里,她的话戛然而止。她有些犹豫,她像在想是否要说出下面的话。一小会儿后,她终于又开口了,声音还是那样温柔,一点也不像是个女鬼。
〃人生如此可恶,爱情如此无聊,姑娘如此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一切都是如此让你灰心丧气。那么,我尘世的朋友,请跟我一起走吧!跟我到鬼魂的世界里去吧!那里也有许多漂亮的女孩,你可以与她们谈情说爱,尽情乱搞也未尝不可。但你首先要听我的安排,跟我走。也就是说,你必须先死去,然后重新做鬼。做鬼是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