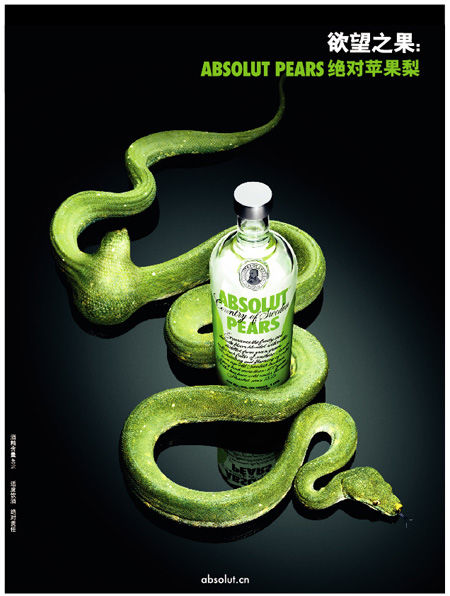苹果-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贺迷跟着唱了几句,就唱不下去了。他只是把脸贴在那位小姐的乳房上傻笑。
大家假模假式地鼓了一通掌。
〃太专业啦。〃木瓜发出感叹,端着啤酒杯向小姐们敬酒。
李宝国突然推开怀里的〃空姐〃和〃村姑〃,嚷嚷着:〃太牛逼啦 ……谁比谁牛……我更牛逼。〃
他从小姐手里抢过麦克风,唱起了一首文革老歌,但就像唱崔健的摇滚歌一样沉迷、疯狂、执著和痛苦。
〃毛主席啊,您是灿烂的太阳,
我们像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
您是灿烂的北斗,我们是群星,
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
您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
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成长,
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
李宝国嘶哑而压抑的声音渐渐变得呜咽,我发现他情绪极为低沉,身体如同风中一根断枝摇摇晃晃。
突然,李宝国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像一个被谁打了的孩子。
他的哭泣用的是一种深沉、哀伤的男低音,听起来既滑稽又令人感动。
那位村姑型的小姐走上去和李宝国紧紧拥抱在一起,像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
看到李宝国这样坚强的男人还如此多愁善感,我心里难受极了。
在包厢外,我点燃一根烟,狠狠地抽着。我痛苦地想,我们到夜总会来消费,就是为了玩,为了放松自己。但李宝国却哭了,在一群三陪小姐面前哭了,这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啊!
我知道,我们不知道该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也知道,我们的生活一片混乱,没有目的,没有具体的内容。
一根烟抽完,我正准备抽二根的时候,一位美丽而有些沧桑感的女人走过来,给我把烟点燃。
打火机蓝色火焰闪起,响起一小曲《致爱丽丝》。在打火机蓝色火焰里,我看到这位女人脸上小小的皱纹。
她说,她是这里的〃妈妈桑〃,想要漂亮小姐可以找她。
我道了谢,接过她的名片,看也没看就塞进了屁股后的口袋里。
包厢里一位声音性感的小姐唱起了一首像是叫《爱人你为什么哭泣》的歌,牛昆也跟着瞎唱一通。
我推开包厢门,看到牛昆正抱着李宝国那位空姐型的小姐,一只手已经伸进了小姐的乳罩里,正粗暴地揉搓着。
徐建设躲在墙角,正津津有味地与一位小姐接吻,想必是一番犬牙交错,口水横流的景象。徐建设蓬乱的头发左右摇晃,小姐被顶在墙上作挣扎状。
木瓜似睡非睡,头歪在沙发上,灯光照在他脸上闪闪烁烁,像一潭死水。
李宝国在看贺迷带来的《存在与虚无》。
那位叫马艳的小姐把头枕在李宝国的大腿上,那本《切·格瓦拉》画册盖在她高耸的胸脯上。
贺迷与那位大波妹唱起了一首《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唱完这支歌,他们俩人偎依着进了另一间房。足足弄了一个小时,贺迷才在木瓜的一再敲门声中出来。他沾沾自喜地对我们说,原来还是一个处女!
但是,但是谁相信贺迷一派胡言呢?
那一夜,在天堂夜总会我们至少喝了瓶虎牌啤酒,唱了首歌,上了盘果盘,抽了盒红塔山(我想,也至少有一半被小姐们藏在皮短裙里偷走了。)
结账时,才发现连包房费、小姐小费、贺迷与大波妹打炮等费用,打折后总共元。
李宝国付完款后,我发现他的皮夹里只有几张一块两块的小钱了。
我们几个都上了李宝国的奔驰。木瓜还在天堂夜总会的门口犹犹豫豫,他嬉皮笑脸地说,奔驰坐不下,他就自个儿打的回去得了。
但在我们发动车准备离去时,那位叫马艳的小姐急匆匆跑出来,与木瓜一起上了一辆夏利出租车,招呼也不打就先于我们开走了。
大家都笑起来了。
木瓜这小子下手居然这么快,谁也没发现他和马艳套磁,而现在居然把人家带回去过夜。
奔驰在三环路上风一样地飘起来,因为喝多了,大家都有点昏昏欲睡。车里一时寂静无声,车窗外黑糊糊的建筑一闪而过。
从侧面看过去,李宝国那张在忽明忽暗的路灯下的脸,仿如一张神秘的雕像面孔。
这位老红卫兵据说在〃文革〃中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与老人家还握过手。可他今夜哭了,哭泣得没有任何缘故。
他开着车,一言不发,心事沉沉的。
突然,奔驰里有一股刺鼻的尿臊气,把众人都熏清醒了。
是他妈的谁拉尿啦 ?
徐建设推醒正发出鼾声的贺迷。我一摸他的裤裆,湿淋淋的一大片,热气腾腾的全是他娘的尿水。
这笨蛋炮也打了,怎么就连一泡尿也憋不住?对他真是烦死了。
大波妹把他弄得可真够累的,徐建设死扯硬拉终于把他的裤子脱了下来,他还哼哼唧唧没有醒过来。
我摇下车窗,把贺迷的裤子扔到了黑夜里。那片刻,尿臊气不见了,只有一丝青麦似的精子气息隐隐从风中飘来。
我知道,那确实是贺迷这位情欲旺盛的小公牛的精子气息。
车快到亚运村时,贺迷被风吹醒了。他这才发现自己光着下身。
他愤怒地叫嚷着:〃那骚娘们把我的裤子也偷走了吗?一点职业道德也没有,这样的小姐谁还敢要?……哦!太差劲!〃
我们被他的叫骂弄得哈哈大笑,连李宝国也笑得不行了,差点把车开到路边的树林里去了。贺迷就这么肯定是小姐偷走了他的裤子!真他娘的太有趣了。
那夜,贺迷一路不停地骂着那位大波妹。
后来他从车座位下找到一张脏报纸,撕成两半总算勉强包住了他的小鸡巴和大屁股。因为我们几个谁都不肯借衣服给他,理由是他可能有脏病。
不知那夜,这位诗人老兄是如何像原始人那样系着一张脏报纸摸回屋的?
听说,贺迷二天还重返天堂夜总会大吵了一番,向大波妹要裤子。
裤子显然是无法要回了。它带着贺迷的尿臊气和臭精子气息,悬挂在亚运村路边的某棵树上,或在路边的阴沟里正变成城市垃圾。
这一切如同那疯狂而忧伤的一夜,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变成臭不可闻的垃圾。当你在以后的日子里,偶尔想起它时,你会有一种难受的东西猛地涌上心来,让你喘不过气来。
这种难受的东西,用一个最不好的词来说就是〃恶心〃。
贺迷从天堂夜总会找回了他最珍爱的两本书:《切·格瓦拉》和《存在与虚无》。但书已被小姐们弄得破烂不堪,散发出一股恶欲生活的异味。
英雄格瓦拉的图片上沾满了粘糊糊的东西,贺迷说那正是小姐们做爱时流下的最肮脏的液体。而萨特先生的头像上则是乱七八糟的口红印,难道还有小姐愿与萨特先生接吻?还有小姐热爱《存在与虚无》?
贺迷为此伤心透顶,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对不起切·格瓦拉与萨特的事。
所以他发誓至少半年不进歌舞厅和夜总会,如果有路边的〃野鸡〃敢向他主动抛媚眼,他就要以切·格瓦拉与萨特的名义向她们的脸上狠狠地啐
一口。
贺迷是一个这样的青年:
他一边狂热地喜欢切·格瓦拉与萨特,把这两位早已死去多年的人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偶像,恨不得以他们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另一边他又那么狂热地需要三陪小姐。他曾发出如此感叹没有三陪小姐的人生是黯淡、消沉、没有情趣的人生。
也就是说,贺迷是一个企图从切·格瓦拉、萨特和三陪小姐中获得激情的青年。
他是一个极端矛盾,同时又极为真实的青年。
我们都很喜欢贺迷。
他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
而我,而我还是生活得很压抑。
我发现我只配拥有痛苦的生活。我总是像一个老人那样在思考人生,回忆过去。
我没有展望未来的习惯。
从北京三陪小姐那里,我还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乐趣。而恰恰相反,每次从她们那里消费回来以后,我马上变得更沮丧,更痛苦。
我不能像贺迷那样既可以爱切·格瓦拉和萨特,又可以爱三陪小姐。
我要么去爱,要么去恨,除此别无选择,像一个傻瓜一样。
下面我想回忆在广州所经历的那次爱情。
在我看来,广州是一个最浪漫最具冒险性的城市,广州的街道两旁花枝招展,一派鸟语花香的景象,好像生活在一个异国小镇。广州的街道两旁站了一大堆等着发财的女子,她们大多是妓女、三陪女、身份不明白的女子,她们可能是四川人、湖南人、贵州人、安徽人,她们打扮得极为妖艳,嘴唇上涂满了黑色的、朱红色的口红,一身廉价的胭脂、香水气息。好像她们来到了纽约的某个街区,可以随便在大街上就与男人成交。
广州真他妈的是一个最浪漫最具冒险性的城市。
我很喜欢广州。
我很喜欢一个开放的环境,看到广州有那么多的花花草草,小鸟在树枝上自由地鸣叫,外地姑娘凭本事挣男人的钱,非常直接地与客人讨价还价,我就觉得很放松,觉得生活已经全部敞开了,许多过去认为见不得人的东西一下子都见得了人。
广州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地方,它消解了羞耻和欲望那类最顽固的东西。
何琴琴是一个复杂的、多情的、狐仙般动人的姑娘。
我与她的那一段广州恋情堪称我人生中的一段传奇。
那时我是一个有身份的青年,不像现在身无分文,居无定所,在爱情上也没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众所周知,本人写诗多年,出版了两部根本没人搭理的破诗集,被人戏称为青年诗人。但就是这点,新闻出版局一位处长老兄对本人颇为赏识,于是推荐本人担任广州一家娱乐报纸的主编。
当我在一群爱慕虚荣,梦想混进娱乐圈的女孩子们中拿出那张印得花里胡哨的名片时,往往会引来一大片火辣辣的目光,本人的身份由此得以体现。
那些女孩总是用一种嗲声嗲气的腔调叫我胡老师,好像在逗我似的,但那段日子我感觉不错。
偶尔我也会用她们中的某一个作报纸的包皮人物,把她们搔首弄姿的性感照片印得大大的,配上牛头不对马嘴的肉麻的吹捧文字。她们有了我这些帮助,就可以顺利进入广州那多如牛毛的三流四流电视剧组,或者模特队、夜总会高级舞蹈团伙,开始她们流血流汗的艺术生涯。
与我睡过的女孩儿都说我是一个好男人。这其中的道理我也不明白。或者是我根本就不想去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我最讨厌那种一夜情后在早晨的鸟鸣声中说爱上了我的女孩,我就是去爱一只乌鸦,也不会随便去爱谁。
何琴琴正是我那段娱乐人生的产物。
她是我手下一位〃娱记〃外号叫〃高佬七〃的小兄弟带来的,记得一次向我介绍时,她说她叫〃夜香港〃,弄得我莫名其妙,怎么会叫这种名呢?
夜香港能说一口纯正的广东话,但说话的腔调如同唱歌,柔声细气,尾音绵长,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除了她说话的腔调有点特别,让我动心外,她身上其他东西我看与别的女孩并没有什么两样。
夜香港是投入我怀中的一个小狐仙。一个复杂的,多情的小狐仙。一个折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