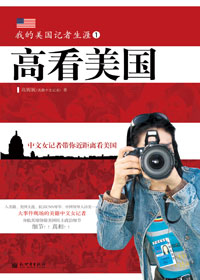美国旅店-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妈咪,相信我,我并没有计划这样,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像你不知道会下雪一样,早上一起来到窗外一看,到处都是白的。
雪是会融化的,你不可以相信任何用雪做成的东西。
我很生气,对她说:为什么连你也这样子?我来美国是希望得到你的支持的。我以为我可以指望你。
指望我什么?指望我从自己的经验告诉你到底有多错?
所以我爱上什么人要由你来决定。
当天晚上我就从家里跑出来,让她与照片上的女儿呆在一起。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妈妈总是喜欢给我拍照了,因为我在照片里是漂亮的,平静的,美好的,而那正是妈妈心中希望的,也是最后锁进妈妈心扉的女儿的形象。
第二十八章 我看到了一颗犹太灵魂(1)
从家里跑出来后,我就去了继父那儿。大卫的妻子把我引进他们新买的公寓式房子,房子不大,但是新的。他们的收入只能买这样的房子。我调侃道:大卫以为他是海明威,其实他只是在婚姻次数上和海明威相似,海明威结了四次婚。你要担心埃他妻子大笑:我不担心。再过几年他需要找一个推轮椅的了,我担心什么?我很快地喜欢上了这个拉丁裔女子。
他穿着一件舒适的套头衫。因为舒服的缘故,袜子是反着穿的。一出门,哪怕只是到门口信箱取邮件,他仍然不忘记把袜子正回来。他只能在自己家里偷得那一点舒适。缓慢而坚持不懈在秃的头发现在已经不再掉了,因为已经没有多少头发可掉了。他半躺在一张支起的沙发上,腿上架着手提式电脑。样子十分随意,像在海滩上晒日光浴,但他的表情并不惬意。他的身后是一排排的书,一堆堆的知识。还有那本打开的深红色的硬皮字典,与他呈现同一种又膨胀又干瘪的样式。这些书打开容易,合上却不容易,沾了人气。人也如此,沾了书气,大卫成了有气息的知识学问。那在灯光下熠熠闪亮的头顶就是他知识的象征。他是一个勤劳的农夫,刚送走一批收成,又已经为下一批的收成忙上了。
我看见了他一夜没睡的杰作:电脑上稀稀拉拉的几个字。现在他见我来了,说他准备退休了,这样可以集中精力写一部大部头。他一直希望能完成一部大部头作品。
我和他太太相望着——他又来了;他一说完,我们就冲他笑——谢谢,终于说完了。于是我进一步看出他的冲突:这种人生是丰富的,却总有点寂寞,因为大卫在乎功名,而又不善于经营功名。我想我可以体会到他的丰富与落寞。
大卫,如果写作成为一种痛苦的话那就别写了。我对他说。我选择写作,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写作更让我高兴。如果有一天,写作无法让我高兴了,或者我找到比写作更开心的事了,我会欣然地放下笔。但我却觉得,对于大卫,写作从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却有着摆脱命运获得拯救的意思。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求赎。
他听不见我似的,接着说他的计划:我是想写完这部小说就好好休息一下,考虑到亚洲的几个国家旅行一次。我希望能再去趟中国。
当心身体埃
他感激地笑笑。他的里里外外都被一个当年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中国小女孩看在眼里。他知道小女孩识破了,但他感谢小女孩不说破。不再像十二岁、十八岁时那样,他看到了我的成熟。
我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本书,说:一天我路过书店,正巧看见这本书。这个作者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在我小说出版的同时,大卫也新出了一本书。书店上万本的书籍,大卫的书站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像大街上站着几个流浪汉,落了单似的不合群。如果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继父,我亦不会看的。这是一个各种声音都存在的国家,要想被人听见,就要喊得比别人怪。大卫的声音太正宗了。
我们的小说都谈到归属的问题。归属问题所引起的苦闷,为我们的文学提供了基本立足点。不同的是,我的小说是写实的,具象化的,以显性呈现的方式与中国移民的生活和文化进行联结,作品本身就昭示了它的中国特质。而大卫并不专注于犹太生活的再现,甚至有意识地回避犹太人这个词,但是你能感觉他是从他的犹太灵魂直接出发的,在犹太性与普遍性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寓言关系。他把犹太性作为一种记忆,而文学的本质就在回忆。
大卫扫过一眼,立刻就明白过来,笑道:这个老家伙还活着呢。我当他死了呢。
嗯,让我查一下,在他的生平介绍里,!”945到——,还好,死亡日期是空白的。
大卫笑,他已经习惯于我这没心没肺的套近乎。
大卫,我看了。
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了一颗犹太灵魂。
尽管他不是宗教色彩浓厚的犹太人,甚至已经脱离与犹太神学的任何联系;尽管他是美国第三代的犹太移民,已不会说什么希伯来语或者意第绪语,但他的血管里毕竟流淌着犹太祖先的血液,几千年的犹太精神与世俗生活的紧密结合,不可能不渗入他的初始观念与思维模式。 比如他说他是犹太人,但并不是犹太作家。他不是写犹太人的生活,但在他的作品里,他的犹太气质与犹太痕迹刻在其中。因为在他看来,犹太人的阐释与人类共同的感情并无二致,并行不悖。他把犹太人作为人类的代表。
谢谢你,孩子。
我又将自己的小说的中文版送给他。他明明看不懂,也一本正经地看,嘴里念念有词。
看什么呢?
我在看有多少字,你能赚多少,我又能从中拿到多少。
我笑。
文学永远是我和继父之间最安全的话题。我们可以从彼此戏谑到推心置腹。
海伦,说吧,你到我家来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公事公办的样子。
大鼻子犹太爸爸啊,难道我就不能单纯地来看望一下你吗?
晚上十一点钟,单纯地来看我?海伦,你就直接说你和你妈妈又怎么了?
关于我的男朋友,是的,我们是有问题,他还没有离婚,但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这是最重要的。可是我妈咪她就不知道这点,她也想让我开心,但是她不想让我决定什么能让我开心。
你妈妈只是在保护你。
我知道。
她不想让你受伤。
我也知道。但是我认为自己知道这次是对的。大卫,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对的?
他故意露出羞愧而滑稽的表情:向一个有过三次婚史的男人咨询婚姻,你真的是找对人了。
我自问自答:他会离婚的,他答应我的。而且我需要他离婚,给我希望。
你错了。
关于他离婚吗?
不,关于希望。希望是自己给的。
很快就证实我妈妈是正确的。而我就是不能接受她是正确的这个现实。他是来美国找我了,只是他告诉我没有完成的事情还是没有完成。我承认他是否一个人对我很重要。我需要证明我妈妈是错的。
他握着我的手,好让我知道他的无奈和矛盾:问题不是我不想完成它,而是我太太可能患了乳癌,现在还不知道。
我得到暗示:如果他太太没有患乳癌,他就向她提出离婚,否则他就必须留在她身边。我沉默了很长时间:如果你有别的地方要去,你就去吧。我把手收回来,收得很迅速,尽量不让他觉得我有多么的优柔寡断。
第二十八章 我看到了一颗犹太灵魂(2)
海伦,请你再重复一遍。
他当然听见了我的话,但他觉得应该给我一个机会把话收回去。
我看了他一眼,意思是谢谢他的机会了。你需要我说出来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听着,如果她平安无事……他又伸出手来握我。他认为自己是一动不动的,但我感觉他的手心有了轻微的松弛。
我说:已经没有如果了。
你说什么?他笑笑。他认为我这样假装坚强是孩子气的,甚至是愚蠢的。我爱你,我知道你也爱我。
是的。你说的没错。
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探查、挽留、遗憾、眷恋,一一传给对方。当我们这样手握着手走在上海外滩时,让我们误以为我们都很无辜,无辜地享受得起这份无法命名的关系,无辜地坚信相爱中的人有什么过错。现在回到了我们熟悉的环境,那种混沌的无辜失去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将这份无法命名的关系维持下去。
回忆起在上海相识相知的日子,我们交换了一个会心且衰弱的微笑。像是笑一段童年往事。那种笑只属于穷途末路的情侣;那种笑让我们确定一切已经事过境迁了。不是吗?人们只会对自己孩提时代的往事有如此缅怀和坦诚的笑容。因为它的久远和幼稚,人们已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而且纠正。
我说:我们可以这样下去,如果我只是我,你只是你,但我不只是我,你也不只是你。
你要我离开吗?
不想,但这会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再次分手,两人都用了一股内力,一股不让对方察觉的力量,渐渐地从对方的手心挣脱。我们持续地握手,再持续地分手。什么都在这之间了,回答已是明确的了。我们作为恋人向对方追探的一切,对方一一作了回答,自己也一一作了交待。奇妙吗?手具有大量潜语,而且非常诚实。无需再用嘴巴去绕弯子,讲一些虚情假意的话去哄自己,也哄别人。
我们都感到一阵的轻松,却不敢去承认这种感觉。同时我得知,他和我大概一样,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他把我当作一个特别亲切的人,期待着一场意外的温情。
我带着受伤的爱情去找大卫。有时候我感觉他是除了我父亲之外惟一理解我的男人。他缓缓地半起身问我喝什么,茶还是咖啡?我说我喝可乐吧。他说你的选择是在可选择之外的,我这儿没有,那是年轻人喝的玩意儿。我说那我就什么也不喝了。然后忙叫他坐着别动:我来帮你。他动作加快:不用,你这个不喝茶的年轻人,会把我的茶糟蹋的。我说:为什么老人都喝茶?你年轻的时候喝不喝茶?他说不。我笑道:怎么回事?一天你觉得自己老了,你觉得自己得喝茶了。他喝的不是超市里五美金一大包的立顿茶包,是正宗的毛尖,看着茶叶一点一点地化开。一个懂茶道的人。
我要出一趟远门了。
又要走了?去南极吗?
我想了想,说我要去中国。又说我要回中国了,自己心里一沉,本来还没决定的事情现在倒好像已成定局。大卫,你知道我在美国的时间并不多了。
大卫定定地看着我:你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不多了。你看,我们都老了。时间都不多了。
大卫,你还记得我妈妈的那本私人帐户吗?
我知道大卫从来没有忘记,说“还记得”,言下之意是他曾经遗忘过,那是对他的尊重。我说:其实她是为了替我爸爸还债才动了那钱。
我知道。我去银行查的。对不起,我是比较计较钱的问题,你妈妈和我常为这吵架。她偷偷地存私房钱,还寄给她的前夫,你要搞清楚,她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