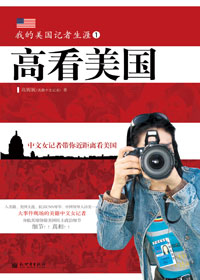美国旅店-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的好的。我无动于衷地说,打了个哈欠,现在我要回去睡觉了。
我们谈谈性这个话题吧。
妈妈突然说,而且突然改说英语,让英语去说她难以启齿的话。
外语就像一件外套,加上非民族性的夸张的手势和习惯动作作为道具,成为一种盾,从此有了某种可以防守的便利。她躲在盾后面,以为也能谈几句性的话题。即便这样,这话到了妈妈口中,还是无端地不自然起来。我敢打保票,她肯定又是受了某本亲子杂志的影响,它们总会讲一些套话:什么如果你不用“正确”影响他们,那么你的孩子就会被“错误”影响;什么你若不积极地花时间在孩子身上,他们会惹上麻烦要你花更多的时间去收拾。我妈妈感觉有对话的必要,只是她强行套用美国家长的模式,有点造作。她甚至无法正眼看我,好像说错了话想立马打住,好重新来过。
说吧,妈咪。然后就一脸祥和地看着她,这一看她就更受不了了。
是这样的……哟,你要不要喝点东西?她完全掩饰不住她的不自在。
不,谢谢。我就是不让她脱身。
她闭了一小会儿眼睛,坚定决心,豁出去了。她开口说道:像你们这个年纪对性都特别好奇,其实没有什么好奇的。
我涂得像两片银贝壳的单眼皮一翻:我早就不好奇了。
她害怕地追问:你什么意思?
我就那么若隐若现地一笑,她更害怕了。
她皱皱眉,就是我奶奶蹙眉的翻版,表示她觉得我太随便。我也跟着皱皱眉,表示我觉得她太不美国,太不酷。
海伦你看看,男人女人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女孩子说我喜欢你,她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成为男女朋友;当一个男孩子说我非常喜欢你时,他的意思是我想和你上床。当一个女孩子说到我家来玩吧,她的意思是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父母;当一个男孩子说到我家来玩吧,他的意思是我想和你上床。当一个女孩子说我想进一步的发展,她的意思是我爱上你了;当一个男孩子说我想确定一下我们的关系,他的意思是……
我大声地与她异口同声:我想和你上床。
妈妈没有听出我的调侃,而是认真地说:你终于认识到问题了。
这种时候她更习惯用英语,而我也更习惯听她讲英语。犹如种种常人嘴里吐不出的词汇在妇科医生那里有绝对的空间。当那些敏感羞涩的词汇还算大方正确地从她唇齿之间轧压出来,说中文的妈妈会突然脸红起来——这些话我可说不出口。可是事后,说英文的妈妈又会稍微轻松——我已经对她说过了。操用中文与英文,是表达自己的两种方式。我们同用英语时,英语的那种率真也让我们少了那份针锋相对。
最后我有点不忍心了:妈咪,我都知道。学校里都教过。
我突然的体贴与善解人意让她有点失措,她只好笑了笑,觉得自己无能的那种笑,畏缩地站在一边。我想如果我把在学校听到的看到的告诉她,她会一蹶不起的。更让我受不了的是她对无知的优越感,你们也太早熟了。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我对她说:妈咪,不要担心我,担心你自己吧。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管好你和大卫的事情吧。
我和大卫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们交流有问题。
是有问题,因为我的英语先天不足。她突然开起玩笑。
妈咪,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们很好。
是吧?我轻快地应道,你和大卫最后一次的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她愣住了,脸唰地就红了,然后像被掐到要害的猫那样惨而无力地“呜”了一声。如果地上有条缝,她会一头钻进去的。她不可能这样问她的父母,中国子女不可能这样质问父母。她想这是谁对谁进行性教育啊?女儿给她扫了一次盲。她望着面前嚼口香糖的少女,这是谁家的女儿啊,该少女与她在音乐学院门口所期许的那个女儿完全没有重叠嘛。那天帕特捧着一束花来家里接我,正赶上他们都在家。妈妈对大卫小声嘀咕:这个孩子是谁呀?大卫说:他是海伦的同学。你不记得了吗?他曾经来过我们家。我妈妈点点头:我知道,我是说这个女孩子是谁呀?
天啊,你不觉得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开口性闭口性地十分下作吗?她说。她希望我成长为一个对自己对他人都知道羞耻二字的中国传统少女。一个女孩子不懂害羞是件糟糕的事情。
第十七章 现在应该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1)
大卫在他的书房睡了几天。
我妈妈和我站在书房门口,他正睡着,两只胳膊趴在书桌上,供着一个大头,耳朵贴着桌面,侧露出一张宣告战败的灰白的脸。耸起的肩膀显得格外大,是个温暖的肩膀,我的妈妈曾在那里安过家。外套滑到腰部。妈妈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迟疑了一会儿,她想自己是否要做这个讨好性的动作,她不愿意让大卫感觉她理亏或者有主动修好之嫌,但还是伸手将落下的外套披了回去。妈妈那双修长的手做起这个动作格外的温存。这个动作惊动了大卫,他的头从胳膊上落下,还碰倒了一本书。他没有去捡,连看一眼也不,而是一睁眼就去看他的太太,就像任何一个清晨一样。
当两个人一说话就会吵,而且还可能是用两种语言吵的时候,不说话最好。
站在门外的我温情地看着这对异国夫妇,心底第一次希望他们好好地过下去。我叹了口气,目光也悯然,何必呢,都这把年纪了。
他还是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的那笔钱做什么了,你不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我调查过了。眼晴却说:你看看你吧,一个好好的正派人逼急了也能跳墙。
妈妈并没有马上回应他的宣战,而是扭过脸对我说:你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我的妈妈像一场战争爆发前叫自己的亲人撤退、准备独自奋战的勇士。也许我错了,她是因为犯了错,不愿意让我知道才把我支开现常
大卫更直接地对我说:你可以回自己的房间吗?我想和你妈妈单独谈谈。
他们需要我离开,让他们自由地争吵。我扫了他们一眼,那种眼神的意思是:谁想听了?
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吵了什么,但是可以断定这笔钱的去向使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后来妈妈终于同意一起接受婚姻心理咨询,算是一种妥协,一种屈尊。他们两人做过一些尝试,说自己宁愿共同面对问题,而不是一个人什么也不面对;还说两人一起生活了这些年,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一点真情,没有一点值得挽回的,他们不会走这么久。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好转。
大卫并没有太多时间经营他的婚姻,因为杰生突然病了。病得很重,重到了什么地步,已经写在大卫的脸上了。大卫变得异常的细心与体贴,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变成初为人父的样子。面对一个无力表达自己不适的婴儿,他急于去掌握他的感受。杰生说不吃苹果,大卫也连忙说不吃不吃。对一个病孩子,父母总是特别谦让和宽容。杰生知道这是因为什么,甚至想一直病下去。这样,他就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了。除了这些古老的代沟,他从来没有怀疑父亲的爱。是父亲教他认星星,教他下棋;他记得他们为一场球赛争执不休,看着日落唱着《红河谷》。杰生的母亲用梳子一点一点整理他因病而脱落所剩不多的长发。这个女人总有得体的表达爱的方式。
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再次坐到一起。我妈妈也来看望过杰生多次,可每一次的看望都让她觉得自己多余。他们友好的目光恰恰让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多么多余。以后妈妈每次看望杰生都会拉上我,既然多余就再多余一个人吧。她大概这么认为。
三个月后,杰生哥哥死了,死于三藩市一片明媚的阳光之中。没有追思礼拜,只有一个小型聚会,婷婷也参加了。我轻轻地拉了拉婷婷淡漠的手,冰冷得寒心,那是一具多年前就冷却了青春的生命。她很少与我谈起杰生,也缄口不谈她的哲学。她是这么说的:哲学这东西能谈吗?有什么好谈的?好像能拿哲学怎么样似的。她知道她的哲学对于她的现实生活毫无帮助,有的只是障碍。
我们站在他的墓碑前,大卫伸手到西装内侧的口袋里去抽一个信封:这是杰生的遗言。杰生不想有葬礼,他说如果有的话,他就不出席了。
大家笑。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公共场合,他对一切的人视若无睹,隔着人丛向他孩子的母亲点点头。他让我们大家在同一时刻得到同一信息:他只关心她一个人的感受。她回报她孩子的父亲一个点头,表示她收到了他的关怀。这使他们之间的意会有了礼尚往来之感。我断定那意会是走火出来的。一个以他们孩子为中心的活动,他们拒绝不了那种情分。而那目光证明他们内心的交流从来没有间断过。大卫与我妈妈也时常有这种目光的交换,却交换不出这么多内容。
我妈妈当然也看到了,但是她优雅地不让别人看到她看到了。
轮到杰生的母亲致词。她一身黑色,经历各种颜色才懂得黑色。好像有这么一首诗:“黑色黑色,是美丽的颜色,当你失去一切,只有黑色,黑色是最美丽的颜色。”一直以来对外界事物的充耳不闻,及大智若愚的操守,终于使她有种超凡脱俗的纯真。几个月的病情她早已暗暗想到险处,现在不过是险情发生了。她说她还保持着打电话给儿子的习惯动作,拿起电话才想起他死了。说着就泣不成声了,这位悲伤过度的母亲当场就晕倒了。
大卫一个大跨步过去扶起他孩子的母亲。他带着侠气的营救,搭配上她离群寡合的古典美貌形成了一幅英雄救美的画面。人群中有声音说:她是不是需要一些水?后来我才分辨出那是我妈妈的声音。大卫说:相信我,现在水是她最后一件需要的东西。她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他右手支撑她的身体,左手除下自己的大衣,过右臂时,他换左手去扶她,右手除衣。然后将脱下的大衣披在她身上。动作不动声色的淡泊和流畅说明那习惯成自然的相知相识。他太太就在他的怀里安稳地躺了会儿,一切并不陌生。
我用“他太太”这个词了吗?哦,这是我当时的感受。也是我们大家的感受。
她微微好了一点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看了我妈妈一眼,隐约的歉意。她不是那种不懂得场合与人情世故的女人。她挣扎出大卫的怀抱,想把大卫还给我妈妈。
我妈妈只装着看不懂那一眼,轻轻地把大卫往他前妻那一推:你最好先把她送回家。
大卫就站在他旧爱新欢的中间地带,等待着她们任何一方的进一步明确。
这里有我。我妈妈又说。
大卫对妈妈感激地点点头,这是全场他与妈妈惟一的一次交流,然后就扶着他孩子的母亲上了车。
大家给他们让道。披着大卫外套的她一直回头看我妈妈,她想知道一切是否妥当。
众人尽量当它没发生过,一派抽象的和睦。妈妈仍然对一些人进行安慰,也被一些人安慰着,只是这安慰中多了一层意味,他们说话时往往低头看自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