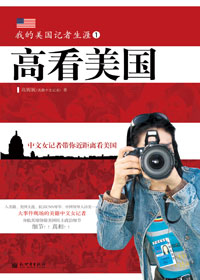美国旅店-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对异国夫妻,尽管来自两个最善于理财的民族,两人脸上都有一股子要改变原本生活状况并且要为此付出努力的精明,还是对对方异于自己的金钱观念拿不出一个合适的态度来。
首先大卫很吃惊他太太的勤俭。 比如他以前每一两个星期看一部电影,现在他太太用录像带取而代之。 比如他太太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减价出售的机会,总是耐心地剪下大小报纸的减价卷。这个勤于家庭建设的上海女人比他这个犹太人还精打细算,将他那点菲薄的教授收入打理出相当不错的日子。他们付清了房屋贷款,而且打算另外购置一栋房子,用来出租。这些年下来,大卫好不容易才明白:他太太需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看得到的地方。
更让他奇怪的是:在他看来,这个只要一撮米和一点酱油就能没有怨言地活下去的中国女人,会突然为了宴请宾客铺张浪费地大摆酒席;会突然为一个派对买一件上千元的名牌大衣。去年他们决定把他的车给海伦开,他再购置一部新车,他太太立刻翻开帐本,盘算了一会儿说这次要买奔驰。他说有这个必要吗?她笑:节约就是为了可以奢侈。他想:她到底是个中国人,可以在节约与奢侈之间达到如此并行不悖的统一。
可是现在他再次糊涂了:这笔钱怎么就突然看不见了,连个打水漂的声音都没有。他实在想像不出这个女人有能力突然开销这么一笔钱在一处看不见也听不着的地方。
我妈妈也很奇怪:中国人讲的“非淡泊无以明志”和“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在大卫身上一点也不奏效。大卫孜孜不倦地追求纯学术的精神世界,过着近乎于僵化刻板的生活,可这并不妨碍他对另外一个极端——金钱的务实且精明的态度,他对家里每一笔钱的分配、去向与目的毫不含糊。她想:他到底是个犹太人,可以将代表精神和物质两个极端的学术和金钱并行不悖地统一起来。
两人一直以来对彼此的金钱观抱着存异求同、殊途同归的思想,今天终于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再问一遍这笔钱去哪里了?我想我有这个权利知道吧。他蓝灰色的眼睛一抖,抖出了一股子气短:我有吗?
对不起。我妈妈面对如此大的气势,站起来缓解道。
我不需要道歉,我需要一个解释。
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想好,也许什么也不做,只是存一笔私房钱。妈妈连忙为这场战争降级。她大概是这样想的:钱用到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钱不见了。
而大卫却为这个真正地生气起来。他声音沙哑颤抖道:操你。大卫只有在公路上被人无缘无故地按喇叭或者被人冷不防超车时才会脱口而出的脏话出现在客厅里,他自己都料不到。显然他把我妈妈的强词夺理当做公路上毫无秩序的蛮横超车,甚至更甚。
先来看我妈妈,垂着手,端着肩,背景是一片深蓝色的丝绒窗帘。像一个被丢入大海的孩子,她的表情相当无辜——像一个孩子做错了事却全然不知。但我得说,她是不天真的,是女人对作为女人的便利的了如指掌而来的狡猾。
太太存点私房钱在中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妈妈突然为自己辩解了这么一句。
第十五章 太太存点私房钱在中国没什么的(2)
在我看来,就是很大的事。大卫的声音依然沙哑。
再来看看大卫,仿佛倒退了几十年,儿童被欺负被出卖的时候才有的神情,儿童的无助与委屈竟然来路不明地挂在这位体面尊严的男人脸上。他的头发发白,唇色泛白,乃至肤色灰白。一片暮年的黯淡。我想起了我爸爸,原来男人在遭受背叛时会如此相似。
你们老外有时候是很奇怪的。
大卫不是第一次听到他的中国太太管他叫“老外”,许多时候他会耸耸肩跟着喊自己一声老外,那动作是相当凑趣的。随后他的中国太太就会半嗔半娇地嗲过去一眼,那一眼是相当妩媚的。现在他第一次觉得这么别扭,还有轻度的受辱。他字正腔圆地纠正他的太太:你们中国人在美国,就应该学会和尊重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妈妈听到的是一股子的优越感,这是大卫从不轻易流露的。不轻易是他的教养——也正是他的优越。
他们不记得有多少这样的时刻:她的黑眼睛和他的蓝眼睛相遇,像是从来不认识。一两句话所冒出的差异,将他们之间无数次的亲密接触化为乌有。
她的黑眼睛猛然地杀出一道锋利:我希望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他的蓝眼睛坚决地挡住了这道锋利: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听出了较量。像两头斗牛,互相征服着,也互相讨好着。他们仍然希望对方先退一步,那样他们就放过对方了。
你想怎么样?她说。
我想怎么样?他说,我想这样。
大卫抖着帐本,鼻翼翕动,歇斯底里地当着我妈妈的面将它撕成碎条。不是两只手一起撕,而是一只手固定着,由另一只手启动“撕”这个动作。从母体上一条一条消灭。然后揉成一团,向我妈妈那边砸去。一个标准的砸的动作,手臂从他的腰部出发,经过头顶,迅速地将纸团向我妈妈砸去。纸团的抛物线与地面形成一张弓,却由于极端的气愤,动作无法到位,纸团经过那只手漂亮弧度的漫长旅程,在他面前两米处就提早降落了,气息奄奄地落在他面前。他冲上前,踢了那纸团一脚,终于把它踢到我妈妈的面前。
如此一系列的动作将他的气愤推上高潮。足够的鲁莽,足够的气魄。
我妈妈并不吃惊,他会这么做的,六年前他就曾经这样撕过他儿子的贺卡。她没有去捡,连低头看一眼也不,却回头看我,焦急地寻找支持。她那么明确地向我投来一个需要助威的眼神。
十二岁来美国的小女孩一直希望有个机会递上这种助威的目光。这一刻,我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我一直装着一个小心思:那就是希望他们吵架,然后让她想起我爸爸的种种好,知道离开我爸爸是多么大的错误。这个心思太隐蔽了,甚至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有了机会,却递不出那种目光。
这算是高潮了。他们都安静下来,他们感觉有这个必要。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小心避开心头对对方的追究,必须沉默,必须避开,否则场面就会失控。
大卫说道: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专业辅导。
大卫以前看过心理医生。我妈妈虽然也承认真实地暴露自己有利于对自身性格的了解,但她骨子里根本就瞧不起那玩意儿。她是用“瞧不起”这个词的,由于经历丰富而来的优越感,从而产生对一切肤浅事物固有的轻蔑。他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无法探知的心路历程远不是美国心理医生所能理解的,更谈不上治疗。后来大卫说,你经历那么多,都没看心理医生,我也不需要看了。今天大卫重新感觉自己及他的太太都有严重的被矫正的需要。
我妈妈问:你认为那有用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不要问我问你自己。
这次恐怕我们想到一块儿了。她说。
他点点头:真要到这步吗?
我知道离婚这个念头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在他们心头起着涟漪。他们都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当然谁骗了谁,他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他感觉自己从这个女人单枪匹马闯进他办公室开始,就步步走入她的圈套。是她在诱惑他,是性骚扰。她一直在利用他,她从来没有爱过他。而她才觉得冤呢。不是吗?一个女留学生,面临生活绝境,他是她的上司,小小的要挟,微微的强迫,以一份廉价的奖学金换取了她整个身心。性侵犯。这是实质。
上当了,他们想。婚姻本来就是上了爱情的当。他们有些不甘心。
他离开现场回到书房。这时他发现了我,明白我全听见了。大卫皱起眉头,急急地看了我一眼,深凹的眼眶里疑云难消。他耸耸肩,首次将这个典型的美国动作做得十分无奈,像是讨教,含糊地带过一句什么:我就是不明白。声音很小,像说给我听的,更像说给他自己听的。
我运动着嘴巴,却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用力嚼口香糖。不支持任何一方。
妈妈后脚到我的面前,她的目光比大卫复杂多了:验证、核对、索求,是向同类要求答案。她的声音也比大卫清楚多了,她说:我没做什么呀?女人存点私房钱这在中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的,对吗?在中国。
我还是没有说话。我不参与他们的战争。
妈妈又用上海话说:对勿对?侬晓得格。一用家乡话,似乎隐藏着更深的含义,期望也更迫切。
我对她期望的答复是吹出一个大泡泡,同时拿英语懒洋洋地说了一句“不关我的”——这时将泡泡“啪”地咬碎——“事”,于是这个词特别响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中立态度明明白白地告诉她。
妈妈盯着她的女儿看。
我把自己裹在过大的硬而挺的牛仔装里,像一颗小糖果。肩部开到小臂,裤腰开到小腹,裤档开到膝盖,全部都向下耷拉着。肥大的裤子露出半截内裤。还有酷野的手镯和挂链钱包。高中生就是喜欢那种码号上十分夸张的衣服,我们班的几十个同学不分男女全是这种酷样。每个少年都分承了别人,从形态到思想。十分青春的五官也是同样十分消极地耷拉着。目光是那种高中生特有的轻蔑,对自己对全人类的轻蔑。嘴唇上像挂着千年老锁,好不容易开了锁,也是那种电报式的短语。
她复杂的目光一下子单纯了,没有指望的单纯。我至今还记得我妈妈目光中的那种单纯。她早我一步意识到这个少女的没有准则。这个十二岁就来美国的中国小女人并不权威,也已经不那么中国了。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沉重地吁了口气,像是对一个没出息的孩子指望不上了似的,心酸到了极点。她能怪谁,是她把一个青涩的中国小女孩变成一个麻辣的美国少女。她转身离去。
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吵架制造出的硝烟弥漫的现常我站在他们所处的位置的中间,看着这团纸团和它的碎条。我打开,就像当年打开爸爸扔进垃圾桶里的信。我看到妈妈的私人存折:一笔突然消失了的数目。然后揉好放回原本的位置,就像将爸爸的书信重新扔回垃圾桶一样,就像小偷行窃之后将现场恢复。厚实的乳白色地毯,丝绒窗帘质地沉稳,水晶吊灯,恢复了一个安宁家庭的常貌。
只是那张长沙发的皮革扶手添了几道指甲的划痕,是我妈妈窘迫的手留下的。
第十六章 我们要讨论一下性这个话题了(1)
他们第一次分房睡。大卫没有回卧室,住进了他的书房。接下来的几天非常滑稽。三个人谁也不和谁说话。在庞大的红木餐桌上,大卫突然冒出句:麻烦把番茄汁递一下。两个肃静进食的女人的头抬起,心想大卫是不是有和好的意思呀?我妈妈正想把她前面的番茄汁递给他。大卫把头一转冲我道:拜托了,海伦。我妈妈看了他一眼,把手上的番茄汁放回原处。一言不发的中国少女伸长个手臂去拿,再伸长个手臂递给大卫。大卫感觉自己这些年对这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