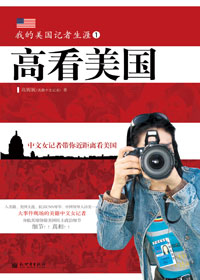美国旅店-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经微微张开微微撮起,像所有的婴儿一样本能地期盼,下嘴唇留有门牙轧过的齿樱她的乳房与我的嘴唇是一对绝配,它们之间关系暧昧。
这样舒服了吧。她说。
那脚突然就像挣脱开笼子的鸟一样,扑腾扑腾地想飞。我将两个脚底对拍了一下,又让十个小脚丫张牙舞爪一番。然后仰着躺下,她也在我旁边仰着躺下。凭借她身上的气息我能感知她的距离。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搭在我身上。
她的手也只是放着,没有动静,在探视我的反应。她显得比机场紧张。在机场更像是即兴表演,出点错也没人计较,乱乱的,大家都来不及理会。现在就剩下我和她,一点错就异常明显。我能察觉到那手紧张而兴奋,我也同样,我在她的手下一动不动。一种久违了的感觉,一时不知道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由于我的顺从,她的手在我的手上摩挲。
我有一对漂亮的手,她也有。手指修长的人喜欢幻想,比如我,比如她。她在许多年前一个黄昏,经过音乐学院,琴声轻盈荡来。可以感觉到它是潜伏过琴房、走廊、楼梯和广场飘然而至,于是就飘出一份路途跋涉的不易与红杏出墙的诱惑。什么曲子来的,她记不得了。好像是《少女的祈祷》,又好像是《小夜曲》,也可能是当时流行的歌曲。记忆往往就是由于不确定而变得美好,可以恣意想像。她想像她坐在一架三角琴后面,音乐、长裙和情感丰富的心灵。她想要成为钢琴后面那个高雅骄傲的女人。许多年后,她想她的女儿要成为高雅骄傲的女人,音乐、长裙和情感丰富的心灵。
小歌,还记得你小时候的事情吗?我们带你去听音乐会,你看见钢琴家在弹琴,就对我们说你也要弹琴。我就对你讲邓肯学舞的故事。邓肯小时候看见别人表演舞蹈,对她妈妈说她也要跳舞。她妈妈说,要跳成这样,需要付出许多,要流许多汗,吃许多苦,而且你就不能常常见到妈妈了。邓肯说,妈妈,如果成功要付出这些,那么我们也只能选择了。我跟你讲完这个故事后也对你说,要想弹成那样,需要付出许多,要流许多汗,吃许多苦。我希望你能像邓肯那样回答,说你不怕吃苦。可你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吗?
我沉默着。
你的回答和邓肯正好相反。你对妈妈说,这样苦,那我们就算了吧。
她笑。她的手顺势上移,抚摸我的胳膊。又抚摸我一捧浓密的头发。
我有一个光洁的额头,她也有。高高的,裸露的,拒绝刘海来掩盖它的傲气。目的明确地让人看见额头中心的一个三角,就是俗称“美人际”的东西。让那些需要用额发来掩饰的额头,自惭形秽。还有茂密的头发。她笑了,头发不能用茂密,树林才能用茂密。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头发就是茂密的。她也一样,茂密的头发。
后来呀,我们带你去少年宫找老师,老师要每个小朋友都说自己学琴的目的。一个小朋友说,她想成为钢琴家。另一个小朋友说我妈妈说我长得不够漂亮,学好了钢琴,将来才可能嫁给有钱的老公。轮到你说,你知道你说什么吗?你说问我妈妈吧,我只是陪她来的。三个月后钢琴老师对我说,你进步得比你女儿快。你瞧,倒真成了你妈妈在学琴了。
她又笑了。她喜欢现在的气氛。你知道吗?你记得吗?你那时候呀,她一下子成了“鞠萍姐姐”,嗯呀嗯呀的语气语调,像对待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其实她是希望我也能把她当作六岁女孩的母亲来对待。
我翻了个身,她也跟着翻了个身,我们两个合体得就像大勺子和小勺子搭在一起。她的手也因为轻松下来的心情更加大胆。
她在抚摸童年的我。
那个小女孩喜欢听她讲大灰狼的故事,吓得直往她怀里钻。喜欢被她抚摸,主动要求她哄她睡觉,喜欢她身上的味道。那时小女孩还是个快乐的孩子,从她一别六年的背影中,从爸爸因为狠狠喝酒而变得通红的脸上,从小朋友“没有妈的孩子”的讥笑声中,这个小女孩一点一点地学会了憎恨。学会憎恨,自然与快乐无缘。她知道,大灰狼骗了小红帽,而她也骗了她。
十二岁女孩子略黑的手臂阴凉,青春期的皮肤突显出敏感,细微地挣扎。几个月前学校要表演天鹅舞,舞蹈老师过来给我们束腰,她的手刚碰到我的腰,我就如同触电似的又笑又跳。老师那种对孤儿怜爱的目光立刻就绪,她扶住我的胳膊说,没有妈妈在身边,没有妈妈抱,才特别敏感。我甩开她的手。我只是怕痒。我一边叫一边跑开。老师在我背后不解:她的学生应该感动的,应该顺势往她怀里一扑,怎么跑掉了?!
我意识不到肌肤的饥饿感,直到现在。孩子,尤其女孩子多么需要母亲的爱抚,那爱抚不是别人可以代替的,女性的,母亲的。她的手像水母伸出的触角,所有的情感借着触须一起伸展出来。她的手像闪电一样击中我,一阵阵电流从全身通过,皮肤的每一个细胞如惊弓之鸟飞了起来。又像是一张宣纸被涨满墨的毛笔轻轻一触即溃四处溢去。
她抚摸的是童年的我,不是现在的我。
我的胳膊蠕动了一下。含羞草似的不安起来,除了紧张,还有点不自然,并没有从如此的抚摸中借到一层亲近。我和她接触是天生的。我曾从她的最隐秘处而来。她的抚摸立刻停止了,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触角试探受到刺激马上退缩回去。她也十分敏感,回到初为人母的时候,需要从孩子鼻翼的张合之间判断孩子的感受。
我们都感到别扭,却不能承认。
我打了个哈欠,但她拒绝接受这个暗示。
她没有马上离开,她意识到我还是不肯叫“妈妈”,从她上次回国到现在我不曾松口叫她一声妈妈。又觉得我们的谈话不太愉快。她看了我一眼说: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飞机,一定累了,你先休息吧。然后离开了。
第二章 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1)
我并不知道妈妈趁我熟睡期间,站在门外凝视着她的女儿:小歌散乱的头发和无知觉的几个动作,比如拉扯一下被子,比如翻个身什么的。她通过我呼吸的频率揣测我睡眠的深浅。她见这个呼吸保持了好一会儿,知道我进入了孩子无知觉的熟睡状态,才离开。可妈妈离开不多久,我就醒了,感觉到下身一阵的不适。
到美国的第一个晚上我来了例假,感觉自己像在少年宫琴房后面的库房里,四周是各种的管弦乐器,手忙脚乱中撞出不和谐的鲁莽的声音。 爸爸一定预感到了,我眉宇间细微的躲闪,那种已经不再完全无所顾忌的眼神让他有所顾忌起来。他看出一个隐约的大姑娘的影子,意识到他的父爱不足够应付我的成长,对自己这份监护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他把我交给我妈妈。
那么我就应该去找妈妈。他们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头。门并没有完全地合上,门外的我影绰地可以看见她和大卫躺在床上说话。我没有马上敲门进去,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没有说我什么,可是听不懂,只听懂“小歌”什么的。之后是低低的昵语声;再之后,竟是异样的喘息和呻吟……
小时候,半夜爸爸会与以为熟睡了的、躺在他们中间的女儿换个位置。这个小东西虽然不知道父母在做些什么,却对这场把她排除在外的活动极为不满,亦明显感觉到它的神秘。这个小东西把自己作为绊脚石,一次次地摔下床铺打搅情意绵绵中的父母。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把这个不小心跌落的女儿抱回床上。心里又心痛又紧张,还有点被败兴的恼火:我们没有占太大地方吧?我们没有发出太大动静吧?这孩子怎么就掉下去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报复。她是故意的。我知道。大人不愿意也不敢承认孩子是有性感知的。大人害怕。大人比孩子还害怕去承认它。这一点当然是我成年后才意识到的,于是我不得不怀疑孩子天真的真诚度。 白天我眨着再天真不过的黑眼睛问他们我是怎么来的,这是他们愿意听到的问题。你是捡来的。他们挤眉弄眼无比安慰地笑着回答我。他们以为安全了。晚上他们就表演给我看我是怎么来的。
现在,这个跌落床下的小东西已经是一个稍晓人事的青春期少女,对于她妈妈与这个男人将要进行的活动更多的是憎恶。妈妈将她和爸爸丢下跑到美国,与一个不是她爸爸的男人做这种事情?!她首先是我的母亲,不是别的。我无法想像她在别的男人怀里的情景,那股女人的香味,被一个外人这样闻去。她没有我期望的挣扎,现在可能还因为这个白人丈夫对她女儿的接受,她迎合得更加彻底。
恨意就这样冲出来,我不能原谅妈妈。也有人给爸爸介绍对象,爸爸总说过几年吧,等这个孩子大了再说。 爸爸担心我会受后妈的气。谁对我更好,一下子就比较出来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最后那一点的主权也不留给她。
我能看见那个初来乍到的小姑娘如何收起自己细长的手脚缩在床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 白色的月亮,一团冷气从上而来,有着一种高处不胜的寒冷。那清冷是月亮的灵魂。这是嫦娥偷吃了后羿的长生不老药时看见的月亮,她最终是去月亮上。月亮照在白色的连衣裙上,新买的。我走的那一天爸爸要我穿上。
我不要穿这件。
为什么?
其实我是拒绝最后一点体己的拘束与害羞也招摇出来,而白色的公主裙显然是童年一切招摇的最大嫌疑。当然这是我今天的总结,那时还认识不到本质。一个十二岁女孩子的语言只能表达成这样:因为我穿起来会太可爱了,会有许多人看我。
爸爸禁不住笑起来,看着小姑娘臭美。他问:你不是最喜欢白色吗?
是我妈妈喜欢白色。我提醒他。
白色公主裙还是套到身上,身体与服装彼此反叛,尤其胸部一直不满这套还属于儿童专柜买的服装的窄小空间的约束。成长发育的女孩子面临着危机,爸爸就在这一刻有了意会。
快要出门的时候,他又说:小歌,你的头发乱了,爸爸再给你梳一下。我坐在镜子前,最后一次享受爸爸日趋成熟的手艺,对于女儿来说,那是奢侈的享受。 爸爸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爸爸从来不说软绵绵的话,而这一刻,他却把爱表达得如此温暖体贴。我就这样带着爸爸的爱来到美国,开始人生的新的征程。
我们在机场重复着六年前妈妈出国的那一幕。只是那个六岁的宋歌,只知道一味地抢妈妈的行李,一味地叫喊妈妈不要去美国。而十二岁的宋歌像所有那个年纪的孩子一样,热衷于摘抄好词好句,喜欢用最学生腔最文艺腔的语言表达自己。我对爸爸他们说:我会有出息的。等我们再见面时,你们猜不出我会变得有多好。
爸爸巨大的左手像一只芭蕉叶一样按在我的肩头,重复着老话题,想另开话题,又怕一时半会儿收不回来,所以就只能这样随着本来的话题一遍一遍重复着:小歌,到了美国要听妈妈的话,要记住给爸爸写信。有什么事情告诉妈妈,不要自己闷着不说话。接着交待空姐把我平安地交到我妈妈手里,当然这话也重复了许多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