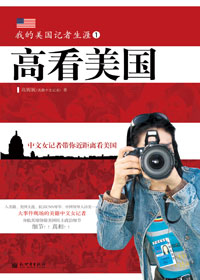美国旅店-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还没有吸毒。
你敢?!
你不要逼我哦,不然我明天就去吸毒去。
她果真不敢再逼我了。她知道我的一身反骨远超出她的认识。
世界上任何东西也许都可以通过欺骗获得,只有一种东西是无法欺骗的,那就是知识。她一下子成了“中央新闻”,字正腔圆,抑扬顿挫。
我沉默片刻。
读书不是为了老师,不是为了父母,是为了你自己。你作弊到底是在骗自己还是骗别人?是你自己。
仍然沉默。
你知道cheating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你背着我爸爸干的就叫cheating。我激动地说,像堵了好累的污水终于找到泄口,又像一把迟迟不肯亮相的暗器,在最关键的时刻亮了出来。我的英语就是为了这个不备而来。
妈妈连忙斜过身子看我,呆了一下,是与米雪小姐同一种的吃惊。她才发现我的英语程度远比她认为的要高。我已经能将这个cheat活学活用了。cheat,破坏规则、作弊出猫、欺诈哄骗。这个词还是英语生动利索些。考试作弊是cheat,感情中的不忠诚也是cheat。它将出轨者那点侥幸、卑屈和玩弄公之于众。
我要回家。我叫。
你正在回家。她也叫。
我要回自己的家,回上海的家。我说罢就去打车门,妈妈迅速地把车门锁了。
我要下车。我提高嗓门说。
你哪里也去不了。她的嗓门比我更大。
妈咪——我突然大叫。
闭嘴吧。
妈咪——车。
一辆面包车已经冲了过来。
我无力描述那场车祸,只能用一系列的字眼概括:血、救护车、鸣叫,交通混乱。他们并不一定是按照此排列顺序发生,有些是瞬间同时发生的,有些则有前后。我们被送到了医院。我无大碍,妈妈失去了她的孩子。她额头飘着散发,嘴巴半张,发出走调的呻吟。一见我,像是等待我去营救似的大张双臂。妈妈弱小极了,需要我在她身边壮大声势。小歌啊,你妹妹没了。你不能再走了。
我正在犹豫,一回头就看见她的脸出现垂死的老母鸡那种哀态:悲伤的目光从美丽的眼睛里流淌出来,身体也如同受伤的母鸡那样微微地抖缩。十一岁那年妈妈回国,也是用这种目光望着我爸爸,让爸爸不痛快却心甘情愿地让我去美国。
如果说我还无法从她的表情判断出她的真诚,那么她的手绝对是真诚的。妈妈握住我的手,随之在我手心做了一个极为轻微的细节性动作:用手指在我的手心上施了点力,很轻,却有一股内在的力量从她体内传递出来,而我要的理由她也传递给了我。与六年前机场的分别相反,她不是甩开我的手,而是握得更紧了。六岁那年被妈妈松开手去,就已经注定我对手的表达格外敏感。
越是惊天动地的事件,越是过眼烟云,记住的往往就是这么一个细微的动作。它被珍贵地保藏下来,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它的力度与它留在我手心的感觉。就是这微不足道的动作让我改变了主意,我没有回国。我真正见到爸爸是在五年后,高中的最后一年。
突然我们母女二人很悲壮地拥抱在一块,成为没有彼此的一体。在对方的怀里才知道两个身体是那么的合体,那么的贴身。
第十二章 你背着我爸爸干的就叫cheating(2)
大卫插在我们中间,拱手让出主角的位置,看这对母女怎么可以风风火火地战争,现在怎么又胡里胡涂地和好。先是自相搏斗,现在又互舔伤口。怀孕又流产整件事好像与他无关一样,而成了这两母女的事情。他夹在中间,不是感觉自己失落尴尬,而是自觉碍事,似乎妨碍到了我们什么。他站在一旁,踱着方步。步子越跨越大,自责也越来越真切。
我和继父的关系也是从那以后开始改变的。我的意思是我和他本来没有关系,是通过我妈妈才有了关系。我们主要是通过共同享用我妈妈做的所谓的中西合璧的晚餐,穿着同样烙下我妈妈不贤惠痕迹的一排扣子的睡衣,来了解对方的。那以后我开始真正地了解他,而且接受他。
我站在他的书房门口。
灯光将他从黑夜中勾勒出来,就这样,明暗二色。灯光照亮了他因为秃而呈嫩红色的头顶。他的面部就像纸头像,不是公园里花几块钱三下五除二剪出的一个轮廓粗糙、面貌模糊的纸人,而是神秘的中国民间艺术家的杰作:线条清晰、眉眼鲜明。由于没有语言交流的管道,他的举止行为成为另一种交流。他那没有完全张开就合上了的双臂,跟在我妈妈后面伸出的随时准备帮忙的双手,端着饼干盒站立在我房门口的样子都是一幅幅极生动的剪影,且独立存在。它们尺度的分寸感与动作的艺术性,巧夺天工。那是语言之前的语言——它耐人寻味又不乏最基本的表达。
大卫的形象理应更深刻,妈妈的丈夫对于我不可能仅仅是几幅剪影,但我几次都扭扭头把目光移开,总用打哈欠瞪眼睛面对他,不愿加强他的形象。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大卫长得不难看,梳着循规蹈矩的偏分,眼睛凹陷,越发衬出那管标志性的大鼻子。他与我爸爸非常不同。我爸爸是个天生的孩子,而他是个永远的老人。那般的睿智,端庄典雅。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还不能对这个对比给予更多、更准确的解说,在今后六年同一屋檐下的朝夕相处中,我会给予它更多的观察,直到可以完全诉诸言词。
我冲大卫笑了笑。大卫也很高兴地对我笑了笑。
其实大人很喜欢对他们友好的孩子。大人认为孩子拥有比自己纯净的心,来自孩子的友好就是一种获胜。越是成年,与世界有越多的接触,越是希望赢得孩子的好感。当然这一点是我成年后才发现的,孩子意识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意识不到,这种友好显得尤其珍贵,而且神秘,带有某种不可探知的仲裁。
我叫了他一声:犹太爸爸大鼻子汉堡包。那是种孩子式的戏耍,要惹大人生气,也要惹大人高兴,总之注意到孩子就行了。
他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想起那句“我庆幸自己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儿”,对我抱歉地笑笑。他想这个小女孩再怎么反叛,也没有反叛到喜欢女孩子埃他的身子倾出书桌,他的目光也倾出眼眶,那是一个邀请:让我进他的书房。
一排排的书规矩地立在书架上,书桌上躺着几本常用的资料书。其中一本字典翻了又翻,受过潮,又被岁月一点点地烘干,渗下一条条土黄色的印子。纸张膨松,两片深红色的硬皮封面如何也裹不住臃肿的身躯,索性随它春光外泄。这些书或站或躺都像战士,守卫保护着他们的国王大卫。这里是一堆有气息的知识学问。
你有很多书哩。你都读过吗?我指指书架。
哦,它们只是装饰品,为了让客人有个好印象的。我从来不读。只有无趣的人才读它们。
我笑了,他也跟着笑起来。
你喜欢读书吗?
我点点头。我想先应下来,以后可以慢慢喜欢。
他突然有点讨好地说:如果你喜欢,将来这些书都可以是你的,我的孩子。
现在回想,我知道自己的心是在这一刻被牵动了。这个失去两个孩子的父亲想以他的全部财富换取一点好感与亲情,就像愿意拿全部玩具去换取一点友谊的儿童,那般的无助与可怜巴巴。
喜欢读书好呀。他试探性地轻微地拍了一下小女孩的头,知道这次是被允许的,才施了力上去。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呻吟道。小女孩知道自己做了某种顶替。他看她的目光是那么慈爱,她却看不到自己,看到的只是他不在场的儿子。然而他带有乞讨性的慈祥已经让小女孩不忍把头收回来。女孩子甚至有点怜悯地想,就让他拍拍吧。
他也感觉到这种亲情的可疑。他感谢小女孩没有揭穿,没有像她妈妈那样跟在他后面大声唠叨: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给你儿子打电话吧。他感谢这一切。
他问我读过哪些美国作品,喜欢谁。
我说我在中国时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当然是中文版的。我喜欢J·D·塞林格。
他是犹太人。大卫冒出这么一句。
大卫的犹太特性早被我刺激出来了,现在只是找到了一个入口。接着他告诉我美国几位著名的犹太作家,辛格、贝娄等等,他说,他们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都是犹太人。他又告诉我犹太人获诺贝尔奖的比例是世界其他民族的二十八倍。支配当今世界思想的有三位是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依德。再接着他就说起法西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而犹太人却从中学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自强不息。
这时他看见他面前的瘦小女孩,两眼大瞪,目光茫然、不解,还有点莫名其妙——好像在说这个大人在说什么呀?就是在饭桌上面对他的发言我最常见的表情。他知道自己讲多了,也深了。他感到对牛弹琴般的无趣,但是他并不遗憾,因为他尽了责任和义务。
大卫需要我在现场去进行这么一场演讲。他需要观众,然后进入无人之境。他忘乎所以,他只管他自己,自娱自乐。而他又会因此而受挫。因为他太把观众当回事,所以常对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不自信,一不自信就陷入冷场的窘境。
正当他挫伤之时,那个小女孩眨了一下她的黑眼睛,说:那个著名的作家海伦呢?她也是犹太人吗?
他笑了,刚才的失意一扫而光:她的继父是犹太人呀。
我冲他做鬼脸。
他一本正经地说:人人都是犹太人,只是他们不知道。
我是后来才知道这是马拉默德的名句。大卫欺负我年幼无知,随便摘抄名人名句,而且不说出处,长大后,读了书长了见识,我大有上当的感觉。
他说我现在应该读一些英文书籍。他站了起来,到书架前面,想找一本适合我读的书。他的目光扫视着一排排士兵的面孔,粗而短的手指划过一排排士兵的肩,就像元首阅兵。思考的时候就把圆圆的食指按在滚圆的鼻头上。
第十二章 你背着我爸爸干的就叫cheating(3)
他挑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写的童话故事。我最欣赏的他的作品都与他儿子有关。这本是他为他儿子的出世写的,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很难想像这样沉静的男人会写童话,而且写得有模有样,带有声音——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闯入一家乐器行东击西撞出的各种声音。后来他又为他儿子的死写了一本书。六年后,杰生病逝,大卫悲痛欲绝,文字成了他惟一的寄托,字里行间无不是对儿子的思念。我读过,一本非常深情的小说。
我捧着他写的童话故事:真的是你写的吗?他点点头。哇呜。哇呜什么我也不清楚,只是一个孩子没有思索的激动。他笑笑,有些感动,让他感动的也正是一个孩子不假思索的激动。我是一个教授,同时也是一个作家;我教书,同时也写书。哇呜,我又叫,再次没有思索。他又感动了一下。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作家从来都是叫人兴奋的。我是一直到现在才知道作家是这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