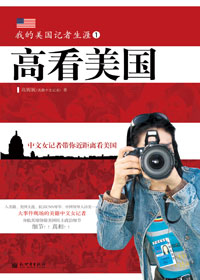美国旅店-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于感激——她是这么认为的,她说想请他吃顿便饭,他也欣然答应了。两人先是随便地谈起系里的各种纷争,她突然说,你想看我女儿的照片吗?我的荣幸,他接过她递过来的照片,嗯,她真漂亮,她的漂亮显然继承了你。谢谢,其实她更像我丈夫。总听你说你女儿,却从来没有听你提起你的婚姻。她苦笑:孩子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而婚姻不是,尤其是坏的婚姻,常常让人无话可说。那你呢?他认真地想了一下:应该说我的婚姻是不错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不过好的婚姻同样无话可说。好的婚姻都很安静。他不知道他已经开始抱怨自己的婚姻了。他说完,借故上洗手间,其实是给他温柔的太太打了个电话:亲爱的,我需要开一个会,不回家吃饭了。
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婚姻,两个人同属于文学青年。忧伤的时候,像阿尔芒对玛丽特说:当你的泪落到了我的手上,我立刻就爱上了你。激动的时候,歌德的《迷娘》就是好的表达了:你可知道那柠檬花开的地方,黯绿的密叶中映着橘橙金黄,怡荡的长风起自蔚蓝的天上,还有那长春幽静和月桂轩昂。总之,都是一些学生腔的爱情,抒情、文艺味十足。 彼此不知不觉像一副齿轮按部就班地旋转,直到有一天,一方觉得乏味了,不转了,另一方想转也转不了。我想就是我妈妈单枪匹马闯办公室的那一天。兴致尽了。这段婚姻完美而乏味。
吃完饭,他送她回家。她突然想这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男人,如果将来女儿过来,他会是个尽职的继父。一想完,自己也吓了一跳:你想得太多了,韩文琴。她请他上来坐一下。两人再次被置于单独的空间,想找一些话来说,竟找不到。于是两人将自己做为话题交给对方,墙上的两个影子越来越紧,紧到任何话都是障碍。这些吻还是比较纯洁的,轻轻的动情的,甚至掺一点儿羞耻。而羞耻感却最容易让肉体欲望膨胀。再后来就吻得不那么纯洁了,两个都使上了一股劲儿要将对方掏空。 彼此摸索起来,寻到一处,出现了片刻的迟疑,迟疑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这个年纪这个场合一切不需要太多的过场,一切好像是瓜熟蒂落。他走后,她才恍然大悟:这一顿饭怎么吃出这么多花样了。
这一天系里每周一次的教学会议上,她一下子就找到了他的眼睛,他隔着所有的人群,向她笑了笑。有了私情的眼神就是不一样。会后,两人有闲聊的机会。他说昨天晚上在沙发上没睡好。她没有问“为什么睡沙发啊?是不是和太太吵架了,因为我吗?”,她不这么问。她说:那今天早点休息吧。他心里一团乌云,乌得像隔夜的墨汁,让他看不到半点希望。是的,今天我要早点回家了。她又说:今晚你不来了吗?
两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他进前一步,她就退后两步,他想放弃了后退一步,她倒上前了一步,不让他断了希望。两人这样一进一退地维持着关系,以为可攻可守了,不想却是进退两难的尴尬。她性格中的冷静、坚韧甚至隐约的伤痛都被披上了异国情调的神秘面纱。对他来说,她就像那个精致易碎的景德镇出的小瓷人,明明知道它碎不了,却不得不随时防备着。这种患得患失的爱情让他觉得年轻,玩得起,像个小伙子。于是他的爱情有了分量和实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富足让生活单调,活跃的激情就剩下爱情和欲念。他心里一片温存的遗憾:他要怎么样她才明白他的用心良苦呢?他决定明说了。
那天他们看了一场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多段的咏叹调,他的手轻轻地在腿上打着拍子。他显然是一个对生活对未来还有信心的人。她想。接下来的晚餐点了烛光。Master信用卡广告做的那种:烛光晚餐2!”!“块钱,鲜花3!“块钱。气氛?气氛是无价的,其余的都可以用Master信用卡。烛光让他们的目光深情起来。他宽大的手托着高脚杯摇晃着,他探出鼻尖闻了闻,说这酒不错。 半杯透明的红葡萄酒随着他的转动一圈一圈晃荡着。
我去过中国,几年前,很希望能够故地重游。
是你单独去吗?
不,和我的妻子,哦,对不起,我是说我的前妻。
她假装听不出问题的关键——他已经与太太分居了,而把问题淡化了:没关系。我也会这样。讲英语就更容易犯语法错误了。
他没有讲他富有的太太如何以他岳父的百万遗产为筹码挽留他,如何软硬兼施地挽留他。他不愿意讲这些,他不愿意讲他的太太。但是他提醒到下一届系主任他很可能当不上了。我需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她得到暗示:他不知道他值不值得。他需要她给个说法。他没有理由为一个外国学生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包括他的名誉。而他是一个把名誉看得很重的男人。
她从心里感激他,感激他为她承担着声誉上的损失,感激他为她而与太太分居,感激他为她而放弃一贯的生活模式。其实她希望的只是一份奖学金,对两人的事情不要太深究,她相信这也是他的希望。 本来嘛,爱情在这年头应该是方便的事情。两人中间隔着的那一步让他们把自己藏在白天里,夜晚才启用他们的身份。
她还拿不准,其实他也拿不准。直到系里有闲话出来,他们才感觉到压力。
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有妇之夫;一个教授,一个学生;一个系主任,一个助教。系里立刻有闲话出来,尤其是她的中国同胞。留学生身在海外向来是宽于律己、严于律人的。有人说,什么留学啊,根本就是留而不学嘛!专业就是找老公。有人说,我也学会了,下次我要奖学金也跑去哭一场,我还直接到校长那去哭得了。
他们当然也听到了闲话,本来就是说给他们听的,不然怎么心甘。她只是对他说她不读了。他问是因为他吗?她摇摇头,说博士要念五年,我不需要懂那么多东西。他说五年读下来,你会发现其实你什么也不懂。她说现在我已经差不多什么也不懂了。他说那就等你彻底什么也不懂的时候再走吧。她突然对他说:对不起,我给您添麻烦了。声音柔懦、令人不忍,像那种特别懂事乖巧的小孩,受了委屈,也不哭不闹,一个人默默承受,还想着安慰别人。见她这般,他的心都疼碎了,他又下了一个自己预先也不知道的决定。他说,他要辞去系主任的职务,这样她在系里的地位不至于太尴尬。
他一直是个小心翼翼的人,除了在她这件事上。他是第一次跟着感觉走,服务他心灵深处的燃烧,而不是他的大脑。事态发展迅速而情形严峻,他的大脑还来不及进行经济、名誉、地位、习性等种种的现实考量。事后他也许为此后悔过,但我觉得她是他惟一不计成本爱的女人。
她摇摇头,表示这不值得。他握住她的手,说:我已经决定了。她郑重地考虑了一会儿后说:你牺牲太大了,还是我离开这所学校 吧。 本来两人的关系挺不算数的,现在搞得跟真的似的。
后来,他辞去了系主任,她也离开了学校。两人还双双离了婚搬到了一起,制造出一副众叛亲离、相依为命的样子,而这种感觉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以为这就是爱情。她说:现在我们只有对方了。他立刻接道:足够了。他又说:去打听一下接你女儿来美的手续吧。她问:你不介意吧。他哈哈一笑:我娶个太太还多出个女儿,这等于是我到商店买了一件大衣,临走还搭了件衬衣。买一送一。她终于笑了。这似乎比他辞职、分居,更能打动她。不久他们就结婚了,成为合法夫妻。他们就是要告诉社会舆论:虽然他们并非所愿地伤害了社会公德,但他们仍然尊重法律。
我虽然对妈妈的突然改嫁有诸多不满,但从不认为她单纯的是为了绿卡、为了钱。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女人从来不想着靠男人。现在的我能明白了布莱克所言:一个人在无路可走时,强行征用爱情。因为只有爱情能给人安慰。而就是牺牲这个词让她以为找到了爱情的真谛。有了牺牲,有了舍弃,有了抗争,爱情才有了厚度。
这种感觉,她并不陌生,时光倒流,她回到与我爸爸相爱的日子。同样因为牺牲抗争,她曾经一度认为她是爱我爸爸的。
第九章 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大米?(1)
时间到了再前面,知青回城。火车站到处都是回城知青。站累了就蹲下来,蹲累了就躺下来,躺累了就起来不耐烦地踱着步。火车终于进站了,从深处呼啸而至,两只车灯发出光芒,接着所有人的眼睛都跟着发出两道光芒。人群沸腾起来,其中一个是我的妈妈,她两眼发光。那是希望,希望结束这里的一切,而不是开始城里的生活,来不及希望太多,还不敢。这点希望已够用了,仿佛自己个人乃至这个国家就这样开始有了光明。
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目标。回城后每天都出去走走,也是给家里紧张的住房留下空隙。她像一个纯粹的陌生人,畏手畏脚地逡巡于这座城市的大路小道。到处都有像她这样的回城知青,这座城市就这样年轻起来,以前年轻姑娘基本上看不到,街道上走来走去多是提菜篮子的中年妇女。大家就都这样走着,想着,也对看。你也是刚回城的知青吧?看得出,我也是,也看得出吧。人人都有故事,都自以为特殊,其实每个人都在分承别人的故事,于是都没有时间去听别人的故事。她的故事毫不新鲜,无法吸引别人,连自己也吸引不了。
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我爸爸恋爱的。家里不同意她和王海涛的事情,因为他还在农村,于是介绍了一个男人。她心里想着王海涛,没有太注意他。有一次去她女友宋红家,认识了女友的弟弟,与他聊起事情。她问他:你有女朋友吗?他说没有。她笑道:是不是女朋友太多了,不知道哪个是了。他笑了,嘴角一缩,羞极了。他反问她:那你呢?你有对象吗?她就跟他聊到王海涛。以后她与他频繁地聊起王海涛,他是很喜欢听的,带着笑听。后来就不那么喜欢听了,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不喜欢听,可还是听了,而且听进去不少。再后来,就一点不肯再听了。以后你少跟我提那个王海涛。他嘟着嘴巴,头一仰,眼睛一瞥。他男孩般的一厢情愿给人以赌气的感觉。
她一开始不明白,后来不明白也多少明白了。多看了几次,她发现这个叫宋伟的人其实不比王海涛差,长得比王海涛要好,家庭环境也好,最主要的是他的母亲有能力把她留在上海。她开始微笑起来,笑里有点暗送秋波的意思。爱情毕竟不能当饭吃,经历过文革,知道利害关系。她不是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人。
可是真明白后反倒要装得不明白似的问:为什么呀?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她说我知道什么呀我不知道。他有点恼了,不知道算了。他生气的模样很是霸道,却也十分稚气。她抿着嘴笑了,调戏道:你喜欢我?!那揭露性的语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了他。他的脸一下就涨红了,像被别人识破什么似的有点挂不住了。她跟抓住他的把柄似的笑得更得意了,轻蔑与自信全齐了。她像许多人那样揶揄他:你怎么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