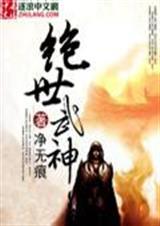芙蓉-2005年第6期-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看来,终于到我算总账的时候啦。早朝上,我问胡惟庸:
“听说,你的丞相府出了命案?”
“臣已经把案件交由御史台,着力查办。”
他故作沉着,我却看得出几分慌乱。皇太子代替我临朝已经有多日,我突然坐到这把龙椅上,不只是他,文武百官都有些不安。
我不再追问下去,因为,从他这一句话,我已经洞悉其奸。这是皇太子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从前,要是李善长家中出了命案,他会尽早来向我告罪,因为他有管理上的责任,而且,他一定会亲自处理案件。胡惟庸没有告诉我,是想隐瞒,再把案件推到御史台,好像是与他无关。
那么,他为什么不去找刑部呢?因为御史大夫陈宁和御史中丞涂节,都是他亲自提拔的,和他必是一党。御史台的职能,是纠察百官,他控制了这里,就可以在暗中另立朝廷,是结党营私之谓也。
当天下午,徐达带着一位老翁来见我,这老翁,从前是军中伙夫,年老退役,在胡惟庸家里掌厨。他向徐达说出了那宗命案的真相,原来,是胡家公子乘车出行,马惊车翻,摔死公子,胡惟庸因此砍死了车夫。
那个车夫,正是我的检校。
徐达和老翁不知道,或许胡惟庸也不知道。
我重赏老翁,让他称病,告假还乡。
徐达建议,马上逮捕胡惟庸。
只说这件事,胡惟庸就是犯了欺君之罪。
事关重大,我不能性急。胡惟庸已经是瓮中之鳖,量他跑不掉,我现在暗中担心的,是我那些检校。我不是担心他们再被害死,是担心他们已经成为胡惟庸的检校,一有风吹草动,都会逃之夭夭。
他们误我大事,我不能便宜了他们。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决定动用亲军,由都卫府选派千人。检校的全部名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诏命他们按名单追杀,一个也不放过。
我明白,会有许多冤枉的。
我更明白,很难查清他们哪一个清白,哪一个不清白。
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现在,正是用得上这句老话的时候。
8
尽管都卫府的亲军奉命谨慎行事,杀那么多人,也很难不留痕迹。刑部接连上奏,几天之间,命案不断,好像要天下大乱了。
被杀的人,也有奉命去杀人的亲军。
在胡惟庸家里,亲军遇到一个矮壮汉子,武功高强,招数怪异,制三名亲军于死地。后来,这汉子终于被擒获,情急之中,他说出几句日本国语。这原本是一个重大线索,可惜,亲军不敢违反杀无赦的命令,当场把他杀死了。
通日本国语的,是哪一个检校?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是武林高手。
天下敢与大明朝为敌的小国,只有两个,一个是蒙古,另一个就是日本。蒙古残军,已经被打残击溃,而日本,因为地处偏远海岛,其海域风急浪高,我一时还没有派大军攻打,他们却经常乘船渡海,搔扰边境。
我居然用日本奸细做了检校!
那么,胡惟庸呢?
家中用一个日本人,莫非他不知道?
他是暗中通敌,蓄意谋反。
这是案中之案,我临事镇定,高屋建瓴,英明决策,牵出了惊天大案。那些忠于我的,冤死的检校,他们可以暝目了,他们虽然承受了冤枉,却是用生命为大明朝作出了贡献啊。我一时还无法补偿他们,或许永远无法补偿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想,善恶有报,应该让上天代我报答他们,不管是在阴间,还是在来世。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大将军徐达应该知道,打一个再怎么样漂亮的胜仗,自家也不会不死伤人马。
当然,这件事,我不会让徐达知道。
以他的聪明,他或许会猜到。
战死疆场的军士,会留下英名,我会照顾他们的家人。对冤死的检校,我却帮不上什么忙了,他们应该把这笔账记在那些双重检校身上,我想,此时此刻,在阴间的某一个地方,那些双重检正在受着惩罚,忠于我的检校不会轻易饶了他们,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
阳世里,也有人应该被剥皮抽筋。
我诏命都卫府,以欺君谋反通敌之罪,立捕胡惟庸。
其家人无一漏网,财产抄没。
因为李善长,我没有对他诛灭九族。
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同案入狱。
如汤浇蚁穴,震惊了满朝文武。
可能我的百官都知道,这是刚刚开了一个头。从胡惟庸家里抄出的财物,几乎敌得过当初的沈万三,金银珠玉,珍宝古玩,满室盈箱。我没给他这么多奉禄啊,他是哪儿来的呢?就是百官,或许是上千的官员给他进贡的。
这些年,我信任胡惟庸,让他独揽朝政,他的权力比当时李善长做丞相大得多,所以,官员们就走他的门路。这些官员,不论是京城的,还是地方的,都跟背叛我的检校一样,应该受到清算。
几日几夜,严刑审讯,我又得到一份名单,其中有文官,也有武官,他们都是因为给胡惟庸送礼,没当官的当了官,当小官的当了大官。我诏命亲军都卫府按名单捉拿,不计其数,大牢里,一时人满为患。
我相信,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冤枉。
无论情节轻重,斩!
杀掉的人里,有宋濂的儿子。这位大儒,没有向我求情,他自知有过,引咎辞职。我喜欢这个满肚子学问的老头儿,可惜他生了一个不肖之子。我深信宋濂事先并不知情,没有怪罪他,安置他去了茂州。
9
环儿,我的洛妃,还是受了委屈,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生下的是双胞胎,两个女儿,皇后担心她年纪小,不会照顾,等孩子满了一岁,就收进了自己宫里,从此,环儿要见女儿一面都难了。
皇后要这样做,我也没办法。
但是,环儿不相信,有时候皇后会比皇帝大。
她向我要女儿,又哭又闹。
开始,她缠着我,要我每夜睡在她那里,作为补偿。出了胡惟庸案之后,因为她对我说过,要学蜂王的话,我记得她的功劳,又喜欢她的聪明,到她那里去的次数多了,她又变换花样,不许我再去,她说,她宁可一辈子独守空房,除非我能帮她从皇后那里把女儿要回来。
许多天了,我没对皇后提起这件事。
我觉得还不是时候,现在提,更不是时候。
但是我今天很想去陪环儿。
从前,我心烦意乱时,就想一个人呆着,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改变了习惯,我更喜欢跟环儿说一说话,消解我的忧烦。
莫非是人老了,害怕孤独?
五十三岁,还不算老。
可是,也不能说是很年轻啦,年轻人,他们已经在我面前长大,没出息的什么事也干不成,有出息的,比如胡惟庸,却要跟我争夺天下。
对李善长,我从来就不敢十分相信他。
对胡惟庸,我却几乎没有提防他。
他真正是有做事的能力,到现在,对于失去了他,我还有些感到可惜,为什么我给了他那么大的权力,他偏要跟我作对呢?他应该满足于万人之上了,莫非不甘心处于一人之下?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是我烦恼的根源。
上天给了我掌管天下的权力,我拿这个权力怎么办?只能分给文武百官,让大官再分给小官,小官分给更小的官,一层一层分下去,直到商人卖他的货,士人读他的书,匠人操他的手艺,农人种他的田。
一县的权力没分好,会乱了一县,一州的权力没分好,会乱了一州,一省的权力没分好,会乱了一省,一国的权力没分好呢?我觉得,这一次中书省出的事就是因为我没有把权力分好。
幸亏发现及时,处置得当,才没有酿成大祸。
我有过错,没有人能够惩罚我。
清算了别人,现在轮到我清算自己。
环儿正在侍弄花草,怀孕的时候,她说,只怕生了孩子以后就没有功夫养花了,她没想到孩子会离开她身边,现在,她多得是功夫。
看见我,她举起一个花盆摔过来。
我闪身躲过,花盆摔碎了。
我呵呵大笑,我说:“环儿,你好大的力气呀!”
她坐到椅子上,低声哭了起来。
我看见她把手放在嘴里吮,啊,流血了。
那是一盆带刺的花。
我连忙传太医,给她敷药,包扎。
都弄好了,太医却还不走,我觉得奇怪,就朝他一挥手:
“这里没事了,你走吧。”
“皇上,臣有一事。”
“你有事?”我更是感到意外,从来太医都是怕事,躲事还来不及,他今天却说有事。我让他讲,他说:“臣曾经为诚意伯诊病。”
“诚意伯,是刘伯温啊!”
“正是。臣以为,他是中了蛊。”
“中了蛊?是何症状?”
“有硬块如拳,生于腹中,多日不化。一旦消化,元气尽失,百药无治。”
“当时,你为何隐瞒此事?”
“臣不敢说。”
“那么,你知道蛊是何人所下?”
“左丞相胡惟庸。”
原来如此,难怪这个太医了。我赏赐他五两银子,他现在能说出来,也算是有良心的。当时,刘伯温得病,我曾经命胡惟庸派医去探望,没想到他居然会借我的名义下了毒手。我又想到,有数名检校都是病死,胡惟庸手下,肯定有一个会下蛊的人,我真是小看了他!
环儿不哭了,在收拾她摔烂的花草。
10
如果环儿没有用花盆砸我,她的手就不会被花刺划破,如果她的手不被花刺划破,我就不会召来太医,那个太医,就可能把下蛊的事压在心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说出来,或者永不会说出来了。
这又是环儿带给我的好处。
她真是我的吉祥星。
可惜,我这个皇帝暂时没有办法报答她。
刘伯温中蛊而死的事,使我心神不定,我十分后怕,如果不是及时除掉了胡惟庸,说不准哪一天,他会用那样的手段对付我。刘伯温不赞成任他为相,徐达建议我尽早易相,我都没有听他们的话,我是错了,而且一错再错,不顾别人的提醒,坚持自己的错,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到,从前的皇帝,有时候会下一道罪己诏。
那多半是他的国家遇到天灾的时候,他认为那是由于自己得罪了上天,担心会受到上天更大的惩罚。
我没必要做那样的事给上天看。
我是在自己怪罪自己啊。
我没在环儿那里久留,去谨身殿读书。
我读了一整夜,未觉困倦。
我喜欢司马迁的《史记》,还喜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两司马,各有千秋。
我读《资治通鉴》唐太宗事:“上问魏征曰,群臣上书可采,及招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写的是唐太宗纳谏。他希望得到有用的建议,真是煞费苦心,看这一点,他似乎比我聪明,我是明明得到了好的建议,却没有及时采用。
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建议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