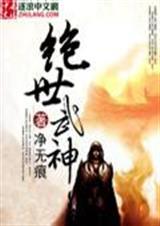芙蓉-2005年第6期-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汴梁,我有过一次微服出访。那一天,艳阳高照,午饭后,趁着酒兴,我带着侍卫来到大街上,我们穿戴的是小生意人衣帽。多年战乱,使这个城市破败不堪,百姓面黄肌瘦,没有几栋像样的楼房。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意外的是看见三个衣着光鲜的壮汉在打一个穷老头儿,我的侍卫要上前,被我拦住了,我要去看看。我在皇觉寺当行童时学过武功,后来又在战场拼杀多年,三拳五脚就打翻了两个壮汉,还有一个从后面抱住我的腰,我用上了郭子兴教我的一招,反臂封喉,这一招我是第一次用,力量用大了,卡断了他的脖颈。我说,你们这点儿本领还要打架,岂不是白送性命?出了命案,官府的人来了,原来我打死的是知府的外甥。我担心挨打的穷老头儿会遭报复,就灭了知府的九族,升原来的同知为知府。当然,那个穷老头儿就是环儿的父亲,他到最后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挨三个壮汉一顿打,因为知府亲戚在街上打人是经常的事。
我的贵妃,是穷老头儿的女儿。
可是,这个穷老头儿家里还有两间房,当年,我父亲连寸土片瓦也没有,我父亲是一个更穷的老头儿啊。
环儿还小,我不能跟她讲我早年的事。
4
我欠了硕妃一个好大的人情,正不知道怎么还她,她自己却有办法。从来不问朝政的她,忽然向我打听大将军徐达的事,我说,徐达刚刚从北平回来。她说,那么,正好。原来,她知道徐达的长女秀美,贞静,好读书,已经成年,想娶来做朱栎的王妃。我当即应允,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姻缘,我最喜欢的第四个儿子,今年十八岁,应该成婚,也只有徐达的女儿才配得上,还幸亏她想到了,另外,我也不担心徐达会不同意。
我召见徐达,要赐给他一座宅邸。
他并不推辞,连忙施礼谢恩。
我说:“那宅子,只是旧了些,你将就住吧。”
他说:“臣常年统兵在外,这里只要能安顿家眷就好。”
我说:“你鞍马奔波多年,也应该歇一歇了,现在北方局势稳定,你这一次可以在京城多住些日子。善长还乡了,伯温过世了,朝中老臣无多,事情又是千头万绪,你正好来帮助我。”
他说:“臣遵旨。”
我说:“给你的宅子,就是我从前的吴国公府。”
他听了,大吃一惊,坚辞不受。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
那宅邸,我已经派人粉刷一新。在册封他女儿为燕王妃的酒宴上,我故意让他多饮了几杯,趁他大醉,派人把他抬进新宅房里。
我还赏赐徐达两名年轻侍女。
这样送人情的方法,我是学的硕妃。
没想到,第二天,那两名侍女又回来了。
原来,徐达一觉睡醒,已是天亮,发现自己身在新居,满屋陈设豪华,就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先赶走了两名侍女。
我没想到徐达居然如此谨慎。
随后,徐达来见我,是谢罪的意思。
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宅子你不肯要,算啦,可是,人,已经是你的人了,你不收,只好把她们拉出去,斩。
他于是同意把两名侍女留下。
他一夜酒醉,怎么说得清床上的事啊?
总算是看见了一点儿兄弟情分。
如果徐达要了吴国公府,我心里会不会不高兴呢?或许会,因为,他再三地不肯要,我很高兴。不过,我赐给他那座旧宅,却并没有试探他的意思,如果给别人,我还真舍不得。世事就是这么奇怪。有时候,一种初衷会带来相反的另一种结果,无法预料,能未卜先知的是圣人。
好像徐达跟圣人差不多啦。
想到这里,莫名其妙地,我又有一些不高兴。
找一个好天气,我约了徐达去游湖。
同行的是两亲家,所谓皇亲国戚,车马仪仗,浩浩荡荡。我的燕王和王妃,也就是徐达的长女,看上去情投意合,使我又一次叹服硕妃的聪明。
应天府有两个大湖,玄武湖和莫愁湖。
玄武湖大一些,据说是得名于宋文帝时,说湖中曾有黑龙显现。我姓朱,朱为红,红为火之色,黑龙为水之色,水克火,所以我不喜欢去玄武湖。但是,我也没有去得罪那条黑龙,因为,虽然水火相克,火却不可没有水,是水火相济的意思。莫愁湖也有一个传说,南齐时,有洛阳女子,名莫愁,嫁到家住此湖边的卢家,后来投湖做了水神。我喜欢这个故事,也就常来这里,还在湖边建筑了亭台楼阁。我想好了,要把其中最大的一栋楼赏赐徐达。
我和他在楼上对弈。
我说:“大将军,这一次你只许赢,不许输。”
他说:“如果皇上棋术高明呢?”
我说:“我许久没输过棋了,我的棋术,太高明啦。”
他哈哈大笑,终于露出一些豪爽性情。
他明白别人跟皇上对弈,不敢让皇上输的心理,也明白我这个皇上,每次对弈都要赢,不免厌烦的心理。我和他对弈五盘,他四胜一负。我说:
“大将军赢了棋,我们赌什么呢?”
“皇上事先没说,哪有见了输赢再下注的道理?”
“其实,我早已经想好啦。”
“皇上要赌的是什么?”
“就是这栋楼,大将军,楼是你的啦。”
这一次他没有推辞,立刻起身,施礼谢恩。我让太监伺候笔墨纸砚,当场写下“胜棋楼”三个大字,诏命做成金匾,悬挂楼上。
输了这局棋,我才赢回另外一局棋。
如今,满朝文武,能跟我这样对弈的,只有徐达一人了,别的人,比如胡惟庸或是汪广洋,他们承受不起。这是权力的游戏。我的龙椅,已经坐上快到十年了,从前,我只要坐得稳当,现在,我还要坐得高兴。
当然,我并没有掉以轻心。
天下这么大,从前,我担心的,是哪里出了什么糟糕的事,比如旱灾、涝灾或者盗贼、瘟疫。现在,我担心的,是哪里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比如哪个武官怕死了,哪个文官贪财了,或者是哪两个官员结成了亲家,还有什么样的官员去吃了喜酒。
无论什么事,只要我知道,就不难办。
如果我不知道,则预示着危险。
这是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打仗的时候,不一定要用兵法,不打仗的时候,一定要用兵法。我看,这条兵法可以说是兵法的兵法,我之所以能用,是因为设有检校。李善长和刘伯温在朝中时,曾经对我设检校表示异议,我没听他们的,但是,也没有让检校放开手脚做事情。我了解天下事,第一是靠各地所上的奏章,第二是靠大臣面奏,第三就是靠检校暗报。这么多年的经验,使我深有体会,奏章里面,水分最大,面奏言语,真伪各半,检校暗报,百无一失。虽然有时候检校报来的事情,鸡毛蒜皮,又多如牛毛,但是,我从来不苛求他们只报大案要案。我希望知道大事,也不讨厌知道小事,而且,有时候,正是一件小事牵出了惊神动鬼的大事。
5
第一个到胜棋楼拜访的,是胡惟庸。
他带去的礼品有:三尺高月季红珊瑚一对,二尺四寸长白玉马一匹,青铜香炉一对,似是汉代以前的东西。
徐达没有收,在大门口就挡住了。
守门人说,大将军有令,任何礼品不可进门。
当然,胡惟庸本人还是进去见了徐达。
守门人是我的检校。
建元洪武的第三年,我把在做吴国公时设立的拱卫司,改为亲军都尉府,掌管前后左右中五卫禁军,检校人选,多出其中。为广泛收集情报,检校中还有各色人等,士农工商,甚至佛与道。他们把情报写成折子,经由太监,直接交给我,太监不准拆封读取。有伪报者,立斩。有立功者,立赏银两,多次立功者,酌情拔任官职。至今,被斩的只有一个人,后来我知道,还是斩错了,他所报情况属实,但是,他是一个铁匠,识字不多,把当事人的姓名写错了一个字。
胡惟庸去见徐达,可以看作是礼节。
他送的礼品,也在情理之中。
我知道徐达不是贪财的人,他打下元大都,派兵马千人封锁元故宫大门,宝物一无所取。可是,胡惟庸哪里来的那些好东西呢?必是别人送给他的,我居然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送的。我想了一会儿,记起来了,洪武四年,杨宪去拜见李善长,送的礼品中,有这样一对大珊瑚。可能是李善长离开京城时,把这东西给了胡惟庸。那匹白玉马和青铜香炉,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对胡惟庸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头,他应该知道,靠这点儿东西,买不动大将军。也许他料到了徐达不会收,所谓送到门口了就是礼。
胡惟庸说:“下官自恨身无武功,不能跟随大将军。”
徐达说:“丞相过谦了,丞相是社稷栋梁啊。”
胡惟庸说:“大将军喜迁新居,要在京城多住些日子吧?”
徐达说:“还不知道,要听皇上旨意。”
两个人见面,除了迎送的寒暄,就是说了这些话。徐达招待胡惟庸的是杭州龙井茶,煎茶老翁,是我的检校。徐达送客送到了大门外,他应该看见了那些礼品,不过,也许礼品是放在车上,他没看见。
徐达有右丞相的官职,但他主要是统帅兵马的大将军。他和胡惟庸,正是一将一相,古人喜欢说,将相和,好事多。这话没错,将相争斗起来,搞不好会天下大乱。可是,我也要提防将相合谋不轨。
我曾经这么想,徐达是我最不需要提防的人。接着我却又想,或许他也是我最需要提防的人。简直是莫名其妙,哪一种想法是正确的呢?俗话谚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喜欢俗话谚语。
成了儿女亲家,我跟徐达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一天,传来元将扩郭贴木儿因病过世的消息,这个元将是徐达的老对手,我特意在华盖殿设酒宴,和他对饮了几杯。他还记得土刺河战败之恨,他说:
“可惜没能生擒了扩郭贴木儿!”
“他算得上是一员猛将,可是,生不逢时。”
“有几次,都是险些就擒住他,却又被他跑掉了。”
徐达好像是真的很不甘心让那位鼎鼎大名的元将就这么过世,我已经有多年未转战疆场,全不是他这样的心情。我希望他也能淡忘一些兵刀水火,因为,我不打算再让他挂帅出征了。我向他说起,要抽调一些羽林军,增强秦、晋、燕三府的护卫,他很是赞同。我又说,打算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他听后,略一思索,说:
“皇上是否有易相之意?”
“现在,我还没有想。”我说的是实话,我要改的是各地行中书省,不是中书省,我更没想易相的事。为了让他听明白,我又说:“胡惟庸办事认真,这几年,没出什么大差错。”
“臣以为,等出了差错再换,不如早换。”
他这么干脆地提出要换掉胡惟庸,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以为,他对朝廷的事会特别回避。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他应该不知道,我已经了解胡惟庸去拜访他的细节。我答应慎重考虑他的话,就送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