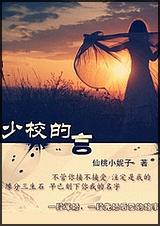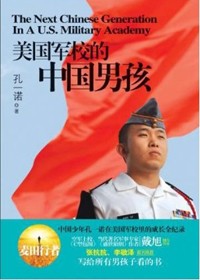王海鸰大校的女儿 (全本)-第6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坚忍身影,那个深夜,我们走在去坑道的蜿蜒小路,一边身侧是刷刷作响的玉米地,朝另一侧望去,便是那面墨蓝锦缎般的大海,海里一轮满月银光灿然,美丽豪华得令人窒息。……一股甜美的感伤悄然升起,轻柔绰约如纱似雾在这间阔大的办公室里弥漫。我定了定神,没时间回忆遐想了,他很忙,我也很忙,不可能无止境地在这里耽搁下去,可我们似还有许多话没说,我说的是那种深切的、直切入肺腑的个人化谈话,而不是诸如打不打台湾、打台湾他们师的位置在哪里。几次想提起上次的话头接着谈下去,都被他不动声色地绕开了。也想是不是我话说得太重刺伤了他,又觉着不像,不会。不知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短暂的静默后,我这样开的头。
“在岛上的时候,在咱连的时候,想没想到过你会有今天?”
“今天指什么,当师长?”
“差不多吧,就这意思。”
“没有。”他老老实实答道,“那个时候我心中的偶像是咱排长。”他刚说罢我们便相对大笑起来。“咱排长”姓于,那年可能也就二十多岁,可在我们眼里,那就是成熟和权威的化身。一度我也崇拜他,须知“崇拜”这东西是有传染性的,不过这崇拜在我那里延续到了他老婆来队的时候就结束了。临时来队家属宿舍离我们排宿舍不远,于排长却始终不让我们去看她,说:“看什么看?没法看,丑得要命。不过,当兵的老婆还是丑了好,一年回去不了一个月,漂亮点的,搁家里怎么放心?”这种话在我十六七岁的耳朵听来简直庸俗透顶,于是崇拜不复存在。于排长军旅生涯的顶峰就是排长,之后转业,再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让你失望了是吧。”看我只笑不语,姜士安说,“在我身上怕是找不到你们理想中的那个,呃,影子。你们爱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说我可从没说过,他没理我,“我嘛,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就是,把该我干的事情干好,认真地、满怀着热爱地去干。对上,让上级放心,不能一件事交给你,后面跟着七八个工作组收拾。对下,让下级信任,觉着跟着你干有前途有价值,打起仗来,做不到‘零伤亡’也得是死得其所,非死不可,崇高悲壮。……当师长前我是参谋长,那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论主官问什么,我脑子里得有,得张口就答;提建议,一提,主官马上采用才行,不能说反正我提了,你爱用不用。做什么事都得有标准,标准就是目标,目标清楚了,你加班加点吃苦受累也会乐此不疲。我跟我的干部们说,干什么吆喝什么,当排长就想着怎么当好你的排长,师长军长的工作用不着你费心考虑。一句话,干好该你干的事,每干成一件事,就是你一个向前迈的台阶,目标再远大,你也得给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
我头也不抬地做着记录。我承认他说得不错,也是一种肺腑之言,是他的一个侧面,但仍不是完全属于他个人、只能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我做记录很大程度是一种姿态,是采访技巧。手指头因为冷而不听使唤,房间太大,暖气不是很足,笔在手里打滑,我放下笔,往手里哈气。姜士安提高嗓门叫了一声,门应声而开,公务员进来,姜士安让他去“拿件大衣”。公务员对师长的这个指示是这样理解执行的:不仅拿来了大衣,两件,还提来了电暖器。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白里透粉的脸蛋上有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在向他的师长脸上瞥了一下之后,立刻就明确了自己下步的行动:毫不犹豫把暖器提到了我坐的这一侧,插电源,打开,安置好后,敬礼退出。点点滴滴,全是素质。披上了军棉大衣,电暖气也开始发热,全身立刻暖和了起来,同时感到的,是一种被权力照顾呵护着的满足。
电话铃响了,姜士安拿起了其中一部白色电话,我借机起身在他的屋子里溜达。这屋里有书柜,文件柜,报架子,奇怪的是,还有衣柜。每个柜子上都贴有打印出的标签,井井有条。书柜是透明的,基本是军事、历史、社科方面的书,文学书也有,只三种,《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我随手抽出了《 三国演义 》,这书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只看了个开头,知道是名著,该看,下过了几次决心攻读,看不下去,只好放弃,说到底文学作品是让人消遣的,为了它痛苦就犯不上了。现在我们家这书已成了海辰的,被他看得封皮儿都掉了,经常还要对我提问,诸如:“刘备娶了孙夫人回荆州诸葛亮给他们接风的第一道菜是什么?”我说你总提这种犄角旮旯的问题有意思吗?他说那你就说说赤壁大战吧。赤壁大战我也只知道个朦胧大概。他就开始给我讲授,兴致勃勃。受此启发,以后凡给海辰买书,就买我不喜欢而比较有名的,比如《 封神演义 》、《 隋唐演义 》,他一概看得津津有味。而对我在他这个年龄时所喜欢的《 安徒生童话 》、《 格林童话 》,他没兴趣,这种性别所致的差异常令我惊叹。姜士安的这本《 三国演义 》看的遍数比海辰只多不少,封皮儿是没有掉,纸页磨薄了。他接完电话走过来问我看什么。我把书合上把封面对他。
他赞叹:“看了《 三国演义 》,就会知道什么叫谋略,怎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无论战略战术战役,堪称军事经典。”
“这本呢?”我指《 水浒传 》。
“我喜欢这里面的剽悍勇猛,还有那种豪情、勇气。”
显然这三本文学书能摆上他的书柜不是偶然的了,看他能对《 西游记 》说出点什么。他说:“异想天开!不拘一格!”
我笑了,索性就此在他阔大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看到什么感兴趣的,就停下来看看,看不明白的,就问问,他毫无异议跟在我的身后,我走他走,我停他停,有问必答,像一个宽厚、耐心、脾气奇好的兄长。我不看他,但全身无一根神经不感觉到他的存在,令人软弱的冲动一阵一阵袭上身来,使我想不顾一切地做点什么,做点心里想做的什么,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女人能够抵抗住这种诱惑:那种来自与你有过青春恋情、现在指挥着千军万马的一个强悍男人如猫一般的驯顺、依恋、温柔所产生出的那种诱惑。有几次我不得不站住,以专心警告自己:小心噢,虚荣心不要发作!……我在他贴有“衣柜”标签的柜前站住,说实在的,打一看到它我就心存了好奇,但到底没好意思擅自打开,衣柜是一个太具隐私色彩的空间。我把手放在柜门的把手上,看他。他毫不迟疑微笑点头。我打开了柜门,里面是作训服,军装,解放鞋,洗漱袋,文件包,令我失望。我希望的东西是不光明的,比如铺盖什么的。不过想想也傻,他一个师长,真的不想跟家属住一块了,哪里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地方?师部两幢三层楼的招待所,套间单间都有。内心阴暗,面上便越发要做得光明磊落,我“砰”地关了柜门,大口大气地说:“嗨!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放家里嘛,办公室里设衣柜,不伦不类!”
“有紧急情况,能立刻就走,用不着再专门跑回家去拿。”
“太夸张了吧,你家离办公室不过五分钟。”
“到那时五分钟也——”
我摆了摆手,我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那些话我从十六岁当兵时就开始听了,听了几十年了,什么样的话听几十年也得听木了,也得听成了套话、大话、空话,至多是,口号而已。可我知道在这里是不一样的,备战打仗在这里鲜活具体深深渗透进了这个男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渗透进了他情感、精神的每一个细胞。心中涌上了一股醋意,面上不动声色。“不错。很不错。”我大咧咧环视着四周,道,“你感觉呢,是不是对自己也很满意?”
“说不上满意,至少是,不后悔吧,几十年啦。军号声,嗷嗷叫的兵,一声令下,不说地动山摇也是一呼百应。每年七八月份外训,千军万马——应该说是千军万车了——装甲车,坦克车,通信车,指挥车,工程车,牵引车,高炮地炮直升机,一齐出动,那场面!”他陶醉般叹息一声,使劲摇了下头,好像要将自己从神往中叫回来,又好像在责备自己的无力描述。接着,把目光移到我的脸上,热烈地说:“韩琳,你再来一趟,明年!亲眼看看!”
“到时候再说,可能够呛,手里还有好多事。”
“来代职嘛!副师长,副政委,都行,来后马上给你配一辆车。想下部队就下,不想下就写你的东西,什么都耽误不了。”
“主要是我家里还有孩子。”
“不就是个上学问题吗?转学过来嘛,很简单,我跟政治部说一声。”
他总是能迅速抓住你所说事情的核心并马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这是最能让女人意志薄弱的一种男人,让你不由自主想听他的,按他说的办,跟着他走。
我挣扎着:“孩子还学着钢琴……”
“钢琴好办!叫几个兵给你拉过来就是了。”
看样子他是真的想让我来,但是,为了什么?不会是就为了让我看一看他那一齐出动的“千军万车”吧?我凝视着他道:“太麻烦了。真要想看那些,你说的那些,哪个部队都一样,可以就近,比如北京军区。”
他愣住,停了停,闷闷应道:“……那倒也是。”
他的反应让我心痛,心痛的时候心就会狠。我说:“我理解你的感觉,万人之上,前呼后拥,像个国王,男人嘛,没有不喜欢这个的——拥有自己的王国,哪怕一个小国呢。但是你想没想过,你的这种感觉,很可能,不过是,由于封闭而造成的一种结果?”
“你的意思是说我——井底之蛙?”
“我的意思是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他耐着性子道:“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精彩,每个人也只能拥有其中的一部分,谁也别想什么都占着。”这我得承认。比如我喜欢我生活状态中的自由自在,那么就别想奢望他生活状态中的地位权力。同是精彩,非此即彼,水火不容。他接着说,“你比方一个人,有很多钱,无数的钱,又能怎么样?像那谁说的,也无外乎一天三顿饭,晚上一张床……”
“那可不一定。比如,他可以包一架豪华飞机,满世界飞!”那时候还没有蒂托花两千万美金遨游太空一事。
“包一架飞机,满世界飞,就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了,本质上是精神需要,精神上的满足。跟我们比,不过是方式不同,渠道不同,趣味不同……”
这样的谈话让我感到累,感到厌倦,索性闭了嘴,由着他说。沉默中我想,我该走了,再待下去也是无趣。我扔下孩子扔下手头的事情大老远地跑来,绝不仅是为了看部队看千军万马,看师长看士兵,为这些,不必非到这个地方。我怀着一个朦胧温柔的愿望而来,怀着对青春岁月的追忆,怀着交流的渴求。刚开始似乎还好,而后,断了,仿佛一把正演奏到好处时突然断了弦的琴,硬要继续演奏下去,只会将原先有过的美妙也破坏光了。
“怎么不说话了,韩琳?”
“不是正听你说呢吗。”
“你来之后净我说了。说说你!”
我猝不及防,泪水一下子涌上眼眶,掩饰都来不及,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