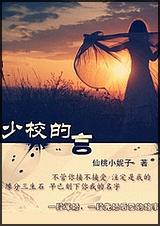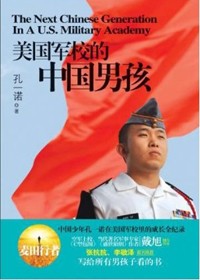王海鸰大校的女儿 (全本)-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了一个箱子一个旅行袋,不假思索地道:“东西好办,我给你看着。”话一出口就后悔,我想请人帮着拍个电报还研究了人家这么半天,我凭着什么就能让人让我帮着看行李了?情急之下马上补充说,“我也在部队工作。”
“从前?”
“也是现在。”
他看我,明显审视的目光。也是,我这副样子,一件皱巴巴的布连衣裙,一条瘸腿,孤零零一个人拖着个箱子,哪里有一点点人们概念中女兵的影子——飒爽英姿?尤其是在这个当口说出,更像是一个骗局,至少是,一个无聊的玩笑。想到他会不信,且有充分理由不信,我有点急。事到如今,拍不拍电报都不主要了,主要的是,关乎荣誉。我想也不想就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了过去,那上面有照片有姓名有我就职的工作单位,当然还有年龄。我这个年龄已经避讳向别人说自己的年龄了,但是当时全然忘记。显然他没想到,颇有点惊愕,完全是凭着下意识把那个红皮小本接了过去。接过去后就像是接过了一个烫山芋,两难: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最后,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当然,“折衷”一说是我的揣测:看,但不细看;匆忙打开,瞄一眼就合上,就还给了我。然后,起身,走,走几步又回来。
“打个长途电话岂不更好?”
“我们家是军线。”
他又那样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把地址姓名电报内容写一下。我写给了他,他看着脸上浮上了一丝淡笑。我禁不住又一阵脸红,那正是本人的重要缺点之一,字难看,这也是日后我换电脑写作的重要动因。他拿着字条走了,我想起又一件该我想着的事。
“哎——钱!”我喊。
“回来再说!”
他答应着就跑远了。他的个子不是中等而是中上,站着看比坐着看要高得多:腿长。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分人材。对于男人来说,身材比脸蛋重要。
一刻钟后,开始检票。前后左右的人纷纷起身,拎着、拖着、招呼着,去排队。这时我尚能沉得住气,从检票到发车,还有二十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我开始着急,伸手将所有行李拢在腿边,以让腿能感觉得到它们存在,一双眼睛,就紧紧盯住了候车大厅入口。又过去了五分钟,检票已基本结束,看着由拥塞变得冷清空阔的检票处,心里阵阵发慌。万一他误了车怎么办?我误了车怎么办?真不该去冒这个险,电报拍不拍真没什么要紧。万一,万一他因为着急撞了车呢?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就是在这一刻,他出现在候车大厅门口,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他看到我时的那一瞬间,他脸上露出的如释重负……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拿着东西就走,前方检票员已经解开铁链子往栏杆上拉了,我们边喊边走,那一刻,我瘸着一条腿居然还能够走得飞快。
他是在差一分钟的时候踏上了他的那次列车,都没能来得及走到卧铺车厢那里,只能上车后再拖着行李一节一节车厢地挪了,也算是万幸中的不幸。他刚上车列车员就收踏板关门了,接着,列车启动,我冲站在车门后的他欣慰地挥手告别,忽然,脑子里嗡的一声——
——钱!
这件事梗在了我的心里。为这个日后我还专门去邮局查了一下,所得结果使我越发难受:发那样的一封加急电报需五块多钱,当时我的月工资才一百八十多块,折合折合,这五块多钱得相当于今天的五十多块。
我忘不了他拍电报回来看到我时脸上的如释重负,那一瞬,我心里有一种骄傲的快意。当时是没机会说,如有机会,我肯定得告诉他:别说你那只是两件行李,就是两箱子钞票,我心不动!这件事他做得也漂亮,在于己无害于人有益的情况下达到了人格的自我完善。本是好事,那五块钱却成了瑕疵,我的瑕疵。他对此有什么感受?懊恼还是窝囊?
曾有一段盼着他能主动联系,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何方人士,他知道我。但是他一直沉默,使我又想起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在我的工作证上那样匆忙地一瞥,未必知道我。
下火车后妹妹在车站门口接我,妈妈从干休所里为我要了车。看到我的脚伤后妹妹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她工作的医院为我挂了急诊拍了个片子,还好,没有骨折。回家后同妈妈讲起了电报的事情,妈妈津津有味地听完了道:
“这孩子不错。”
家里真好。
干休所傍山而建,我们家在干休所的最里面,窗外的对面就是山,葱茏青翠。家里小院的花草树木蓬蓬勃勃,清晨,耳边是一声声鸟叫,新鲜空气直沁脾肺。没有汽车,没有烟尘,没有嘈杂拥挤的人。各种娱乐、生活服务、医疗保健设施齐全,大院门口还有士兵站岗,是一个安度晚年的好地方。
雁南来看我了。
当时我正在跟母亲说《 周末 》演出前后的情景,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叙述法,从头道来。把个母亲听得目不转睛屏息静气,随着我的讲述时而叹息,时而紧张,时而生气,时而开怀,一杯泡好的绿茶搁在床头柜上都放凉了,忘了喝了。当我说到我们的那位男主角用筷子从地上夹“酸黄瓜”吃时,母亲放声大笑,笑得全身颤抖泪都出来了。我心里一动,建议母亲去趟北京看我的戏。母亲想了想说算了。我问为什么。她不说。我非要她说。她说:
“要是你爸爸能看到这些,该多高兴啊。”
我哑然。父亲是我们忌讳跟母亲提及的话题,母亲也轻易不提。焉知道父亲已浸透在了母亲四十三年的生活里,事事处处点点滴滴。母亲的不提仅仅是在嘴上,是体谅我们,她的心里,何曾就有过片刻的忘记了?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就是这时门铃及时地响了,我扭脸向窗外看去,高兴地看到了站在院门外的雁南。
雁南的到来使我们静悄悄的家热闹了起来。她给我带来了“奇正藏药”,专治跌打扭伤,敷上后二十四小时即可见效;给母亲带来了一大堆乱七八糟价格昂贵的补品;给保姆小英带了一条七成新的裙子。小英因此也喜欢雁南,洗水果拿瓜子热情空前,并主动请示母亲给客人预备什么饭,从前,小英一向最烦有客人在家吃饭。
刚开始母亲也一块坐了会儿,母亲在场我们聊天的范围就比较局限,无外乎工作啊身体啊什么的,措词也较收敛。这时雁南已调到军区总院了,她退下来的副司令员父亲成功地为她又发挥了一次余热;怀孕也有五个月了,肚子不见大多少,腰明显粗了,两颧骨还长出了妊娠斑,妊娠反应已经过去,现在出奇地能吃。我们谈到了小梅,没细说,不知为什么,我一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谈论有关“性”的事情。母亲走后,我才对雁南说了那事,雁南说她知道也正在帮小梅想办法,又说:
“那位百祥同志如果完全不行,是不行,首先孩子,从哪来?但要是有了孩子,叫我说,行不行的,无所谓。跟你说韩琳,现在我挺烦那些事儿的。隔几天他就非得来那么一次,有什么意思啊真是的,想不通。”
“新鲜劲儿过去了。”
“可能。我现在挺羡慕你的。”
“莫名其妙!”
“你不可能理解我。”
“该有的你全有了,丈夫,孩子,喜欢的工作,你还想要什么?”
“得到的同时就意味着失去。”哲学语言,让人费解。
“你失去什么了?”
“自由。选择的自由,恋爱的自由,独往独来的自由。”
“绕这么大半天弯子,你是不是又看上什么人了?”
“哪里还有这个资格!”
“那是另一回事。”
于是雁南长叹一声,不说话了。雁南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或者说,很容易动心的人。一个忧郁的眼神,一道才华的闪光,一个微笑,甚至苦难、不幸,都有可能使她心动,并且每一次她都会觉着这一次是真的,就是说,起码在她这方面,非常真诚。事后我嘲笑她,说她擦出的那些感情火花就像电焊的光,亮,热,美,但是轻飘,薄脆,短命,没有根基到可以挥手即去。她为自己辩驳说时间连生命都可以更新呢何况感情?雁南动辄爱以生命作比,妇产医生做久了的缘故。我说别人怎么就不像你呢?还是你水性杨花。实际上我的评价对她不完全公正,她同时又相当地传统自律,任心中波涛起伏汹涌,从未付诸过行动。按说像她这种空想式的精神恋爱者,丈夫孩子这些世俗因素本构不成妨碍的,可惜她又生性追求完美,即使仅仅是在遐想的爱河里遨游,也不希望自己有一点点瑕疵。后来,许久以后,我乘车上街路过一家报亭,在众多封面女郎的俏脸中瞥见了一个文章题目,叫做《 结了婚的女人想恋爱 》,不由会心一笑,想,这不是说的雁南么?
沉默良久,雁南开口了,问我想不想知道他是谁。我问她我认不认识他,她说不认识。那我就不想知道了。如果双方我都认识,还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分析、联想的乐趣。否则,这种事情,往往当事人说起来有滋有味惊心动魄,第三者听来却是大同小异似曾相识。说到底,男女间的恋爱不就那么几个套路?雁南的套路比之别人要更乏味一些:她最高潮的一个结尾,也就是同人拥抱了一次,还是在冬天的马路边上,隔着两个人用以御寒的纺织物,那拥抱又要打去许多的折扣。但看雁南兴致勃勃,甚至带着一点恳求——她需要倾诉——我实在不忍直接打击她,只好采取缓兵之计。
“雁南,不要以为这一次就是真的了,早晚还得过去!”
“不一定。这次的感觉和以前绝对不同。”
“每次你都这样说。”
“是吗?”
“是的。”
雁南便有些惶惑,想想,说:“那就让时间来检验吧——三个月!”
“什么三个月?”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三个月之内,过去了,就过去了;过不去,三个月以后还是忘不了,那就是真的了。”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别看我说雁南水性杨花,心里却非常清楚我跟她差不多少,我是说在对待感情问题的风格上,我也属于很容易心动的那种,否则,不至于带伤仓皇出逃走到这步。也许,其实人人都差不多少,区别只在于行动与不行动?好吧,三个月之后!
进家不久,母亲就开始问我的“个人问题”了。我不喜欢母亲问这些,不喜欢任何人问,但自从父亲去后,无论母亲问什么,我都会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从前,常常什么原因没有,我就会跟父母闹别扭,他们想听我说点什么,我偏不说什么,现在不了。我跟母亲说了我新处的那个男友,母亲全神贯注听完了后,下结论说:这人不行。母亲的态度让我温暖让我感激,她从来不说“差不多就行了”,她仍然珍重我,在她的心里,我仍然不是需要做季节性降价的处理品。自从进入大龄女青年的行列以来,我经常受到这类打击我都烦了。
当时我半坐床上背靠海绵垫子,受伤的左脚下垫着又一个海绵垫子,随意,慵懒,舒适。这是楼上的一个房间,父母从前的卧室,房间窗下就是一架葡萄,密密匝匝仿佛翠绿的地毯;院外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四季葱茏的山,秋风由窗口吹进,一阵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