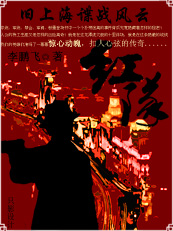上海的金枝玉叶-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58 五十岁 最长的一天
They never discussed his feelings towards the plight he was in。 Maybe Daisy was not as strong as she became later; and neither of them wanted to face the grave shadow that was reaching out for them at any moment。 Maybe they wanted to pretend that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这一年,戴西的丈夫吴毓骧被划为右派。戴西从此开始她炼狱的生活。
在1956年,兴华科学仪器行与政府正式合营,并入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吴毓骧从资方成为机械进出口公司的业务科长,被派到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一边被洗脑,一边参加了对共产党的大鸣大放,当时,他大概以为积极参加各种共产党鼓励的活动,是正确的表现,或者他的生性就是不能好好设防的,容易激动的,没有更多目的就像他年轻时代跟着清华同学去参加〃五四〃游行一样,这一切,就像他当时冒着当反革命的危险收听美国广播。不是要知道反华宣传,也不是要知道被封锁的世界新闻,而是忍不住要听美国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在这同时,他认识了更多的工商界前任的资方,他们在一起郊游和聚餐,互相以〃老〃相尊,吴毓骧开始被人称为〃毓老〃,甚为得意忘形。
但是现在不能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与感受了,甚至在当时,连戴西和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确定。他们在一起旅游,在一起吃饭,在自家花园里照相,熟悉在季节转换时的那些清晨,他因为支气管敏感而爆发出的一连串咳嗽和喷嚏声,就像德国木钟里的小木头鸟按时出来叫时一样。可他们从来不谈论他对于自己处境的感受。也许戴西还不像后来那样坚强,她和他都不想面对越来越近、伸手可及的巨大阴影。也许他们都想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也许他们认为说了也没用,反而是徒增烦恼。他们就这样在阴影逼近的时候紧紧关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嘴,像鸵鸟。
当1957年到来,吴毓骧在一张《解放日报》上,看到自己上了右派的名单。可是他不知道在他的档案里,从来就没有右派的材料,到1980年全国右派甄别平反时,已经在提篮桥监狱病逝二十年的吴毓骧,因为档案里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的记录,而被无法平反。谁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解放日报》的右派名单上。
很快,他被通知不再担任业务科长的工作,改做清洁工,他回家来,向佣人学怎么将拖把拧干,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到了这一天,戴西夫妇才真正明白过来,他们发家致富的时代没有到,根本没有到。而他们慢慢失去一切的日子,倒是不由分说来到了。
戴西也离开外滩的办公室,被送到资本家学习班去学习。在学习班上,她也第一次学习怎么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子,送去修路用,支援国家建设。开始她不懂,后来,她知道在砸石头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厚手套。
1958年3月15日,戴西在学习班上被通知说,公安局在家里等她,要她马上回家。
果然有两个警察在家里等她。自从家里的保姆偷了美金那次,家里来过警察,这是戴西家中第二次有警察进入。这一次,他们是来通知她,吴毓骧已经被捕,要她将入狱要用的行李送到思南路的看守所,那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那些可以送去的东西,包括衣服、被子、毛巾和草纸,但不可以送牙膏牙刷,怕牙膏里藏着毒药,牙刷的硬柄会用于自杀。
戴西说:〃我听到警察对我说这些话,几乎惊倒。〃
这时,她听到楼下的客厅里传来了琴声,有人在弹琴,她听出来那个人在弹中正这个星期正在练习的曲子。然后,她意识到,是十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了。他从来不热衷弹钢琴,他们也从没有想过要让他当一个音乐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拖拉着学琴。她一开始在心里奇怪,怎么中正今天这么起劲,然后,琴声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知道自己的亲人回来了,虽然只是一个上初三的儿子,可他是自己的亲人,这种安慰让她清醒过来。
过了三十七年,中正从美国回来看戴西,他回忆了那一年三月十五日的情形,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一天,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那个下午长大的。在这一天以前,他还是一个贪玩的男孩,每个学期开始的第一天,要戴西将他一大早叫到自己卧室里,训一次话,重申戒条。到第二个学期开始的第一天情晨,再把他叫到卧室里,将上学期的话说一遍。
那一天,中正放学回家,一进门,大厨子就把他拖住,告诉他家里出了大事,现在警察和妈妈就在楼上。中正希望妈妈知道自己已经回家,但他觉得不能上楼去,他觉得楼上有巨大的危险,于是,他到客厅里去弹琴。琴声一响,吓得大厨摇着双手飞跑过来,要将他往琴凳下拉。中正对厨子说:〃这样,妈咪就知道我回家来了。〃
戴西日后说,是中正的琴声把灵魂重新带回来给她。
他们一起为吴毓骧收拾了一个包裹,准备送到第一看守所去。
在他们就要离开家以前,电话突然响了,是一个戴西非常陌生的男人的声音。他告诉她吴毓骧开去上班的黑色福特车,就停在离单位不远的九江路上。他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中正和戴西一起去送了包裹。按照地址,他们来到一处非常热闹的街市中,沿着阴沉的灰墙一直走,走到开在边上的铁门边上,就能进出一处平房。里面有一长排木头柜台,后面坐着没有戴帽子的警察。他们给了戴西和中正一个号码,一夕之中,现在它代表着她的丈夫,他的爹爹,他成了一个号码,直到他去世,他一直叫一六七五号。
在警察检查东西的时候,中正透过通向里面大院的门,看到了一棵矮小的塔松,还有空无一人的院子。它看上去甚至可以说是宁静的,令十四岁的中正非常惊异。中正就这样记住了这个门框里的院子,那是他爹爹住的地方。以后,是他代替无法出来送东西的妈妈,为关在这里的爹爹送了整整三年的东西,他每次都耐心地等着将家里的东西送进木门去的警察回来,他会带回一张小小的纸,上面有爹爹写的自己的号码,表示东西已经收到,也表示自己还活着。对中正来说,它是表示着自己还能与爹爹有某种联系的证明。那对十多岁时突然失去父亲的男孩子来说,是重要的安慰。
当时吴硫骧每次都要家里带棉线去,中正对此十分不解。直到吴毓骧去世,中正陪戴西从监狱里将他的遗物取回来,才发现他所有衣服上的扣子都被剪去了,为了要让衣服能包住身体,吴毓骧将棉线搓成了小绳子,代替扣子。这是后话了。
谁也没有看见高大风流、一表人才的吴毓骧穿棉线当扣子的衣服,是什么样子,最后一次,看着他出门,他还是整整齐齐的,用穿西服的样子异常端正地穿着布做的人民装。
这一天,一定是中正和戴西的生活中最长的一天。
送完东西出来,他们一起去外滩的九江路,把家里的车开回来。那辆黑色的福特车,已经用了许多年。公私合营以后,在外滩上班的资本家们,大部自己收敛了平时的气焰,开始雇三轮车,或者和职员们一样,乘公共汽车上班。只有吴毓骧,每天开着自家的汽车去,就是直接去厕所,取了拖把做清洁,他也要开了福特车去。
因为多年没有维修福特车,而且自己开车在当时已经太过招摇,戴西警告过丈夫几次,希望他不要再开车了,可他从来不听她的。只是他不再让戴西坐自己的车上班,让她改乘公共汽车。
在没有一棵街树、两侧高楼林立、黑黝黝像山谷一样的九江路上,他们找到了孤独地停在夜色里的黑色的车,他们坐了进去。当发动后,戴西发现车况非常糟糕,几乎不能再开。这回家的一路上,它时而失去控制,时而突然媳火,在繁忙的大街上险象坏生。戴西必须集中全部精力。
他们拐上南京路。相去不远,就是永安公司了,那时商厦里灯火通明。它曾是戴西家的产业,它使戴西离开了和平的澳大利亚来到中国,给了戴西一份富有健康的生活,她那样生活了五十年,可是从这天晚上起,不再这样生活了。他们的车背着这个大商厦,越开越远了。
他们经过国际饭店,那是戴西二十年代冲进照相店去,把自己的照片从橱窗里摘下来的地方,可那照片又被当时追求她的吴敏骧偷去挂在自己房间里了;也是1936年组织上海第一场锦霓时装秀的地方;是每年圣诞全家团聚吃饭的地方;也是与那个神秘的犹太人8碰头拿装着钱的纸袋的地方;它带着三十年代曼哈顿的气味。可戴西在那一夜,什么也不能想地经过它的身边。要是车况尚好的话,我想也许戴西会想起当年记者紫燕的那篇感慨的报道,当年这个记者感慨富家小姐们与穷人的理想之间的差距之大,现在是不是戴西也可以感慨自己的生活中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他们经过延安路,很靠近那个有大花园的郭家老宅。从前戴西有了什么难处,她就回家去,那里有成群的兄弟姐妹,有强势的父母,他们家的孩子大都以率性的态度处世,因为他们从前不大知道,在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自己不能掌握的。现在,他们已经四散在美国各地,父母已经过世,老宅已经是国家财产。戴西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去杭州玩时摔伤了腿,就开车回家让哥哥帮忙包好。也许她根本没有时间多愁善感,她怕出了车祸。她从那里拐了开去,回到自己的家。
在戴西后来的回忆录里,只写了一句话,表达当时在车上自己的思想。
我驾着根本不能开的车回家,我想YH早已经知道这车是不能开的,我猜也许他就是希望开车时能出意外。
我想,要是我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车里曾掩盖着这样的绝望,会五内俱焚。我不知道戴西会不会这样。因为她没有多说,对一直跟着她的中正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回到家以后,她默默地把车泊进车库,熄了火,再没有去碰它,直到它被政府没收。
吴家的宅子和一天以前一样宁静,站在埋枪的小上堆边上的那棵棕搁树,和一天以前一样在开始暖和起来的夜风里沙沙地响,甚至在甬道上,和一天以前吴毓骧下班回家来的时候一样,泊了车后,留着劣质汽油微微的臭气。而生活从此变了,对吴家花园的每个人来说。
临进家门的时候,中正在后面叫住戴西,说:〃妈眯,今天我长大了。〃
我猜想这张照片是1958年晚些时候拍摄的。那时,戴西一家开始习惯家中的亲人变成一个号码的事实,他们与留在上海没有离开的唯一一家至亲波丽一家去了公园散心。照片上的戴西,还是笑着的,可那笑容里已经没有了神采,而且还看不出后来眼睛里无邪而且无畏的坚定,她的笑容里有一种楞怔,一种恍惚,一种惊惧,她还没有真正适应1958年的新生活,她还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在这张照片里,她开始穿起了长裤,而波丽仍旧穿着大衣和长裙。五卜岁的她,开始了第二次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像浅剧里一样充满了对比与反差的生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