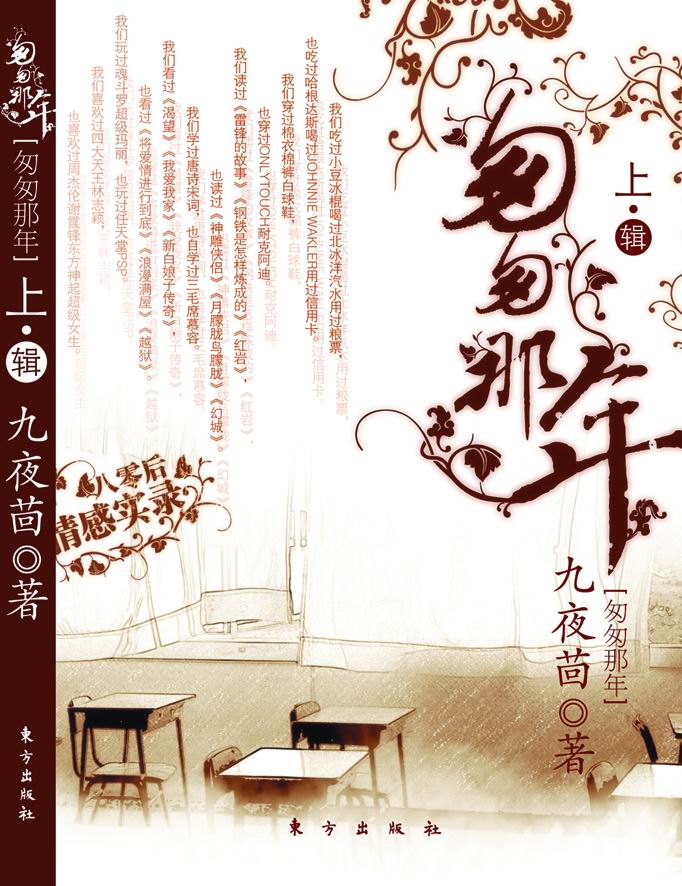那年那月的事-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到眼前的范建国被他训斥得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李宪平也有些后悔,他本想找对方谈谈心,聊聊身世的。有关除四害的那些言论当然也要谈,那只不过是要劝告对方注意吸取以往的教训,不要乱放炮。不想一说就激动起来,就抡起了重锤,他依然是当兵时养成的习气,越是自己喜爱的部下,就越是批评起来不管不顾。
李宪平很有些悔意,于是倒了一杯水端到范建国跟前,“喝吧,就用我的杯子,我可是什么病都没有!”他完全是一种对老朋友的语调。
范建国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双手颤抖地接过有些烫手的杯子。这多半年来,还从未有过一位领导这样对待他,完全是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式对待他,对此他已完全陌生了,他所熟悉是对待异类的目光,冷冰冰的眼神。他觉得自己的眼圈开始发热,他强抑制着自己,眼泪还是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借着李宪平接电话的机会,悄悄抹去了脸上的泪水。
李宪平接过电话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冲范建国挥挥手轻声说:“你先回去吧,咱们改日再聊。”
电话是区工业部部长周彦琪打来的。
对方在电话中劈头盖脸地责问他说:“你不是向我打保票说,接收第二批右派学生是全支部讨论一致通过的吗?怎么这样快就有人向上反映不同意见?告诉你,人家已反映到章书记那里去了!接收不接收这些人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反映你们对这些人管理不严!知道吗?……”
“章书记怎么说?”
“你先不要急于打听领导怎么说!我就问你为什么向我打埋伏?向上面汇报工作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你那个支部到底研究讨论过没有?你要给我说清楚!”
“是讨论过,只不过事先没说接收这么多……”
“我不听你口头上瞎扯!”周部长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让你们支部书记给我就这个问题写个书面汇报来,写清楚你们的态度。为什么要接收这些右派学生?不是说厂里技术底子薄嘛!全写清楚。还有,我跟你说,第一批接收的那些人表现得到底怎么样也要写清楚。”
“表现不错啊,有一个还在制材车间搞了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件事在下面反响很大……”
“行啦!别光说好听的。人家反映了,这些人当中还有乱说话的!连除四害这么大的事他也敢攻击,说三道四!”周彦琪在电话里提高调门吼道,“你给我记住最重要的一点,这些人是右派分子!是我们的改造对象!我们接收他们是遵循党的政策给出路,要改造他们!其次才是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这个关系不能颠倒!这些人中如果有乱说乱动的,绝不能客气!”
等周彦琪发够了火,电话才挂断。
这个电话搅得李宪平心里很乱,把他已保持了一整天的好心情全扫荡光了。清晨,打麻雀他几乎百发百中,他的枪法依然这么好多少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中午吃饭时,他将邹晓风偷偷拉到自己屋来,两人关上门喝开了酒。下酒菜是食堂发给每个职工的两只炸麻雀,酒是他珍藏了半年的一瓶好酒。那种兴奋,激动,喜悦之情倒不是他击中了多少麻雀,过了枪瘾,而是枪声令他想起了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想起了过去的老战友,怀旧之情使他动了喝酒的念头。
他的举动令邹晓风也很激动,喝着酒两个人又念叨起那些熟悉的名字,包括死去的战友。当然,又提到了“大鼻涕”。邹晓风当时很动感情地说,“那咱们就努力把厂里新来的这些‘大鼻涕们’改造好吧!”
李宪平激动得为邹晓风这句话跟他碰了杯。
两个人躲在屋里偷着喝酒时,就听陈爱兰在外面嘟囔着说找不到人。陈爱兰还上前头推了推门又走开了。两个人看在眼里,捂着嘴这个乐呀,像两个办了坏事的孩子。屋里的人透过窗上的纱帘能看清外面,而外面的人却看不清里边。陈爱兰手里拿着广播稿,显然是来找邹晓风或李宪平请示什么的。而这种时候,陈爱兰多半会找邹晓风,因为他喜欢改广播稿。
这个短暂的中午,李宪平感到开心极了。那份好心情一直保持着,他觉得好心情就如同怀里揣着一瓶陈年佳酿令人回味无穷。而就是这么一个电话,将
他的“陈年佳酿”打得支离破碎,将他的好心情扫荡得一干二净。
无疑是支部里有人向上打了小报告,他首先想到的是支部副书记谷玉森。他觉得不会是别人,谷玉森这么干也不是头一回,但一下子就捅到区委书记那里却令他十分吃惊。他万没想到谷玉森会有这么大的能量,过去他从不把谷玉森看在眼里,只是觉得他思想狭隘得很,气量太小,满嘴的马列主义理论,自视水平很高的那么一种人。现在看来,是低估了谷玉森的权欲野心,否则他不会这么小题大作,背后捅他一刀。
接收几个右派学生,李宪平始终觉得算不上什么大事。接收他们是来厂里当普通劳力使用的,即便是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也没将这些人捧为上宾。况且曙光木材厂又是个区属的小厂,厂址又远离市区没人愿意来。前年,区人事局分配了一名林业学院应届的毕业生,来了不到半年就通过关系调进了城。如今一下来那么多的大学生,又不讲什么条件,这些人头上戴着帽子又好管理,这对厂子的发展无疑是好事一桩。但如今在某些人眼里就成了问题,甚至看作是他的立场问题。
显然,周部长的态度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点李宪平已明显感受到了。这说明他已受到了来自上方的压力,否则他不会措辞如此严厉。曙光木材厂接收右派学生的始作蛹者是他,正是这位周部长认为这是一件有助于曙光木材厂发展的大好事,才与他李宪平一拍即合。
李宪平想不通,对这么一件于企业的发展,于右派分子改造都不抵触的事情,区委书记怎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呢?在他的心目中,区委书记章华是位很有水平的领导。他虽与这位区委书记没什么接触,但章华的报告却没少听,讲起话来引经据典,很有水平啊!他想到一定是打小报告的人夸大了什么。
想到周部长在电话中提到厂里先接收的右派学生有人乱说乱动,攻击“除四害”的行动,李宪平敢肯定,一定是谷玉森在这点上做了文章。这是个要害。他会说这些右派学生在厂里没有人监督其改造,放任自流,甚至还会说是他这个当厂长的放纵了这些右派分子,说他的立场有问题。因为正是他李宪平在支委会上提出建议,要在适当的场合,对范建国的技改成果提出表扬的。一样的事,分怎么说,其效果会大为不同,这个道理他是清楚的。谷玉森在这方面作些文章,就难免会产生他所希望的效果。
李宪平敢肯定,周部长让他们以厂支部的名义写一个有关接收右派学生的书面报告是周部长本人的主意。其目的是当做“挡箭牌”用的,既可为他周部长防暗箭,又可为他李宪平开脱一些责任。这样一来,接受右派学生就成了厂领导集体的决议。周部长在电话中着重提醒他要在为“企业发展需要”上着笔,就足以说明其用心良苦。此时“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刚兴起,风怎么刮,雨怎么下,谁的心里都没底,但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自我保护,防范的意识还是有的。这一点,李宪平对周部长的良苦用心还是理解的。
晚饭后的职工集体宿舍区一片宁静,连每晚必拉几段二胡的老马也没了动静,早早就上了床。人们都累了,让麻雀闹的。早上天没亮就折腾,不是摇旗呐喊,就是上房掏窝,可着劲地嘶叫,傍晚下班又玩命折腾了一个多钟头,麻雀都累死了一片,人能不累吗!人们都想着早些休息,明天全市还有剿灭麻雀的统一大行动,依然要起个大早。
就在人们快要入睡的时候,从后排宿舍传出杀猪一般的嘶叫声,将人们的睡意吓跑了大半。
“是黑驴这小子在叫唤。”老马第一个做出判断说。在曙光木材厂很少有人敢叫孙广财的外号,但老马是个例外。老马不但二胡拉得好,还练就一身好跤,全厂的小伙子没一个是他的对手。夏天看老马的身板那是一种享受,胸肌发达得很。老马为人正派,他看不惯孙广财这号人。
“像是这小子吃了亏,挨谁的打呢?”与老马同屋的唐贵祥已推开了后窗户。孙广财就住他们的后排,从这里能影影绰绰看到孙广财与人扭打在一起。
“新鲜,有人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这可要瞧瞧去。”好贪热闹的老马趿拉着鞋出了屋。
唐贵祥站在那里没动。他已看清了,是孙广财占了下风,占上风的是那个新近来厂的大个子学生。唐贵祥受过孙广财的欺负,如今能有人教训这小子他自然心里高兴,但过去如不拉架就容易招恨,不如远远地看风景。
打架的正是孙广财与范建国。
范建国重回到宿舍的时候,孙广财一个人正在屋里闷头喝酒。两个人谁也没理谁,范建国一头躺在床上,满脑子里想的还是厂长跟他讲的那些话。厂长的话大半是批评他的,但又让他听得那么入耳,那么舒畅。他能感受到,厂长是完全平等的对待他,没有把他当作异类训斥,他好久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批抨了。说来也怪,挨完批评会比受了表扬还美!
直到洗完脚要睡觉的时候,范建国才想起看一眼笼子里的麻雀。这一看,令他大吃一惊,笼子里早已空空如也。再看刚才孙广财喝酒的地方,地上扔了一堆麻雀的骨头,班长让他看管的战利品早成了孙广财的下酒菜被吃下了肚。再看孙广财,这小子眯着眼躺在床上正跷着二郎腿抽着烟,哼着小曲呢。
范建国心头的怒火一下子窜到了脑瓜顶,他上前一巴掌将孙广财手里的烟头打飞了,用手指着他的脑门厉声喝问道:“那些麻雀让你下酒啦?”
“你他妈的跟谁说话呢?找死呀!”孙广财在眯眯糊糊中挨了一击,着实吓得不轻,他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他的话虽说得很横,但心里却一阵发虚。范建国比他几乎高出了一头,块儿头也比他粗壮得多,真动起手来,恐怕没他的便宜。
“我再问你一句,那些麻雀是不是你吃了?”范建国的嗓门又高了几度,手指头几乎碰到了孙广财的脑门。也许是气的,他声调明显有些颤抖。
孙广财做出一副满不在乎样子推开了他的手,咧着嘴说:“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为那些家雀儿啊?谁吃不是他妈的吃,你还想养起来呀!”
望着那张无赖的脸,范建国真想一拳打他个满脸花,但一想到还要与这无赖同住一室,他还是强忍住了。他给对方找了一个台阶,说:“我不想跟你打架,明儿一早你跟我一起对我们班长说清楚就行。他怎么说就怎么办。”
这孙广财天生是个欺软怕硬的青皮,他一见范建国软了,反到硬了起来,嘴里骂骂咧咧地说道:“找他妈谁啊?我不归王河那孙子管,凭什么找他说去?找他妈的谁也是吃进肚子了!那是‘四害’,不该吃是怎么着?‘四害’知道不,跟地,富,反,坏,右是一个样儿,是专政的对象!”
范建国听得出来,这小子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歪理是冲他的痛处扎的,他的拳头真的发痒了,但一想到自己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