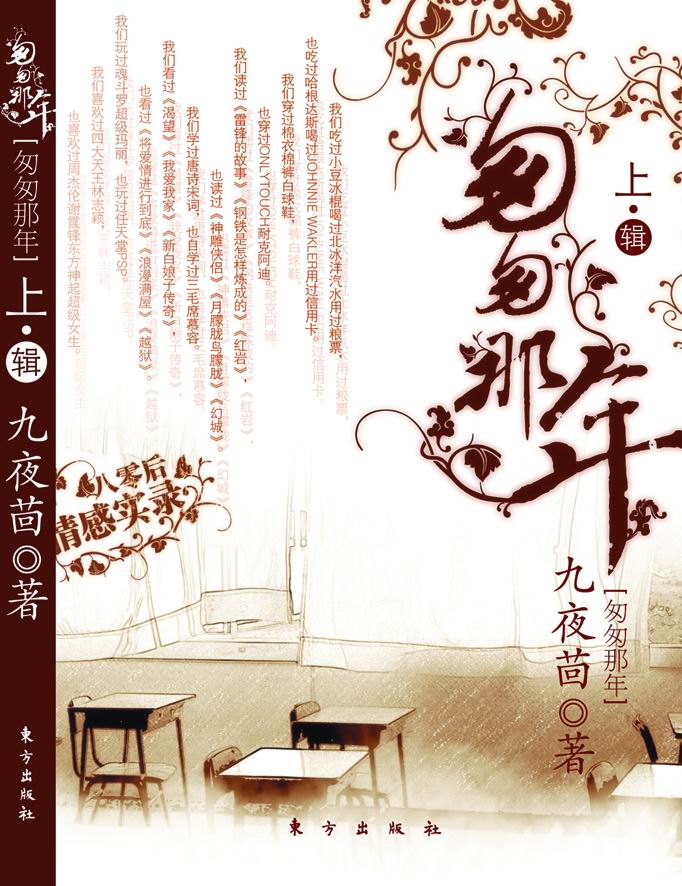那年那月的事-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北角。厂里的职工大半是一工一农的结构,家属在农村的居多,平日住厂的不少。
厂的西邻是铝制品加工厂,整日“叮当,叮当”的冲床声。东边隔着铁道的是个建材仓库,堆积的是些水泥制品,整日里有车辆出出进进。厂的后边便是大片的农田,据说还是个比较富的生产队。厂门的前面是一条引水渠,水面很宽,水流很急。过了桥便是公路。跑这趟线的郊区车特为这两个厂设了一个站,站名就叫曙光厂。
天已亮了半边天,但注定是阴天,没有一丝阳光能挤出那厚厚的云层。这或许是天公对难以数计的小生灵面临的灭顶之灾仅能表达的一点点哀思。
锣鼓声下人们的呐喊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惊恐的鸟儿开始四下乱窜,无处落脚。远处的庄稼地里除了有社员们在摇旗呐喊,地里还树起了无数的稻草人,大概鸟儿们在此时此刻才知道将面临灭顶之灾,没命地到处乱窜一气。厂内有数的几条电线上成了鸟儿能落脚喘气的地方,但很快就被气枪,弹弓击落了几只,吓得又奔命去了。
有一两粒雨点落在了范建国的脸上,更激起了他内心的感慨,他觉得天公为这些小生灵表达不平的方式是那样的无力,为什么不来一场倾盆大雨呢?他虽然深知即使下一场大雨也无法改变鸟儿灭门九族的命运,还是企盼着能有一场大雨快些到来,哪怕那只是天公大哭一场也好。
“大个儿,别净站在上边瞎喊!弹弓子呢?”王河在下面冲范建国吼起来,又指了指离他不远的电线上的麻雀。显然他是有些不大满意。
范建国的弹弓很快惊飞了那只鸟。
此时,从厂办公室的方向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随之便是人们的欢呼喝彩声。那枪声在阴霾的空中是那样的刺耳,久久在耳边回荡。
“现在广播一号战报,现在广播一号战报……”大喇叭里的广播将嘈杂之声压了下来,接着便是女广播员激动人心的语调,“经过全厂职工近一个小时的奋战,全厂捕灭的麻雀总数已超过二百只!厂长李宪平同志不愧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神枪手,刚刚用七发子弹击落了空中五只正在逃窜的麻雀,极大的激发了全厂职工的斗志!……”
范建国听得出来,那是陈爱兰的声音。令他想不到的是李宪平能有这样的好枪法。他随之由那些麻雀的命运又想到了自己,他那些为麻雀叫冤的言论已传到了厂领导的耳朵里,李宪平已提到要找他。虽然他对这位厂长的印象不错,但挨批怕是躲不过的。不由他有些后悔,不该对陈爱兰乱发议论,一激动就忘了厉害,忘掉了惨痛的教训。
“师傅,咱们要在这上面吆喝到什么时候?”那个年岁大些的主动凑过来与范建国搭话。
范建国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脸,那是一张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脸。那神情也是那个群体所特有的,谦恭中暗含着清高,困惑中潜藏着无奈。
“您贵姓?您是新调来的?”范建国没有回答对方的提问,而是急于想印证自己的猜测。
“免贵,我姓石,石国栋。昨天下午报的到,从机械学院来。政治上,犯、犯错误啦……”石国栋口吃起来,大概是一时不知该如何介绍自己的身份。
“这么说咱们是同类?”范建国握住了对方的手,但随之很快又松开了,他意识到两个人此时高高在上,下面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在仰着头搜索敌情,如意外发现两个老右在众目睽睽之下热烈相聚,哪还得了!
“你也是老右?”石国栋的惊奇远在对方之上。当看到对方点头之后,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他转身用力摇晃着手里的竹杆,又学着吆喝了几声,才问道:“哪个学校的?”
“建筑工程学院五六届的毕业生,分配到研究所不到一年就赶上运动了。所长家里的鸡窝盖的满够水平,用的是公家的材料。所里的群众有意见,就有几个人联名写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大字报。我自告奋勇配了一幅漫画,一首诗,满以为这是帮领导整风,不想成了向党进攻,成了老右,连党籍都丢了……”范建国说着自己的经历很是伤感。
“你也是党员?”
“在大学里入的党。”
“还不知你怎么称呼呢?”
“范建国。惭愧得很,与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本家。”范建国苦笑着自嘲道,“当初起这个名子也有学先人的意思。”
“你这个名字好熟啊!”石国栋拍了拍脑门突然叫道,“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前些年报上介绍过的那个孤儿院里出来的大学生吧?对了,是你!”
范建国含笑点了点头。他找了个干净些的地方坐下来。手里仍不住摇晃着那绑着破布条的竹杆。许是突然被人提起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令他的心中如同被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腿肚子也一阵发软。他真想大哭一场,眼泪已含在了眼圈里,但他还是强忍住了。
石国栋意识到自己触到了别人的痛处,但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便学着范建国的样子在离他一米多远的地方冲着相反的方向坐下来,有气无力地晃动着手里的布招子。其实,他的心情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沉重。
“一九四四年你多大?”石国栋的头微微扭过来问道。
“还不满十岁。”
“就在那一年我加入了北平的地下党。”石国栋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说,“我说这个丝毫没有向你摆老资格的意思,我是说我们全是党培养起来的孩子,是一心要跟党走的。但做父母的也有打错自己孩子的时候,只要我们问心无愧,总会盼到那一天的。”石国栋实在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描述他说的那一天准确的含义,但他始终坚信不会总是这个样子。
尽管他怀疑对方说的不全是真心话,但听了石国栋的劝慰和自述,范建国的心情还是豁然开朗了许多,并开始对石国栋怀着几许敬意,盼望着今后他能和自己分在一起,他最怕的是孤独。他指着站在远处的“眼镜”问道:“你们俩全分到制材车间了?他那种身子骨在这干可够呛!”
石国栋告诉他,小个子叫何小波,是钢院大三的学生。至于是不是明确分在了这个车间,他也不太清楚。
何小波显然不爱说话,更没有主动接近谁的意思。他始终远远地一个人站在那里,双手握住竹杆在胸前不紧不慢地晃动,身子也随之有节奏的摆动着,就像个机器人。从登上了屋顶也没听到他吆喝过一声,如同个哑巴。宽大的工作服从他的背后看就像披着一个深蓝色的面口袋。
云层很厚,大半是那种乌黑的云,将苍穹勾画得象一张欲哭无泪的鬼脸,望着那些无助的小生灵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乱飞乱窜。
先是那些学飞不久的幼鸟从空中不断地落下来,每一只累死的麻雀掉下来都会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人们的吆喝也由此变得更加起劲,将手中的布招子晃动得频率又加快了一些,锣鼓之声也更加震耳欲聋。
广播喇叭里在播放第二号战报,全厂歼灭的麻雀已突破四百只。并为此算了一笔经济账,说按一只麻雀每月要吃二两谷物计算,消灭四百只麻雀一年至少可以使国家少损失一千多斤粮食。广播员最后以激动人心的语调发问道:“同志们,大家想一想,全国六亿人民齐心协力围歼,节省下的粮食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辉煌的数字!”许是由于激动,广播员的声音已有些嘶哑。
“这又是一本糊涂账!”范建国忿忿地说。他头一次对那熟悉的女中音产生了反感,“怎么不算算四百只麻雀一年能吃多少害虫,那些虫子又能祸害多少粮食啊!”他说完扭过头望望石国栋,许是希望引起共呜。大概因为面对的是同类,一激动使他的胆子又变大了许多。
石国栋像是什么也没有听到,眼睛呆呆地望着空中,双手机械地晃动着布招。他脸上看似毫无表情,实则是将引发的共鸣强压了下去,是将不吐不快的那些议论没出口就嚼碎了生咽了回去,新到了一个地方他更要谨慎一些。
有关麻雀的话题如让他说,会比范建国说得更有根有据。他的姐姐是搞生物的,一年前他就从姐姐拿回的学报上看到有关麻雀的各种争议,并知道一位全国知名的生物学家郑作新院士和他的学生们曾大胆为麻雀辩护。郑院士带领他的学生走遍了河北的农村地区,采集了八百多只麻雀的标本,一个个地解剖,其结论是麻雀不是害鸟,不能捕灭。后来这篇论文还发表在权威性的报纸上,但这声音很快就被另一种声音淹没了,后一种声音发自伟大的人物。
伟大的人物还会有错吗?这是石国栋经常暗自发问的一个问题。包括他自己由一个始终忠于党的儿子突然变成异类,尽管他对自己是属于挨错了打的孩子坚信不疑,但对自己是否还会有个明朗的未来却常常将信将疑。其实他并不想用那种自己都将信将疑的话来安慰与他同病相怜的年轻人,但他除此之外又实难找出更合适的话来。
此时他对范建国的话装耷作哑,是觉得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太好冲动,如对他发表与之相同的看法,等于是往他的枪里装药,什么时候捅出去又是个麻烦。况且大势已定,再说什么也改变不了麻雀的命运,又何必再自寻烦恼呢。
范建国见对方对他的话不理不睬,料定是戒心很重,便不再说什么。想到自己的处境,也比麻雀强不了多少,不由对自己空发的那番议论又觉得可笑得很。麻雀虽遭灭顶之灾,但还有一双翅膀,尚有一丝逃生的机会。即便被捉,死的倒也干脆。而自己呢,从被圈入那特定的指标那天起,自己便不再是自己,一切身不由已,仿佛被困进了一个无形的笼子里。
先是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让他挖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说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动机。罪名和帽子都大得吓人,似乎他已经承认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拼命地抗争,为自己的那幅漫画辩解,为自己说过的一些连自己也记不清的话辩解,但一切徒劳,所有辩解却成为他态度顽固不化的表现。
他说自己苦孩子出身的人怎么会反党?自己在外国教会的孤儿院虽然能上学,但晚上要当童工,要干到很晚,却拿不到工钱。是解放了才使他能读完高中又考上了大学入了党,报恩还报不过来怎么会反党!他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这番话反使人家找到了他反党的依据,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还能培养出好苗子来?斗争会反而更激烈了。这也使他反而增加了抵触情绪,他为自己争辩得也更加激烈了。
幕后的大人物终于走向了前台,那位将自家的鸡窝用公家的人力物力盖得像一座微型宫殿的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说是谈谈心。领导的态度和蔼可亲,说谁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说你还年轻,将来所里的发展靠谁?当然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说大家几个晚上不休息帮你挖根源是为谁?还不是为了使你能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说深挖一挖嘛,早认识了早一些取得群众的谅解又有什么不好?你还是党的人嘛!
领导的态度使他流了泪,觉得对不起人的该是他自己。人家革命了十几年,盖了一座鸡窝又能算什么?又能占公家多大的便宜!自己真的是小题大做了。再一想到是自己使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