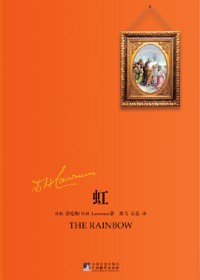人民文学0512-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店门前;十几个木头桩子一般的士兵持枪站立在冷风里;一辆囚车横在门前。
罗光春笑了笑;一扬手;一串钥匙在他头顶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就着一串哗啦的碎响;便落在了当街;继而大步走上了囚车。风渐渐地硬了。天阴得更重;一场大雪将至。一街人涌出来观着;见囚车拉着高大的罗光春驶出了秀水街。
第二日清晨;罗光春顶着松松紧紧的雪花儿;被斩于保定大旗杆下。罪名是伪造国家印信。他的首级在保定的大旗杆上悬挂了七天示众。再三日之后;罗光春的尸体被人出资收敛了;首级也有人出资请人缝合了;许多人看到;一口柏木棺材装着罗光春的尸首;载上了一辆牛车;就吱吱呀呀地碾着一路冰冻的积雪;涩涩地出城去了。
无人知道罗光春被埋在何处了。出资办理这件事儿的人始终没有露面。
罗光春就这样死了;润文轩也就此关张了。他的徒弟李双夺张得意也不知所终了。
后来听人说;李双夺和张得意都曾经在北京开过刻字社;他们二位的传人仍在北京。只是传说;并无实据。
一九九八年;保定有一位名叫石桥的文友;主编了一套《保定艺术人才大观》(共三卷本;内部资料;没有正式出版);上边有罗光春的几十字的材料;现引在这里:
罗光春(?——1915年):男;河北曲阳人(一说河北唐山人);治印艺人。曾在保定秀水街开办“润文轩”刻字社。名重一时。
谈歌曾经听人说保定仍存有罗光春的治印;可是遍访收藏者;均无下落。那一日;谈歌在秀水街中的一家文物店里;见到了一方闲章:清水听音。谈歌感觉刀工非常;冲中见切;切中藏冲;大气磅礴;夺人目光。谈歌心中起疑;莫非是罗光春的作品?当下便问及店主此印的来历。店主道:此是当年保定一位刻字大家留下的。谈歌再问详细;店主也不知就里。谈歌问及罗光春这个名字;店主想了想;笑道:“我还真是听说过这个名字。”
谈歌来了兴趣;忙道:“说来听听。”
店主皱着眉头回忆着说:“我也是听人讲的;说这个姓罗的是个盗墓的;也收藏了许多文物;‘文化大革命’中给枪毙了。您问的是不是这个人呢?”店主盯紧了谈歌。
谈歌慨然作罢。
(责任编辑 程绍武)
摘自:《人民文学》2005年12期 作者:谈 歌
敲狗
在这里;狗是不能杀的;只能敲狗。狗厨子说;杀猪要放血;宰牛羊要放血;狗血是不能放的;放了就不好吃了。有人说;咋个办?厨子说;敲狗。
敲狗比杀狗更凶残;这一带的农家人一般不吃狗肉;也就不敲狗了。可是;花江镇上的人却喜欢吃狗肉。人一爱吃什么东西了就会琢磨出好做法来;好做法就有好味道;到后来这味道;不但香飘花江镇;而且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很多人闻名而来;不是为了来看花江大峡谷;都是为了狗肉而来。久而久之;知道花江大峡谷的没几个人;大多知道花江狗肉。
花江的小街不长也不宽;这并不影响来往过路的各种车辆。只要有临街的店门;都开狗肉馆。每一个狗肉馆几乎都是这样;灶台上放着一只黄澄澄煮熟的去了骨的狗;离灶台一二米的铁笼子里关着一只夹着尾巴浑身发抖的狗。
那只熟狗旁的锅里;熬着翻滚的汤;汤随着热气散发出一种异常的香味;逗得路过的车辆必须停下来。熟狗与活着的样子差不多;除了皮上没毛了;肉里没骨头了;其余都在。喜爱哪个部位;客人自己选。那只关着的狗;却只是让人看的;无非是说;就是这种狗。
这里的狗被送进了狗肉馆;没有活过第二天的。而关在铁笼里的那条狗却能较长时间地活着。这只狗能活得长一点;主要是它的主人不愿意亲自把绳索套在狗的脖子上。初送来的狗;似乎都能预感到它的末日来到了;对着狗馆的厨子龇牙露齿狂吠不已。可主人不离开;它也不逃走。等主人与厨子一番讨价还价后;厨子拿了一条绳索给主人;狗才吓得浑身颤抖;却还是不逃走;反而依偎在主人的两腿之间;夹着尾巴发出呜咽声。主人弯腰把绳索套在狗的头上后;接下来是把狗拴在一棵树上。这样做了;主人再不好意思面对可怜的、恐惧的狗;多半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狗见主人一走;眼睛里的绝望便体现在它狂乱的四蹄上;它奋力地迈腿想紧跟主人的脚步;可是它没迈出几步;又被紧绷的绳子拉回来;又奋力地迈步;又被绳子拉回来。狗脖子虽然被绳套勒得呼吸困难;可它的确想叫出声音来;它是在呼喊主人;还是在愤怒绳子;不得而知;总之它平时洪亮的声音变成了呜咽的呻吟。
狗是比较喜欢叫的动物;它的叫声很久以来一直是伴随着人的。在这块土地上;一户人家也许没有牛羊马叫;甚至没有猪叫;但很少没有狗叫的家。汪汪汪的狗叫;几乎是每个成年人在儿童时期最喜欢模仿的声音。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人们最美好的记忆;莫过于自己一吹响口哨;狗就跑到你身边;亲热而又忠诚地摇着尾巴跟着你;无论你要去什么地方。狗叫的声音对主人是忠诚与踏实;对好人是亲切和提醒;对坏人来讲是胆寒和警告。当狗叫不出声音的时候;就好像人在痛苦地呻吟;也像婴儿在哭一样。狗哭的时候;主人是不能听的;他的选择只有不回头。
任凭狗怎样地挣扎;越挣扎;它脖子上的绳索越紧。当狗由于憋气在地上翻滚时;厨子拉动绳子;把狗吊了起来。狗身子悬空起来;不沾地的四蹄更加挣扎不已。厨子拿来一把包了布头的铁锤猛击狗鼻梁;狗扭曲着身子;被绳子紧勒的喉咙里发出像奶娃哭泣的叫声。狗在这猛击中只能坚持几分钟;便没了声息。这时的狗;样子挺可怜又挺吓人。它的眼睛圆瞪着;两行泪水流过脸庞;舌头夸张地伸出嘴巴。厨子的样子却挺得意;他并不注意狗的可怜。厨子的得意体现在他丢锤子的劲头上;打完最后一锤;厨子把锤子往地上一摔;锤子便连翻了几个跟头。厨子接着用手去摸狗鼻梁;确定没碰烂皮后;顺手摸合了狗眼睛。厨子的手湿湿的;并不是有汗;而是狗的眼泪。厨子把手掌在腰间的围巾上擦了擦;对徒弟说;看明白了;就这样打。狗鼻子最脆弱;要敲而不破才好。
徒弟望着厨子的手;也望着厨子腰间那张不知擦了多少狗眼泪的围巾说;师傅;下一个我来敲。
厨子闻声很高兴;就把手上残留的狗泪拍在了徒弟的头上;说好好干;好好学;以后你就靠这个穿衣吃饭。
徒弟是厨子新收的。厨子一般两年就收一个徒弟;不是厨子有喜爱收徒弟的嗜好;而是徒弟们没有超过三年而不走的。徒弟们走了;花江狗肉馆就开得到处都是。先是县里、市里有了;再是省城有了;最后有人竟然开到了北京。厨子听说后;不以为然。有人说;你徒弟们都发财了;你老要是去外地开一个;还不更发财呀!厨子一笑说;钱我也喜欢;我更喜欢狗肉。有人说;莫非只有在这里才是狗肉;外地的不是呀!厨子说;不是我们的花江狗。有人说;外地都用花江狗肉的招牌。厨子说;我说过了;不是我们花江狗。
狗还得吊着;过了半个时辰再放下来。厨子当徒弟时;曾跑过一条狗。不过那狗跑了几天又回来了。那年厨子刚进师门不久;正是大年前夕;师傅想吃狗肉;可过年过节的。没人送狗来卖。师傅叹了口气说;把大黄敲了吧!大黄是师傅养了两年的狗。师傅敲狗如麻;却还是不敲自己养的狗。于是徒弟去敲。徒弟照着平时师傅敲狗的过程来了一遍;可以说投什么错误的;问题出在徒弟见狗被敲得没了声息;便解了狗的绳套放在地上。死狗是不能马上放下地的;狗会扯地气;地气一上身;狗便会醒过来。等徒弟从屋里端了个大盆来装狗时;大黄早跑得没了踪影。徒弟自然是少不了挨顿臭骂;看着师傅因没有了狗肉吃而暴跳如雷的样子;徒弟心里难过极了;毕竟是要过大年了;把师傅气得这样子;的确不应该。由此徒弟永远地记住敲了狗不能马上放在地上。
狗对主人的无限忠诚;表现在无论主人怎样对它;它始终忠于主人。大黄也是这样的一条狗;在它挨敲死里逃生后的第三天;又肿着个鼻子回到了主人家。
厨子至今也在想;师傅为什么要亲自敲掉大黄。大黄被敲后吊在树干上的样子;厨子这辈子是没法忘记的了。大黄的鼻子肿得发亮;眼睛瞪得圆凸凸的;眼泪特别地多;都死了半晌了;还有几颗晶莹的泪滴挂在下巴上。从那以后厨子敲了狗一定得给狗合眼。
厨子的徒弟从屋里端出一个大木盆放在树下;然后把狗放下来;提起狗的四蹄丢进木盆里。接着徒弟又从灶台上提来一大壶开水;慢慢地把水往狗身上淋。厨子拿了个大铁夹子;给狗翻身子;然后把狗头按压在水里多烫一会儿;又把狗蹄往水里按。
每天;关在铁笼子里的那条狗;都能听见它同类的像哭的声音。这狗先是在狗的哭叫声中;在那个不大仅仅能转身的铁笼里;惊恐地团团转。后是仰着头寻找可以逃走的缝隙;可是那些铁条的间隙只能让它伸出一个鼻子头;它甚至试图对着铁条下嘴咬;可它的牙齿却怎么也咬不到铁条。
后来;铁笼子里的狗不再惊恐了;它似乎听惯了同类像哭的呻吟。它把后腿收在屁股下;前腿朝前伸直平放;这是一种卧着身子却又保持着起跑的姿势。时间长了;狗就把头平放在两个前腿之间;眯着眼。
厨子的徒弟拿来一把刮毛刀等候在厨子旁边。厨子丢了铁夹;猛地从烫水中抓起狗蹄子;嘴巴嘘唏着;把狗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把手放在嘴下吹气。显然厨子的手被水
烫得发痛;可他每次都是这样。仿佛他不这样被烫一下就对不起狗一样。徒弟刚来时就见师傅的手被烫;很想给师傅说;有很多办法可以不烫手;比如;抓狗蹄子之前先抓一把凉水;或者一个铁夹使力不够;再多一个铁夹。但徒弟就是徒弟;徒弟教师傅;在这一带是最不敬的事。师傅这么干;徒弟当然也只能这么干。有一次;徒弟终于忍不住说;师傅烫了手怎么办?徒弟说的话;当然不是讲师傅的手;师傅的手天天被烫已经千锤百炼了;徒弟甚至怀疑师傅的手早没了痛感;师傅的嘴巴又是嘘唏又是对着手吹气;可是烫的痛感并未上脸。徒弟知道自己的手;只要是被什么一烫;脸比手更容易让人知道二—被烫了。徒弟由此认为;师傅的嘘唏和对手吹气只是个习惯。是呀!徒弟只见过嘴巴对冬天的冷手吹热气。
徒弟问师傅烫了手怎么办;当然不包括师傅的手。徒弟这样问是想找一个师傅同意的理由;使他可以用不烫手的办法去抓烫水里的狗蹄。但是师傅的回答却不给他任何理由。师傅把手伸到徒弟眼前晃动;说烫什么手;我烫了几十年。不要怕烫;手比哪样都快;水还没来及烫手就离手了嘛!干活嘛就要像干活的样子。徒弟说;师傅真烫手哩!师傅说;烫了也不要紧;去擦点狗油;一会儿就好了。再说烫多了就不烫了。
厨子接过徒弟递到手的刀片;习惯性地用拇指试了试锋口;然后像刮胡子一样刮起了狗毛。刀锋所到之处;泛起白条条的狗皮来。厨子说;刀锋落在皮上;不能轻也不能过重;别破了皮子。下手要快;毛皮凉了就刮不下来了。
徒弟在师傅的吩咐中点着头;却不太认真看刀锋和狗皮;他用心地看着师傅的手;师傅的手红中带着紫色;看来的确烫得不轻。狗毛热气腾腾;烫水在刀锋的起刮处不断地流出来;流过刀片流过师傅的手又流到地上。地上被烫水热起了水泡沫;水泡沫顺着地势又流过那关狗的铁笼子;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