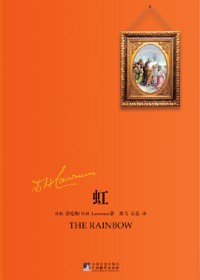人民文学0511-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妻子用指头点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受的这些苦你知不知道?
我的鼻子发酸。我说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妻子说;你知道就好;这辈子跟你我就认了;下辈子我可不干。
说罢;她又哈哈哈地笑起来。无论多难;她都永远是这么快乐。
笑过了;她才想起我之前是在为大嫂伤心;突然发现不该自己来诉苦的;于是说;你经常讲大嫂的好;可大嫂怎么个好法;你却从来没对我说过;反正睡不着;你就说一说嘛。
真要说大嫂;我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只讲了跟我有关的两件事情。
我念初中是在普光镇的一个半岛上;那不是镇中学;而是县里办在普光镇的一所学校。镇子西面的河坝是个猪牛市场;
从那里渡河过去;就是三面环水的半岛。半岛很大;夏秋两季;青纱帐一望无际。学校在半岛中央;离镇上的河码头有六七里地。我们那时候读书要交大米;一斤米再加一角多钱;才能领到一斤饭票。前半年是父亲给我送;我念初一下学期时大嫂嫁给了我大哥;自从嫁过来;给我扎鞋是她的事;去半岛送米送钱;照样是她的事。从我们村到镇上;上坡下坎的有二十五里;加半岛上的那一段;就是三十余里。每次大嫂都是天不亮就出发;到我们学校时;要是我还没放午学;她决不会到教室找我;而是蹲在教学楼外的洋槐树下等……
这里要说的;是我读初三那年;那是五月底;还有一个多月我就毕业了。那天放午学后;我看见洋槐树下吵吵嚷嚷的围了一大堆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多关心;就回寝室去了。
把饭打回来;听寝室的人讲;说有一个卖李子的妇女被学校的治安员打了。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的心就咯噔一声;我下意识地觉得那个妇女很可能就是我大嫂。
我把饭碗一放;就往教学楼外的洋槐树下跑。
人群外到处是被踩得稀烂的李子。我挤进去一看;心都碎了。
正是我的大嫂——大嫂嫁到我们家两年了;她为我们家所付出的牺牲;从嫁过来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我已经不仅仅把她看成大嫂;还看成了母亲。
大嫂的半边脸被打肿;紫红紫红的。她胸前的一颗纽扣也被扯掉了。而那个人高马大的治安员;还在跟她夺一把小秤。
大嫂双手紧紧地抓住秤杆;治安员每用一下力;她单薄的身体就摇晃几下;并伴随着一声尖叫。当她重新站稳;就求治安员不要把秤杆撇断了;她说这秤是她从镇上一个熟人那里借来的;撇断了她就要赔。治安员说像你这种不讲理的婆娘;不要说赔秤;赔人也该!
我不声不响地拾起地上的秤砣;猛地向治安员的胸膛上砸去。
秤砣刚脱我手;治安员见一团黑影朝他飞来;敏捷地跳开了。
我没有砸着他。
大嫂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她说你做啥呀!
治安员疑惑而尴尬地恨了我两眼;走了。他是认识我的;那是因为我成绩好;在一所规模不大的中学里;成绩特别拔尖的学生;连炊事员都认识。治安员平时还喜欢跟我说话;只要在路上遇见我;他都要拍拍我的头;说李夏至;你这娃娃有出息;好好学哟。
围观的人见无戏可看;都跑到食堂打饭去了。
大嫂蹲下身去捡李子。李子全都踩烂了;只要是烂掉半边的;大嫂都捡起来;放到背篼沿口上的竹筛里。大嫂这样捡了十来个;还把她胸前绷掉的那颗纽扣从一撮污泥里抠了出来。她说这李子是卖不掉的了;你拿回寝室去;洗一洗还可以吃;言毕就揣进我的荷包。我没说话。我看不清自己的表情;但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是铁青的。大嫂看出我心里想的还是那个治安员;她说;其实今天不怪他;我晓得你没钱用;就去姑姑家(她娘家姑姑;住在杨侯山上)摘了点李子来卖。李子有些涩口;镇上卖不脱手;我想学生娃可能喜欢吃;就背过来了。我哪晓得你们学校不准小商小贩进来呢;那个人站在远处吼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吼啥;还以为不是朝我吼呢;就没管他。他跑过来;一家伙就把筛子给我掀倒了;我骂了他两声;他才打我的。其实不怪他呀。
我的眼前;晃动着大嫂肿起来的半边脸;还有胸前掉了的那颗纽扣。大嫂的脸比开始肿得更高了;使她说话的声音也变了调。
她理了理我卷进去的衣领;说;要是你那一秤砣打在他身上;要出大事的;秤砣是铁的;哪能打人呢?要是你把人打伤了;学校会把你开除的。你都是要参加考试的人了。
开除就开除;我瓮声瓮气地说;我不读了!
大嫂变得严肃起来;她说这哪像你说的话?几匹山上的人都知道你成绩好;碰到爸爸都要谈起你;说你那个三儿子不得了呢;听说他写的作文都拿到县里去了;县文教局打印了好多份;发给全县的中学当范文呢!爸爸听到这话;心里有多舒坦;你想想他心里会有多舒坦!家里那么穷;可是穷不败;这是为啥?就因为有个想头!……今后;那种没出息的话不能再说了。
末了;大嫂问我;我看那个人不是被你手里的秤砣吓走的;他肯定认识你;他也知道你成绩好;是吧?
我说他知道。
早晓得;大嫂说;我该先就把我三弟的名字说出来;他就不会倒我的李子了。
那一刻;大嫂骄傲极了。
而我却流下了眼泪。
大嫂一面用粗糙的手掌为我擦泪;一面说;哭啥?没啥好哭的。人活一辈子;没有哪个逃得过三灾八难;我不过就是被人打了几下;又没打好狠;有啥了不起的?只是那二十多斤李子可惜了。不要哭了;免得被人看见;这多不好。
我当真不哭了。我把涌上来的眼泪;全都吞进了胃里。
大嫂说;你没啥钱了吧?我说还有。其实我已经好几顿没买过菜吃了。大嫂说;有?我不信!你先借来用着;我回去马上想法;过两天就给你送来。
她挎着背篼走了。
我多想留大嫂吃顿饭;但她是不会吃的;以往我每次留她吃饭;她都说自己一点儿也不饿。
我远远地跟着大嫂。半岛上是密集的玉米地;玉米秆有一人多高;在绿浪中穿行的大嫂;发现不了我。
我一直把大嫂送到了半岛边缘的码头上;我望见她渡过河去;上了猪牛市场;隐没于镇子石板街上的低矮房舍之间
我给妻子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我高考之后。
我念高中的学校;就是大嫂的小儿子清华正就读的县中。考试那几天我都是好好的;最后一堂考下来;我突然觉得不行了。头晕;胸痛;痛得像针刺。
是大哥和大嫂去县城接我的(那时候二哥早已结婚;大哥大嫂已分出去了);见此情形;他们都被吓住了。我的班主任老师说;没关系;可能是太劳累;送医院去检查一下。鉴于我肯定能考上大学;班主任提议不要去当时很混乱的县医院;直接送市医院算了。市区离我们县城只有两个小时车程。大哥送我走;大嫂回去借钱。那时候的医院还不像现在;只要没钱;病得要死也不能人院——那时候没钱是准许入院的;只是不能用药。住院的非常多;走廊上也搭满了钢丝床。我们在角落里放垃圾桶和痰盂的地方挤出了一块儿;搭了张床;忐忑不安地等大嫂。
大嫂第二天赶下来了;和她一起来的是父亲。交了钱;一检查;说我得的是胸膜炎;胸部积水很多。胸膜炎都是跟肺结核有牵连的;我的肺部已经感染了;只是不严重;但必须住院。
大哥和大嫂回去了;由父亲陪着我。大嫂借来的钱是很有限的;她说过十来天她再下来。
两天之后;一个中年女医生带着一群活蹦乱跳的实习生来抽了我胸部的积水;我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
医生给我输液;并观察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对我父亲说;你孩子可以出院了。父亲说;可以出院了吗?医生说可以了。父亲说我儿子今年考大学;肯定考得上;听说上学的时候还要检查;要是身体不过
关;被打回来了咋办?
不知是不是那医生的孩子也正考大学;她态度特别地慈祥;她说一百个放心;我说没事了就是没事了。随后给我开了个方子;说回去之后;照方子抓药;再吃一段时间。
我和父亲去办出院手续;结果还余下一点钱;够我们坐车回到镇上。
回去之后才知道;大嫂今天带着借来的钱去市医院了。我们错过了。
按理;大嫂当天夜间就该回来;但第二天没回来;第三天还是没回来;又没得个音信;就跟她这次去广东不和家里联系一样。不过那时候城里有家庭电话的也不多;山区农村就更不用说;大嫂想联系也没办法。我们一家人坐在房子旁边的一棵杏树底下;愁眉苦脸;又无计可施。父亲说;是不是有人谋害她呀?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嫂身上带着从大队部借来的两百块钱。大哥坐在那里哭;说夏至呀;这都是为了你呀!大哥并不是成心责怪我;他是担心糊涂了。二哥由于教了一阵子书又被取缔的事;本来对大嫂心生怨恨;但眼见她几天没有人影子;也着急得吃不下饭;不过他比我们都要冷静。他说;明天再等一天;如果明天还不回来;我就去市医院看看。大哥哭着说;去市医院有啥用;她一问就知道夏至出了院;就会离开了;肯定不在那里了。可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第二天;我们依然聚在杏树底下;空坐到黄昏时分;全都耷拉着脖子;没有人弄饭吃;也没有人开腔说话。心想这么多天了;完了。
就在这时候;二嫂突然叫一声:大嫂回来了!
十余米外的石梯上;冒出一张笑盈盈的脸;接着;大嫂披一身金色的霞光上来了。她的第一句话是:考上了;上重点线了!原来;她从市医院出来;直接去县中看我的考分去了。考分要过几天才下来;她就在那里等。晚上;她就睡在学校的花园里。这么几天过去;她只吃过三顿饭;都是二两一碗的挂面。
一家人处在喜庆之中;大哥却在恶毒地骂大嫂。
不管大哥怎样骂;大嫂都是傻兮兮地笑;满脸通红;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考上了;上重点线了……
大嫂果然在广东的工地上昏倒了。
热啊!在太阳坝干活;不要说她这种体质本来就差的女人;就是很强健的男人;照样可能脱水昏倒。
大嫂是在推斗车的时候突然倒下的。那里有一段斜坡;大嫂要把满满一斗车砖;从那斜坡推上去。大嫂双脚朝后蹬;把腰伏得很深;不仅手上用力;还用肩膀去顶斗车把。她的个子矮;这种姿势;使她的脸几乎贴到了地面上。地面是水泥路;被午后的太阳晒得亮晃晃的;好像燃烧起来了;而照在背部和后脑的太阳;仿佛就悬在屋檐那么高的位置。大嫂觉得自己不行了;她抬头想喊人;可那些人似乎离她都非常遥远;遥远得只有一个梦幻般的影子(其实不过二三十米);她心想那么远的人;怎么喊得应呢。再说她也没有精力喊;她把骨髓里的力量;都抠出来推斗车了;喊人就要泄气;一泄气她就完了。她没有经验;不知道人处在极端境遇的时候;连一丝一毫的杂念也是不能有的;有了杂念就会分心。斗车也怕热;本来就叫唤着不肯上行;猛然间发现推它的人没那么用劲了;便趁机往后退了两步。这一退;大嫂就要付出双倍的代价去稳住它。可她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呢;只不过两秒钟时间;她就偏偏倒倒地栽下去了。
斗车得到了解放;吱溜溜地朝后滑。
轮胎从大嫂的一条腿上碾过。
当斗车退到坡下的砖墙处;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工人们才看见发生的事情。
大嫂被送到了医院。她腿上被搓掉了一张皮;幸好骨头没被轧断。
没有人把这事告诉大哥;也没有人告诉我。大嫂肯定是不会打电话的(她怕家里人一知道;就会让她回去);胡贵也没打电话;胡贵不仅自己不打电话;还不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