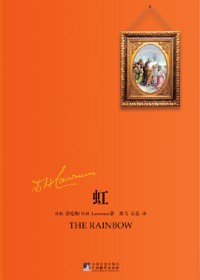人民文学0511-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到底还是把我想起来了。没听人说吗;铁不铁;就看你生病了想的是谁。”
秦阳依旧是没心没肺的;田田听了却是一怔;一时竟是无话。
田田得的是美尼尔综合症。发病时症状凶猛;医生下令暂时吊销驾驶执照半年。田田的住处离公车线有一段距离;早上赶车太急;秦阳就来接田田上班。接了几天;田田说你不如就在这儿住吧;省得天天起得这么早。
第二天秦阳果真就搬了进来。从此就没有再搬回去。
田田临回加拿大之前;在父亲的学校里给赵春枝找了一间房子暂且住下——是学校办外语培训班时给外地学员准备的宿舍。春枝和三个外地女学员一起住。房管处知道何淳安教授家里出了事;多少有些可怜老头子;便睁只眼闭只眼;由着去了。田田又去买了辆女式自行车;作为春枝在校园和家之间的交通工具。等拿着了房门钥匙和自行车钥匙;保姆赵春枝就正式走马上任了。
春枝早上骑车到何淳安教授家里;去小菜场买好一天的菜;准备早中晚三顿饭食;
收拾整理房间;清洗被褥衣物。何教授身体基本健康;行动方便;也极少挑口。何家的这一点简单家务;春枝弹琴似的顺过一遍;还没来得及调动所有的指头;就完成了。于是;春枝手里就剩下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春枝使用空闲时间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绣花。
春枝不绣寻常的花草鸳鸯;春枝绣的是西洋油画。春枝的绣花绷子很大;大得像一幅画。春枝把印刷品的油画贴在布上;就直接按着画上的颜色上针;深的上深色;浅的上浅色。不过春枝有时也不完全跟着画谱走;比方说;绣到房顶时;春枝用了很多金黄色的丝线。绣到树梢时明明应该用绿色;春枝却偏偏用了粉白。那黄的和白的乍看起来像是半空落下来的鸟屎;出跳而别扭地粘在屋顶和树枝之间。等到一幅画都绣完了;远远地挂在墙上;眯了眼睛细细地去品味;才发现那黄和那白的使得原本幽暗的景致里突然涌现出一片片瀑布似的阳光。
何淳安看了;愣了很久;才轻轻说了一声“没想到”。
春枝把剪子线团咚地一声扔回针线包里;笑了一笑;说没想到什么呢?没想到我们乡下人也有点艺术细胞;是不是?田田在京的那几天;春枝说话还有些顾忌。待田田一走;春枝就露出了真性情;想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何淳安辩解不得;只好呵呵地傻笑。
其实何淳安也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何淳安现在极少去学校。何淳安见不得众人那躲躲闪闪半是怜悯半是猜测的目光。那些目光如春日挂在树梢上的一抹飞丝;拿手指头轻轻一挑就断了。断在手上;看是看不见了;却缠缠绕绕总也感觉不甚清爽。
何淳安空闲的时候;就爱看书。何淳安看起书来;全然不是市井闲散之辈的那种看法;何淳安对看书的准备和姿势实在是很挑剔的。首先;茶是必备的。上好的毛尖;二遍茶——第一遍是要过滤倒掉的。其次;老花镜要仔仔细细地呵气擦拭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云雾。再者;躺椅的倾斜角度也是一个定数;要调到头颈和身子大致成四十五度角的那个位置。这些姿势排场都做过了;何淳安才能静下心来看书。心是静下来了;书却依旧看不下去。书里的字像是一块块黝黑的岩石;成团结伙地阻拦着何淳安的思绪。何淳安看懂了每一块岩石;何淳安却没有看懂山。何淳安的目光在岩石之间惶乱地走过几遭;就很是疲乏起来;睡意翩然而至;书咚地落到了地上。
春枝捡起书来;撩起衣襟擦了擦何淳安落在书上的口涎;看见封面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眉黑目深的高鼻梁西洋女人。女人的笑意很浅;嘴唇抿得紧紧的;神情有些寂寥。翻了翻书的内容;通篇上下竟没有一个中文字。正惊异间;突然想起老头子是教英文出身的;才忍不住咕的一声笑出声来。
这一笑;就把何淳安惊醒了。坐起来;一时不知身为何处。懵懵懂懂之间;突然叫了一声“延安”。叫完了;人就完全醒了。愣愣地呆了一会儿;才慢慢起身去了厕所。
嗒的一声;门从里边锁上了。一阵之后;就有了些叮咚的水声;接着就是哗哗的水声。再后来;就是一片长久的凝固不化的静寂。春枝听说过李延安是怎么死的;这时突然有些心悸;忍不住悄悄地走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屏着气听。谁知人还没有站稳;门却骤然开了;春枝身子一歪;几乎跌倒。何淳安扶住了春枝;叹了一口气;说:“她糊涂;我哪能也跟着她一般糊涂。”
春枝的心方咚地落到了实处;也叹了一口气;说:“别人说她糊涂;是不明白她;连你也跟着说。她哪是糊涂呢;她这明明是病。她病得这般苦;你既不能替她受这个苦;还不让她痛快地走。她走了;对你来说是舍不得;那是你的自私;她却是解放了呢。让你试试看;这样的病;苦得没个尽头没个解救的;放在你身上你受得了?”
何淳安却是从没听过别人这样劝解自己的。突然间;黑隧道般阴稠的心里;窄窄地流进了一线光亮;光亮之下;有纤尘细细地扬起。沉实了多日的心;开始有了第一丝的松动。
两人回到客厅;绣花的依旧绣花;看书的依旧看书。春枝将一根线头在嘴里含了半天;才吐出来;朝着何淳安手里的那本书努了努;问:“何老师;那个沃尔芙;文章写得好吗?”
何淳安吃了一惊;问你看得懂英文?春枝将脸涨红了;说就认得几个字而已。从前做事的那户人家;爱看录像带。有个电影;就是讲这个沃尔芙的;说是个有名的英国作家;投河死的。
“你说的那个电影叫《时光》;说的是沃尔芙死前的那一段。其实人家活着的时候就出大名了;倒是死了;却没怎么着。那年我去伦敦访问;下着大雨撑着把破伞去戈登广场找沃尔芙故居。找着了;连个牌子都没有。旁边那座房子;倒挂了个大牌子;说是某某某;赞助过沃尔芙的。连英国也这样;只记得阔佬;却不记得秀才。”
春枝扑哧笑了一声;说怎么不记得?何老师你看的是谁的书呢?阔佬有书留下来么?没听说人阔了就想买学位吗?可见秀才还是比阔佬稀罕些呢。
何淳安被春枝逗乐了;也跟着笑;说是呀是呀;那个沃尔芙;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人都得读她的书呀。她倒是很替你们女人说话的。就是她说的;女人想写书;首先得有自己的房间;再得有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她是说女人当自立——那都是女权主义的最初意识呢。
春枝撇了撇嘴;说女不女权的;我是不懂的;我只知道那女人长得倒是挺灵秀的。可是心里冷着呢;一条路黑冷到底;多好的男人都暖她不过来呢。
何淳安没有说话。过了好久;春枝抬起头来;才看见了老头颊上斑驳的泪痕。
李延安心里大约也是那样一条路黑冷到底;再也没有人可以暖她过来;才决定走了那样的极端吧?
可是;李延安年轻的时候;却是一枝火把;一盏灯;站在最暗的路口;也能毫不费力地照着自己照着别人。
何淳安认识李延安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他留校在外文系教欧美小说;她才刚刚分配进学校的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他偶然从别人嘴里听说了她父亲原来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才开始对她有了星点的好奇。在他那个人生阶段里;用“星点”来形容他对她的好奇;实在是恰到好处的。
那时他早已不是一张白纸了。
何淳安从小在教会学校里学的英文;口音里带着一丝牛津校园味;文章更是写得地道典雅。自小就将一应欧美名著看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时常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是外文系理所当然的业务尖子;却又没有洋文教授通常有的虚浮轻佻;行事为人很是稳重厚道;自然是讨女孩子欢喜的。在认识李延安之前;他曾有过两次恋爱经历;一次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另一次是他朋友的妹妹。然而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两个女人都却步了。他是侨乡来的;身世充满了故事;有许多近亲远亲在海外;所以他在系里;无论是提职还是提薪;都是落在最后的。他的两任女朋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离他而去的。
那两个女人;也绝非浅薄低俗之类;都是人中的尖子;花中的花。她们都很懂得他的优点。可是他的优点仿佛是伞;而他的身
世却是雨伞再好;也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雨。所以她们后来都选择了不需要伞的晴天。
这两次恋爱;他都爱得死去活来。到分手时;他觉得已经耗尽了他的心神。在那个凡事讲究简单纯洁的年代里;他的感情经历就算是复杂得有些可疑了。在那之后他再见到适婚的年轻女子;便有了尚未得到就已经害怕失去的焦虑。这份焦虑最初是隐隐约约;似有似无地藏在心中最深处的那个角落的;后来被年岁搅动着;零零星星地浮现上来;积在眼角眉梢鬓脚唇边;直到有一天;他在公共浴室的镜子前擦头发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有了第一缕的落魄和沧桑。
那天是何淳安二十五岁生日。他从学校的澡堂洗完澡出来;拎了一网兜换下来的脏衣服;行走在校园四月的暖春里;湿润的头发被风随意扬起;像一株盛开的蒲公英。而他那天的心境;也恰恰符合了蒲公英的比喻——从盛开到凋零;似乎只需要一阵风。二十五岁仿佛是一道坎;二十五岁之前;他有些不知不觉。过了二十五岁;他突然就感觉到了风的存在。
可是那天的李延安还是一叠白纸。十九页;页页雪白平整;毫无印记折皱。
那时李延安的父母已经结束了多年的戎马生涯;渐渐适应了安定的城市生活。当父母终于意识到子女的存在时;李延安已经像一根石头缝里的小草;自说自话地长成了一棵结实的小树。最好的学校最称职的老师都无济于事;李延安已经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对读书的兴趣。李延安留了一年级;才勉强初中毕业;却无论如何考不上高中;就在一家工厂里做了几年车床操作工。李延安虽然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一块读书的材料;却一直憧憬着在读书人的环境里工作。出于对女儿的内疚;李延安的父亲做了一生中唯一一件利用职权的事——把李延安安排进了大学的图书馆工作。然而李延安父亲的特权只行使到了图书馆门外;门内的一切;却是看李延安自己的造化了。李延安进入图书馆之后;名义上是管理员;很长的时间里其实都在做一个小工的事——搬运存书;清理书架;打扫卫生。数年以后;馆里来了更年轻的新人;她才调到了编目室工作。
那天何淳安洗完澡;就去学校的食堂吃了顿晚饭;又回宿舍翻了几页哈代的小说。终是无心无绪;便决定去图书馆找一本英国湖畔诗人的诗集。在过道上;他被一辆装满了书的手推车撞上了。车轮上的铁片直直地割进了他的脚踝;当时他只觉出了酥麻——疼痛是后来的事。他身子一矮;布袋似的软在了地上;手紧紧地捂住了脚踝。推车的女人连忙停下车来扶他;他却不肯松手。过了一会儿;就有液体从他的指缝里慢慢渗出;将他的袜子染成一幅紫红色的图画。旁边围观的人开始惊叫起来。女人拨开了他的手;一把扯下他的袜子;在他的脚踝上扎了个死死的结;就架着他去了学校的医务室。女人身量不高;他得倾斜着身体才能靠在她的肩上;可是那天他感觉仿佛是靠在一堵矮而结实的砖墙上;他竟放心踏实地在上面放上了自己的重量。
一直到处理完了伤口;他才有机会看了女人一眼。这一看;就看出很多意外来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她竟是那样年轻;年轻得几乎还不能称之为女人;衣妆发式眼神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