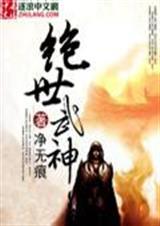芙蓉-2005年第4期-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气味。他梦想着易小小会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像一切雀跃而怀春的女子一样,蒙住自己喜欢的男人的眼睛。易小小当然没去,听人说华子常去河滨路,而且迅速消瘦下去,身体像冬天的树枝,衣服穿在身上,像挂在晾衣竿上,易小小只是沉默了半天……她肯定地认为,华子之所以至今不娶,是因为还爱着她,等着她,她也完全应该从梦境中走出来,把一些并未事先设计的计划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易小小的丈夫朱耳,却在学校找到了平静的精神领地。学校不仅每个月发给他七百元钱,还把五楼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他给高三美术班学生授课的教室,也成了下课后他私人的画室。这个学校每年高考,美术生上线人数占了全校上线人数的四分之一,因此校方一直比较重视。以前教高三美术的,是一个有三十年工龄的老教师,朱耳一来,杨校长亲自做主,让朱耳把老教师换了下来。学校对朱耳有大恩大德,朱耳心中有数,他决心带好这个毕业班,报答学校的恩情,也帮助他的弟子成才。因此,易小小心里所发生的变化,他一无所知。就连易小小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尽她所有的力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找了华子,他也全无知觉。
朱耳所用的那间特殊的教室里,除了一把椅子和一个写字台,没有一张桌椅,学生听讲都是站着。四周放满了学生的作品。作品倚墙而立,温暖的阳光,尖厉的野风,光灿的麦芒,宁静的菜园,和那些平凡的生活──平凡到清洁工清扫垃圾的场面──都在色块和线条之间颤颤流动。学生的风格就是朱耳的风格,永远关注现实,并在现实之中寻求简单的幸福和健康的理性。正对大门的墙面上,是朱耳为学生写的一段话:“同学们,当你们遇到麻烦时,要力图找出解决的办法,不要只是绝望地放弃。一定要摆脱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力求克服对失败的恐惧。你们不能以种种欺骗自己的借口来动摇自己的信心,最重要的课题,是思考怎样把一团颜料摆上白色的画布。你们真正需要的是勇气!”
这天,朱耳正在美术室给学生传授绘画的基本技法,杨校长推门而入,把一封信递给朱耳,然后说:“朱老师,川西生物教研会临时决定在我校召开,你弄几幅标语。”
“什么时候要?”
“今天必须弄好。人已聚在市里,明天到我们学校来。”
杨校长离去之后,朱耳把信放在一边,继续给学生上课:“我必须提醒大家,要尽力克服在使用颜料时的吝啬。你们往往将一丁点儿颜料挤在调色板上,又立即放回自己的画箱,用句行话说这叫‘饥饿的调色板’……除非你们学会慷慨而不浪费地使用颜料,当你把一种颜色与另一种颜色调和时,你的画才会产生一种颜色的气氛……”
学生们仔细揣摩着老师的话。尽管他们还谈不上艺术的创造,但是,他们已从老师的身上得到了良好的熏陶。他们都很崇敬自己的老师。这不仅因为他在当地的名声,他严谨的风格,还因为他苦难的人生和传奇的经历。他们知道老师曾挎着画板,到大巴山、秦岭、西双版纳和青藏高原写生。他不足一米六五的个子,登上过许许多多大山之巅。他的不少作品,都是在人烟稀绝的荒野或陌生的客栈里完成。他们还知道老师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在美院求学的两年中,他未接受过家里一分钱,周末和寒暑假,都混在浑身酸臭的人群里打零工,抬石头打灰浆烧砖窑什么都干过……
朱耳个人的天地是在学生下课之后。那张大写字台,他认为是杨校长有意放在那里为他提供方便的。据说杨校长年轻时侍弄过文学,懂得艺术家的穷困和艰辛。每天,朱耳总是很晚才回家。放学之后,他把美术室的门关上,整幢教学楼里,除了守门的师傅,就只有他了。墙角放着他的画布,他坐在地上盯着那块画布。画布像一只眼睛,与他对视着。他心灵的深处,沸腾着,燃烧着。当他无法承受心灵之重的时候,往往一跃而起,冲到画布前,让柳木炭条重重地在画布上流动。他感觉到炭条与画布摩擦时传递到指尖上的颤动。这是一首美妙无比的音乐!
这一天,学生离开之后,朱耳竟然忘记了杨校长的吩咐,他站在墙角望着窗外。窗外梧桐树繁密的叶片间,游走着四月的风声。他心里有许多美好的设想,但他懂得,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等定货,不等买主,而是今天,明天,永远——都在劳动,并养成劳苦的习惯,惟如此,设想才能和创造力打成一片。所谓灵感,就是意志力和长期观察所得到的结果,惟有艰苦的、诚实的劳动,才能拯救一个艺术家。朱耳收回目光,挨个儿巡视了学生的作品,并在教学笔记本上以漂亮的行书飞快地记录着什么,然后走到东墙边一幅一米见方的画布前,踌躇地拿起柳木炭条,思索片刻,他就飞快地划动起来──然而这不过是虚拟的动作,画布上并没留下一根线条。他不知是多少天面对这张空白的画布了,这张空白的画布给他带来难以言说的精神的痛苦。他要表现的东西太多,他企图在这张一米见方的空间里,浓缩他的理想、抗争、追求乃至生命。然而,那些东西都与时尚远离。他的才具似乎还不足以为他确立坚持的力量和坚定的信仰,这是他痛苦的根源。然而,如果让他丢掉作品中灵魂的因素,而去着意表现一些迎合的东西,就是拔掉了他心灵中的旗帜,他的劳动除了可以卖钱,就不具备任何价值。——如果是这样,那就不仅是痛苦,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他把门闭紧了,又坐在地板上思索。
刚刚坐下,就有人敲门了。朱耳打开一看,是总务室的小伍。小伍气忿忿地说:“朱耳,杨校长不是说你要来领纸么,现在都不来,我可就不管了!纸领不到,标语弄不出,由你自己负责!”说罢转身离去。
小伍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漂亮而狐媚,父母颇有家财,一心一意要把独生女盘出个模样儿,无奈小伍前世与书无缘,初中未毕业就不辞而别,与几个哥们姐们南下广东追求自由去了。两个月后,小伍垂头丧气回到父母身边,免不了一顿臭骂和痛打。可是,书是决不愿再读下去。学校也不敢接收说出走就出走的学生。尤其是女生。从此,小伍这个公司搞两天,那个商场混几日,在任何一家单位,都干不上一月。去年,她痛心疾首的父母调动种种关系,才为女儿在这所学校谋了个正式职工席位。父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在小伍看来,她这种漂亮姑娘,屈尊在一个学校的总务室发放纸张墨水粉笔帚帕之类,简直是苍天瞎眼!好在她常常迟到早退,甚至一天只上两小时班,也从没有人过问她,否则,她是忍受不下去的。
这时候,朱耳突然感到疲倦。可他不能迟疑。美术室在五楼,总务室在二楼,他知道只要稍稍慢了一点,尊贵的小姐就真会把门锁上,不再理他。他快步跟了下去。他想:你为什么不可以给我送上来呢?……待他下去,小伍已经到了底楼的大厅,纸被放在总务室外面的过道上。
朱耳将纸抱上楼去,就觉得站不住了。他一屁股坐在糊满各色颜料的椅子上,望着窗外的艳阳天。一只灰色的鸟儿,在梧桐树上鸣叫。叫了许久,没有同类的应声,便跳过横贯过来的枝桠,过渡到美术室的窗台上,温柔地看了屋角的朱耳两眼,展翅远去。
弄出几幅标语,说起来不复杂,可也不是件易事。除了纸自己裁,内容自己编,写好之后,还要在大门口和教学楼底楼牵绳子,把那斗大的字挂上去。来到这所学校之后,朱耳都是这么过来的,不仅写标语,每个办公室的“教师守则”,每间教室的“学生守则”,就连楼道里的“文明用语”,甚至厕所里诸如“请将便纸放入纸篓内,以防堵塞”一类的忠告,也是他用标准的魏碑写出并贴上去的。
把标语挂好,已是夜里九点多,朱耳回美术室放东西的时候,才发现放在写字台上没有拆封的信。他拿起信封一看,竟是加拿大寄来的,抽出信纸,全是英文,他的英文不地道,明白不了其中的意思,便下楼去,敲开了一个英语教师的门。
“你的画获奖了!”英语教师激动地说,同时把信高高举起,一字一顿地念道:“对你这位富有天才想象力的艺术家,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恭请你于×年×月×日光临多伦多德尔· 贝娄画廊参加授奖大会。”
朱耳不停地搓着手:“就这些?”
“另外是一些资料,介绍这次获奖画家的情况。对你的介绍是:‘朱耳,中国画家,代表作《母亲》。’”
朱耳的眼睛湿润了。正是这幅《母亲》,为他的流浪生活画上了句号。
见朱耳的眉宇间充满忧愁,英语教师问道:“获奖了,咋不高兴?”
朱耳说:“如果能去见识一下德尔·贝娄画廊的壮观场面,确实是我的心愿。但是,这样的奖只是个荣誉,没什么奖金,因此我是去不了的。”
英语教师理解地点了点头。朱耳把信收好,道了谢,就踏上了回家的路。四站公交车的路程,他总是步行。
一路沿锦江走去,夜色安静而慵懒地躺在河面。桥下的河水,幽深而灵动,无声无息地流向远方。朱耳想:如果用一个汽车轮胎做救生圈,我能沿着这条河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吗?
他在铁桥上又站了个把时辰。
“才回来?”朱耳刚进屋,坐在暗淡灯光下的母亲问。儿子朱无病躺在沙发上,病恹恹地睡着,嘴角残存着一片黄不拉叽的白菜叶。
“才回来。小小呢?”
母亲不回儿子的话,站起身,颤颤巍巍地去为儿子热饭菜。
“小小呢?”朱耳又问。
“管她呢!总是到哪里找野……”母亲说到这儿猛然打住。
朱耳脸上的肉抽搐了一下。
母亲痛惜地看了儿子一眼,说:“明天是周末,你把娃娃抱到医院抓两副中药。他一天吃不了二两饭,都瘦成一根蔫丝瓜了。”
朱耳看了看儿子,心里一阵刺痛。他把儿子放到了母亲的床上。
“咋这么晚才回来?”母亲问。
“为学校写了几幅标语,”朱耳说。他想把自己的作品在加拿大获奖的事告诉母亲,可他突然没有心情。
朱耳吃了很少一点儿饭。
母亲收罢碗筷,进屋睡觉去了。
易小小还没回来。
朱耳走到阳台上去,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他想把灯光下和暗影里的每一张面孔都辨认清楚。人们举着自己的脑袋,不断地涌出来,又不断地消逝。人声嗡嗡嘤嘤,像渺茫的涛声。后来,街道空阔起来,丝丝缕缕的孤独,摸不着,看不见,把街道缠住了。
易小小依然没回来。
朱耳一夜没睡,易小小一夜没回来。
天一亮,朱耳就把儿子抱去看医生。医生说,孩子有点贫血。什么都可以贫,就是不能贫血。朱耳回来一面老老实实地向母亲报告,一面把怀里的孩子放下来。
“奶奶,我的药。”无病吃力地抱住两袋中药。
母亲把药接过去,“我的孙孙会做事了。”
“妈,我想到学校去一趟。”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