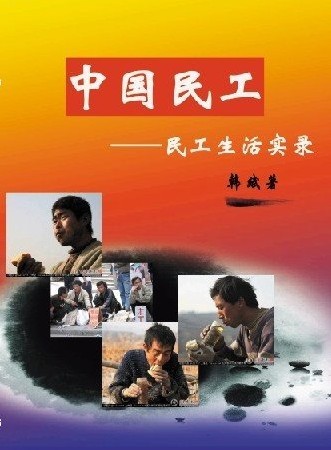一对农民夫妇的流浪生活:盲流-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苏桂芬的哭泣中还有感动,她觉得孙国民实在是太好了,一个人一生里能有这样一个男人为自己发这样的誓言,就足够了。
苏桂芬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孙国民,想安慰孙国民,想告诉孙国民,就是这样一辈子要饭,也觉得很好,要饭也没什么,从古到今,哪一代没有要饭的呢,有了难关不就是靠要饭过来的吗。凭什么自己嫁到要饭村就不能要饭呢。怎么会因为要饭而也不会小看自己的男人呢,但是苏桂芬有这样的想法,但不知道怎么说。
那天晚上在路边睡觉的时候,苏桂芬一手给栩栩扳脚丫子,一手用一本旧杂志给孙国民驱赶蚊子。
苏桂芬觉得只有这样做能让自己好受一些。也能让丈夫知道自己知道错了,自己后悔了,明白地告诉丈夫自己崇拜他,尊敬他。
此时孙国民如果想的也是这些的话,那他就不是孙国民了,他想的是如何快速地抵达那些有着无数工厂的城市,找到工作。而不是用脚一步步地丈量广东省的公路。
//
…
盲流46
…
孙国民和苏桂芬抱着孩子站在路边,看着路边呼啸而过的各种交通工具,孙国民的脑子开始飞速的转动,他想起了老家地边的那个小土地庙,当初就是祈祷那个土地庙才有了栩栩,正是那个土地庙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在全村人以及干部们的面前活出了尊严。
孙国民决定再次祈祷,祈祷一个愿意帮助自己的好心人停下车来。把自己捎上。想到这里,孙国民脸就红了起来,这样想,多不好意思呀,人家开车都是为了赚钱的,白捎上自己。实在不好意思,想到这里又想起了阿东,阿东为了自己挨了那样一顿打,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感激人家。现在又要白搭人家的车。要是人家不答应还好一点,要是答应了。该怎么谢人呢。
想着,孙国民看看栩栩,又换了个想法,自己也不是白搭人家的车,车闲着也是闲着,又不在乎多三个人,况且如果不搭车,自己和栩栩还有苏桂芬确实很难抵达目的地。
正想着,一辆货车停了下来。其实孙国民和苏桂芬并没有勇气招手,而是侧身抱着孩子站在公路旁边。
一辆香港的货车司机停下车来,驾驶室里两个人,另一个人趴在车窗上看看苏桂芬和孙国民还有他们抱着的栩栩。
因为语言不通,孙国民说的安徽江北方言司机听不懂,司机说的蹩脚普通话,孙国民也听不懂,但意思大家都是知道的。
孙国民和苏桂芬搭乘这辆货车开始了新的旅程。
路上,司机和副驾驶还下车吃了顿饭,也捎上了孙国民和苏桂芬。依然是语言不通,但意思都是明白的,苏桂芬不知道该不该吃人家请的饭菜,扭头看孙国民,孙国民脑海里还想着家乡的那个土地爷爷。
心里想,家乡的土地真灵验啊。
苏桂芬捅了捅孙国民,孙国民才开始想,到底该不该吃人家的饭菜。由于饿的缘故,孙国民的脑海里经过了最简短的思考,以最快的速度说服了自己,必须吃,因为这是别人主动请自己的,算不上要饭。只有自己主动向别人要,那才叫讨饭。饭间,又是手语,又是难以沟通的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孙国民大致说清楚了要去的地方和目的。
车到东莞,司机下车在路边的一个小超市里给栩栩买了好几袋奶粉。还往栩栩的怀里塞了三百块钱。
苏桂芬吓了一跳,赶紧回头看孙国民,孙国民也吓了一跳,还没等自己做出判断。两个司机已经上车走了。
虽然语言不通,但从他们的动作和语气上,孙国民听出来他们有事情,很着急,要急着走,让他们自己保重。
孙国民看着苏桂芬那着三百块钱的那个困惑和焦急的神情,赶紧把刚才的那个关于给和要的区别的话重新叙述了一遍,苏桂芬这才塌实下来,其实苏桂芬也知道孙国民会这样告诉自己,但是孙国民不说出来,她就不好受,说出来了,心里就坦然。
货车司机把孙国民夫妇放下的地方是一个工厂的旁边,正是傍晚,路边有大排挡,三三两两的一看就是打工的人在散步和吃饭。孙国民激动不已。因为车还没进东莞城区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工厂,车慢的时候看到这些工厂的大门口都张贴着招工的启示,要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当时就想让司机停车,下去。
离孙国民几百米外就有一个工厂的大门,很气派的门,门上写着中文还有外文。孙国民想明天肯定不能就这样去找工,应该找个小水塘,好好把自己洗干净,把自己的衣服也洗干净,然后干干净净地找工。
孙国民想,自己能干什么呢。当然工厂一定需要技术,但一定也有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做卫生,看夜。要是人家不需要没技术的工人,也没关系,那么多的工厂,《半月谈》上都说了,有那样多的工厂,书上都说了,还能错的了。还能没有孙国民干活的地方。
孙国民想着想着,就激动起来。猛地呼吸一口南方潮湿而温暖的空气,高兴的很不得马上就大笑几声。恨不得马上就找到一个小水塘,把自己洗干净。
忽然间,前面有人转身奔跑,孙国民正张望呢,几个年轻的治安员出现在孙国民和苏桂芬的面前。
查暂住证。
//
…
盲流47
…
孙国民和苏桂芬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送往樟木头,在那里干了一个月的活,之后被遣送回安徽。两人在浙江的金华下了车。
后来又辗转去了湖北、湖南,山东、江西、海南岛、吐鲁番等地。都因为身份的原因没能扎住根。只能四处流浪。几年来,虽然吃了不少的苦,但有一件最让孙国民夫妇欣慰的事情,也是更加令苏桂芬崇拜自己的丈夫的奇迹发生了,由于他们数年里坚持不分昼夜给孩子扳脚丫子,孩子的脚丫子已经恢复到可以正常穿鞋,正常行走。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这曾经是一只残疾的脚。
栩栩六岁那年,他们在湖北的武汉稳定下来,稳定的原因是认识了一个叫大柱的流浪儿,这个大柱自幼父母离异,无人管教,还随身带着一个七岁的弟弟二柱,这个弟弟是同母异父的弟弟,父母酗酒、赌博,分别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一个坐牢去了,另一个不知下落。出来两年半,认识孙国民夫妇的时候已经十五岁了,身边竟然聚集了十多个身世相似的流浪儿,有的比大柱还大三、四岁,由于大柱天生的领导能力和聪明异常加上为人丈义,竟然死心塌地地跟着这个十五岁的少年。
大柱的那些十来个手下,长期游荡在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以及百货大楼和商业区附近乞讨。这些孩子将乞讨来的钱交给大柱,而大柱则替这些孩子了结“道”上的困难。和各种人周旋。俨然一个说话落地有声的头目。
大柱身材瘦小,乍看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一对警惕而透着灵气的大眼睛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是个平常的孩子,据说有不少“道”上的朋友都喜欢这个大柱,这也是大柱小小年纪能够指挥的动十多个人并且能在“道”上混下去的重要原因。从面相上看,大柱绝对是个老江湖的面相,说话做事老道而熟练,但毕竟年纪还小,仔细看,总是可以看的到童稚的一面。
大柱是在湖南岳阳郊区的一片小树林里认识了孙国民夫妇。
大柱那天在长江边的小树林里休息,孙国民夫妇也在那里,拾废品,正好日头太烈,怕晒着栩栩,就在小树林里歇一会儿。栩栩看见那里躺着一个人,就跑过去。蹲在大柱的旁边。
大柱说:“哪里来的小丫头啊。”
栩栩说:“我是栩栩啊。”
孙国民赶紧跑过来,一把抱起栩栩,连连对大柱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
大柱说:“没事,这个小丫头真是可爱啊。怎么跟着你们拣破烂啊。多可惜。”
孙国民和苏桂芬的脸顿时通红。
搭讪中,大柱建议孙国民和苏桂芬带着栩栩在岳阳讨钱,或者去长沙,或者去武汉。这样比拣破烂要强的多,而且可以让栩栩在夜市上卖玫瑰花,就能赚大钱了。有很多湖南的乞丐都让孩子在夜市上卖花,专卖给年轻的情侣,挺赚钱的。
大柱的建议被孙国民否决了。虽然交流的话语不多,但大柱倒是比较能理解孙国民的想法。因为大柱讲了一点他对流浪以及钱的看法,让孙国民很佩服。这一点,很少有人理解过大柱,所以大柱觉得孙国民是个好人。这感觉很奇怪,长期在外流浪的大柱已经养成了一个生存习惯,就是不和任何人交心,无论什么条件下,都不会和人说实话。但和孙国民则不一样。大柱觉得孙国民不是一般人,至少和一般人不一样。因为孙国民肯耐心地听自己说,而且还会表现出确实理解自己的态度来。大柱就能够理解孙国民的想法。这个感觉是用语言难以表达出来的。
大柱不贪财,他手下十多个孩子要来了钱,天天就买些好吃的大家吃光,从来也不攒,大柱对孩子们也很好,所以孩子们都愿意跟着大柱。这些孩子有的是不愿意上学而离家出走的,有的是父母双亡而无人照看的,有的是遭受父母或者亲人虐待的。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七岁,平时聚集在大柱身边,靠乞讨和流浪为生。在大柱的领导下集体行动,集体谋生,互相有个照应。
大柱从不亏待自己的弟弟二柱,也不亏待跟着他的那些孩子们,到手的钱从来也不留,都花光吃光。他的仗义让孙国民佩服的了不得,因为孙国民向来吝啬,从不舍得花钱,栩栩五岁了,从未吃过糖和冰棍什么的,有一次栩栩在马路边看别人吃冰棍,也要吃,孙国民舍不得买,告诉栩栩那是药。苦的。
大柱和孙国民聊起流浪的苦乐酸甜时,大柱说,流浪在别人看特别苦,但他觉得很快乐,没有烦心事,没有人管,也不用管别人,自由自在,尤其是独自一个人躺在小树林的时候,听着小鸟的叫声,自己没有一点牵挂,那时的感觉才真的是棒。不过,也有不爽的地方,就是下雨找不到住的地方,别人的白眼,有的时候抢地盘干不过别人的时候就得挨打,还有饿肚子,蚊子咬还有挨冻以及没有钱的那些日子不好受。
如果不想钱的话,大多数都挺快乐的。
这一点和孙国民想的是一样的。
大柱和孙国民一家相处的那些日子,每天四处乞讨的孩子们回到小树林里,带着钱和各种各样的食物,象一个大家庭一样,只是孙国民和苏桂芬和孩子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吃他们的东西,也告戒栩栩不吃他们的东西。
大柱非要给栩栩吃,栩栩说:“我爸我妈不让我吃你给的东西。”
弟弟二柱和栩栩玩的非常好,每天,竟然不愿意跟着大家出去要钱,而愿意跟着栩栩玩。有的时候竟然学着栩栩喊孙国民夫妇爸爸和妈妈。
最触动大柱的是,那天二柱竟然也学着栩栩不吃大柱给的东西了。二柱学着栩栩说:“我爸我妈不让我吃你给的东西。”这句话深深打动了这个已经有着两年半流浪史并且手下聚集了十多个流浪少年的心,大柱忽然间开始想念自己的亲人,也想象栩栩那样叫爸爸和妈妈,大柱掐着指头算出记忆里最疼自己的人,是他奶奶。他还有个奶奶在湖北的武汉,他记得奶奶在武汉的郊外养了很多鸡。
想到这里大





![三只鸳鸯一对半[出书版]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