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比尔-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分,说评得不公,并且,有一种流言开始流传,那就是三中队评为第一名,是因为
队长们鼓励她们,让她们早日改造完毕。而这一切,却都使人们变得天真和纯洁了,
无论是干部还是劳教。
歌咏比赛结束了,劳教们进了工场继续做活。干部们下班回家了,汽车在路上
颠簸,落日在后窗上冉冉下沉,女孩们长久地快乐地议论着歌咏比赛的事情,这给
队长们带来的快乐是和带给劳教们同样多的。我感动地想道:在这里尚保留着一片
圣洁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负了十字架的革命者从热闹的上海,来到了偏僻
荒芜的丘陵,披荆斩棘,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以他们那虽然受挫却依然虔诚
的信念牢牢卫护着一支朗朗的行进着的队列歌曲。他们三十年来,几乎一直过着类
似供给制的生活,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一次进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惊异他说道:
上海有那么多的供应站啊!甚至三十年来,们还能完好地保留着上海的口音,而没
有被四下包围着的皖南口音异化,再甚至还稍稍地、隐隐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对外
地人的小偏见。它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而这些女人们却带着上海最阴暗的角落里
的故事,来到这土地上。她们来了两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创造新的故
事,又有一批女人带了最近的奇异而丑陋的故事来到这里。这些故事好像水从河床
里流淌似的绵绵不断,从这里流去,留下了永远的河床。
在那初次来到的暴热的晚上,有一位队长对我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这
一些,有没有意义。她的脸隐在幽暗的灯影里,看上去有些软弱。我鼓励她道:
“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的劳动使一些人变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你们相
信吗?”“我想,我是相信的。”因为那是初来的日子,我这样回答。“有时候送
了一个人走,很快又接了她进来,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她忧伤地转过脸,
沉默了很久。她的父亲是最早来到白茅岭的公安干部,那都是一些带了错误,怀了
赎罪心情来到此地的开垦者。她又想说她父亲的事情,张张嘴又打消了念头,算了。
过了一会儿,她转回眼睛,说:在这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我问,在这里,
面对了劳教和犯人,你会觉得你比他们都强,都胜利,你的心里就平衡了。我心里
奇异地感动了一下,我想,她是将我当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了这样深刻而诚实的心
情。那一个夜晚,是令人难忘的,月亮很炎热地悬在空中,四下里都是昆虫的歌唱。
白茅岭的采访应当到此结束了,可是过后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记录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记着那个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为她的申
诉提供帮助,她绝望的神情使我们耿耿于怀。他通过一些朋友关系在公安分局找到
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记录的材料是惊人的,无法为她开脱,她对我们说了谎,效果
还相当成功。这使我们对白茅岭得来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们也许是虔诚而
感动地一个接一个一共听了十几位女人的谎言,便觉得事情十分滑稽,却也难免十
分沮丧。
第二件事是我们受托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后遇到种种挫
折,受人歧视,她曾先后来过两封信给过去的队长,前封信说:我如不是想到队长
你,我就又要进去了!后封信说:假如我又做了坏事,队长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实
在太难了。我们十分周折地在一个菜市场后面嘈杂拥挤的平房里找到了她,递给她
我们的名片,说如有什么困难,可来找我们。她瞥了一眼名片,说:你们是作家,
作家就只能写几篇文章,登在报刊上,便完了,你们帮不了我什么的。我说我们愿
意试一试。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们是幸福的人,不像我们,我们只有去买
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觉得很幸福。你们以后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
如经常来这种地方,会变得残酷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从门里走出
来看我们,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来。在这些前后挨得很近,以至长年照不进阳光的
房子里,有些什么样的生计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觉得罪恶离这里很近,只在
咫尺之间。犯罪在这里,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稍一失足,
便堕入了另一个世界里。离开她家,我们上了汽车,红绿灯在路上闪耀。
白茅岭的故事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我会在街上、电影院里、音
乐茶座上,或者某地的宾馆里,又遇上我们所采访过的劳教们,她们将穿了全新的
服装,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也许会认不出我们或者装作认不出
我们,我们又将对她们说些什么呢?我编织着这种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笔记本上还
记录着她们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过去看看她们中的某人,可是这些念头
转瞬即逝,我想我是没有权利在上海去打扰她们的,对于她们,白茅岭已是过去的
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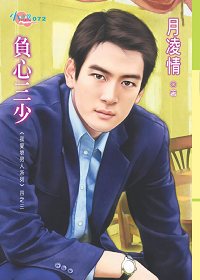



![[足坛]如果我爱你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5/555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