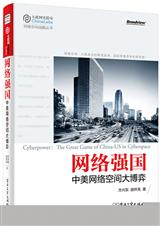配方博弈-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足。这样的组织,如何能战斗?”
她不知道方兴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只得应付道:“是的。不能战斗。”
“你们这代人,知识结构要比我们这代人合理。你们会外语、计算机,还懂得证券、法律。我们那时候,学的尽是些没用的东西。但有一点我们要比你们强,那就是对人性看得比你们透。”他喝了一口水,“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战争中学习战争。观察一个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跟搞科学试验一样,要不停地监测。隔一阵,就要取一个数据出来。‘文革》时期,家父被关押。有一次,我和弟弟实在没钱花了,就偷偷撕开造反派贴的封条,潜入家中偷出老爷子的一副金丝眼镜去卖。眼镜店的师傅一看,就说是铜的。我们兄弟不服,这个老头就说:你们不信,咱们就剪断它,放在试金石上试验。我们同意了。在试金石上一试,果然和金子划出来的道不一样。”他顿了一下,“我说了这么半天,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
她见他的目光,很明确地落在她的纸巾上,立刻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我顺便在北海茶道喝了点儿茶。”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独自在茶馆喝茶。”他说罢,把目光移开。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碰到了一个朋友。”
“偶然碰到的,还是预约的?”
“以前约过,这两天一直在这里搞方案,没时间见。”她模棱两可地回答。
“不要说去茶馆,就是去旅馆开房间,也是你的自由。你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任何人,你只属于你自己。你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所要告诉你的仅仅是:在工作上,你我应该以诚相待。”他说罢,继续看书。
她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不敢走开。
今天是中考的日子,张琴和周鞍钢专程送周小擎到学校。
在车上,张琴非要周小擎再看看书。见他不肯,就说:“孔子都说,学而时习之。功课就要温习,这是大道理、硬道理。”
周小擎不服气地说:“这话够傻的。谁不知道?老爸,你说对不对?”
周鞍钢当然知道孔子所谓的“学”是理论的意思,“习”则是实践的意思。联起来就是有了理论,就要反复实践。但他不会去纠正。
下车到了校门口,张琴又说:“考卷发下来,先写名字。”
周小擎更不耐烦了:“知道了,知道了!”
她虽然不高兴,但不敢说别的:“你就会说,知道了。”
“皇帝在奏折上,最常批的就是这三个字。大白话最有力量!”他知道此刻不该给儿子施加压力,“不就是场考试吗?别紧张。”
“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丁小莉,学习特别的好。可一到考试就紧张。毕业考的时候,竟然用左手写起字来。做了一半,才被老师发现。”见母亲又担心,周小擎不以为然地说;“我不会,我的心理素质特别好。”
她把一块巧克力递给周小擎:“别人都说有恃无恐。有恃才能无恐,‘恃》说的就是实力。”
“你别说了。无恃无恐,总比无恃有恐好。”他摆手,将儿子释放。
她见儿子走远,对丈夫说:“你我任重道远啊!”
“以后不懂,就别瞎说。幸亏你不是老师,否则你误己子弟不算,还要误人子弟。”
张琴感觉自己的话可能有错,便问:“这话莫非不是任务重,担子重,道路又遥远的意思?”
“刚才你就犯了一个错误,你儿子都明白,孔子不会说这么傻的话。”他讲解“学而时习之”的含义后又说,“这个‘任》使命的意思。‘道》是终极道理的意思。联起来就是追求‘道》的‘士》的使命重大,终极道理又永远追求不到。”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德国军事家毛奇说得好,一场战争,在初始阶段犯下的错误,终局不能扭转。”
林恕洗了一个痛快的桑拿之后,换上全套的新衣服,神闲气定地进入秦芳的房间。随后,简略地向她讲述过程:“你一定想不到,这个老家伙竟然首先发起攻击。”他拿起桌子上的一把裁纸刀,“但业余得很,刀尖朝外,刀背朝上,就和电影中鬼子进村,端刺刀的架势一模一样。”见她不解,他示范道,“应该让刀和手掌成九十度直角,刀尖朝下。这样才不会被别人夺去。”
她关心尸体的处理。听他说扔到江里面去了,不由地想起金秋子:“尸体一旦被捞起来,咱们可就危险了。袁因离KG太近了。”
“我在里面,放了一块铸铁。”
“万一漂起来呢?”
“就算漂起来,谁知道奔腾咆哮的江水会把他带到哪去!”
“无论漂到哪里,都是问题。天下公安是一家。”
“假设尸体没有漂入大海,在五十公里处被捞起来了。当地的公安,就要发通告。这时,宁水的公安就会看见。但看见不等于认出来。尸体一泡,必定变形。就算认出来了,也不一定会和KG联系在一起。就算联系在一起,也不一定注意到咱们。就算注意到咱们,咱们肯定已经把配方搞到手,开路了。”
她平静下来后,问配方是否到手。
“像袁因这样的人,如果有配方,早就拿出来换女儿了。配方和样品一定在李帅手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你在李帅身上,下的工夫也不少了。炆火炖肉,该揭锅盖的时候,就要揭锅盖。”
“什么时候该揭,我心里清楚。”她明白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听他强调行动必须统一。她又说:“这要看往哪统一了。”
他阴沉着脸,没再说话。
因为袁因失踪,周鞍钢召开了紧急会议。
徐纲首先发言,认为袁因一定携带配方和样品出逃,应立刻发通缉令。
那红却认为通过阅读袁因的材料,感觉应该不会:“他上学、毕业、结婚、进宁水市药物研究所工作。后来研究所改制,他就进了隆德药业,足迹一直就在宁水。他的社会关系也极其简单。我认为,这样的人,不具备出逃的条件。或者说,他没有能力出逃。”接着,她分析了出逃的必备条件,“出逃的人,大体上可分为两种:贪官和普通刑事犯罪的人。首先说说普通刑事罪犯。他们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激情杀人。因为一件事,一时冲动,发生了命案。这之后,他们也很害怕。不是投案自首,就是束手就擒。而另一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就会出逃。因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有组织的。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有后勤支援。这些人出逃,不以国外为目的。多在境内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而贪官则分两种。一种是仓皇出逃,这种人通常随身携带巨款,但是孤家寡人,因仓皇而出错,所以多数会落网。还有一种人,就像海南国际开发银行的行长汪明一样,是早有准备的。这包括经济上的准备,钱早已经分别转入若干个国家的若干个银行。组织上的准备也是充足的,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接应,路线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有若干条:广西、云南,甚至内蒙、西藏。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若干本护照,很多、很多的身份证。”
徐纲反驳:“按照你的分类,袁因属于仓皇出逃的那种。”
“那他的经济支持在什么地方?”见他回答不上来,她又说,“我调查了他的信用卡和银行存款,一切都很正常。再说,像他这样的规矩人,就算跑也跑不远。他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弄假身份证,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住。不要身份证的桑拿浴室、鸡毛小店等等,对他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
徐纲将“袁因的女儿在美国”这一支持,摆到桌面上。
她早有准备:“这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我用若干种方式,与他的女儿联系,但都没能联系上。昨天午夜,我联系上麻省理工学院。学院的有关部门说,她已经有一个来月没有来上学了。”
“一个来月。”周鞍钢感觉触到问题的关键,“一定与KG有关!”他立刻命令徐纲通过公安部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调袁因女儿袁小雨的电话单。
周小擎背着书包,大大咧咧地与同学说笑着从学校的大门出来。可一见张琴,顿时不高兴地问:“您怎么来了?”
“来接你啊!”张琴其实就没走,一直在校门口望眼欲穿。
周小擎不高兴地说:“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你就是三百岁,也是我儿子。”张琴把他搂过去,不理会他挣脱的企图,对他的同学说,“你们先走吧。”等同学走开后,她关切地问:“考得怎么样?”
“会的都做了,不知道对不对。”周小擎没好气地说完后问,“我爸没来?”
“别提你爸。一提你爸,我就来气。你爸的老婆是检察院,儿子是案件。”
周小擎却高兴地说:“古人说,梅妻鹤子。是高人的表现。”听母亲问这话是否又是从金庸小说里看来的。他说:“凡是有您不知道的事,您就往金庸那说。要是金庸听见了,非得跟您急了不可。”
“我还跟他急呢!”她无法在这方面与儿子论争,“刚才我说你爸,说到哪了?”
周小擎径自往前走:“您说话又没有什么逻辑性,谁记得住?”
张琴跟在后面:“凡是你的事,你爸从来就没管过。怀着你的时候,他一直忙一个大案子,一口饭也没给我做过。你还一个劲儿地在肚子里乱踢。那天半夜,我肚子疼得厉害,就叫他陪我去医院。你猜他说的什么?”
“说什么?”
张琴学着周鞍钢的腔调说:“你不能忍着点,明天再说。”见他笑,又说,“还有一次。”
周小擎不耐烦地大步往前走:“这些陈年老账,您就别说了。等我有能力了,一定让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那我不就成了地主了?”
周小擎大步前行。张琴只好紧追。
晚上十点,美方的结果来了。
周鞍钢仔细看完后说:“对照刚才的袁因的电话记录,几乎可以肯定袁因的女儿袁小雨,被人绑架了。”他指点着若干张记录说,“平常袁因几乎三天一个电话,很少有例外。但在一个半月前,突然就没有了,一个也没有了。”
徐纲重提袁因出逃说:“袁小雨也是学化学的,可能父女共谋。”
“联系的中断,是在KG最后一次试验之前。这说明,有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要利用他女儿威胁他。”
“可具体目标,一个也没有。唯一一个,还给丢了。”徐纲急躁地说。
“要戒急用忍。”周鞍钢拍拍他的肩膀。
正在这时,张琴来电话说,儿子明天要考英文,要他回去辅导。他应付了一下后说:“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找到袁因,我去和公安方面联系。”接着,他否决了徐纲要去的请求,“还是我去吧,我去分量重一些。”徐纲当然承认周鞍钢的分量重,但提醒他注意张琴刚才的电话。他边收拾东西边说,“我儿子的学习我知道,辅导不辅导没关系。”
那红插话:“一定能考上?”
他穿上外衣说:“一定能考上的反面。”
那红关灯又说:“我听别人说,你当年曾经是八一中学第一名的学生。很会念书。”
他不无得意地说:“这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