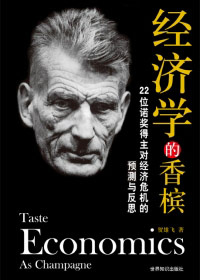感情经济学:教你如何开掘幸福原动力-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桓隽餍幸衾置缘氖焙颍琕ictor不断放他喜欢的CD,像一个优秀的音乐DJ。最终,我们在王菲的《乘客》中流连忘返:
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这旅程不曲折/一转眼就到了/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我们好快乐……
我是一个28岁的单身女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终于在京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却始终没有一份不错的感情眷顾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发现,自己太需要一个港湾,哪怕是一个临时的男人的臂膀。
那天我像跟屁虫一样追随Victor左右。Victor说他每周都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基本是一个“户外男人”。也许见多了常年呆在空调办公室里因为缺少日照而面色苍白的白领男,我对这个皮肤有些粗糙、相貌一般的“户外男人”颇有好感。
那天爬完山,本来有聚餐,可是Victor却带着我“逃之夭夭”了。
我们直抵嘉里中心附近一个叫“金涛湾”的餐厅。Victor选择的越南菜正是我的最爱。
席间,Victor一直在摆弄他的银色打火机。我猜他是个瘾君子。Victor却说:“其实我不怎么抽烟,但我喜欢带两样东西在身上。一是钥匙,它能保证我可以进家门;第二就是打火机,他能保证我每打必着……”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Victor一语双关地说:“送男人最好的礼物,不是领带,也不是钱夹,而是打火机。”
正巧女友云不但是一个女烟民,同时也刚好是一个打火机爱好者。所以我很容易地就“借用”了她那段著名的理论。
我不急不慢地对Victor说:“爱用银色火机的男人比较安静内秀,心思浪漫而细腻;爱用金色火机的男人性格外向,追求奢华、喜欢炫耀;而喜欢另类色彩如紫灰或黑色的,则多半个性独特,并以自己的独特为荣。”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方程式9:男人精 捂紧口袋说“爱你”(3)
Victor听罢颇显吃惊,他看着我问:“你哪里得来的这套理论?”
我清了清嗓子,学着女巫般的语调说:“男人喜欢打火机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行为。男人喜欢掌握、操纵一些事物,崇尚运筹帷幄、易如反掌的感觉。但非常遗憾的是,社会不能为太多的男人创造这种机会,于是小小一只打火机就成为男人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一个把打火机紧紧抓在手里的男人,表面上看不动声色,其实他的内心是焦虑不安的,对他而言,世界太大,欲望太多,当他心理脆弱的时候,唯一能牢牢把握的,可能也只有这一只打火机了。”
显然,我移花接木的这套“打火机理论”,让Victor对我刮目相看。
结账的时候,小姐把账单递给Victor,只见Victor掏出几张代金券递给了服务员小姐。
那顿晚餐吃得心花怒放。结果是那天晚上,我被这个“心花”牵着,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切。
那是Victor一个出国朋友的房子。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周日都与Victor一起去爬山,然后就是我们一起失踪。
每次见面,我都会送Victor一些礼物,以打火机为主。渐渐地,见面的时候,Victor会很自然地流露出类似的信息:你很会穿衣服,什么时候也给我买几件?你的太阳镜很时尚,也帮我买一副同样品牌的?今天你请我吃什么啊?……此时,我把这些信号当作是我们关系亲密的认定。
4月28日是Victor的生日,我送他的是韩国版的价值299元的Zippo打火机——银灰色的机身,斜排着三排心型图案,只有一个是粉红色的。我说那颗代表我的心。
但是随着交往的加深,我发现自己是只出不进。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结账时Victor掏钱包的速度总是慢半拍,这让我屡屡感觉不爽。
男女交往就像一个天平,讲的就是平等,有来有往,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金钱上。当你越来越多地付出而他对你却“每况愈下”,那么可以断定,此情不可待。
有时我会把不满情绪表现出来,Victor总是口口声声地说:“我的还不都是你的。”
再后来,他的那个朋友回国了,我们也失去了秘密据点。这时候,我已经有点离不开Victor了。但当我提出见面时,他居然说:“好啊,你找好地方通知我!”
这个号称年薪20万的男人,就是这样温柔地给了我致命的一刀!
还好我不是那种一棵树上吊死的傻女人,当然是毅然决然地了断了这段感情。Victor不解地问:“天地良心,我对你怎样!”但是此时我已经认定——那纯属谎言。
所以,当女人发现一个男人一边说“我爱你”,一边捂紧自己的口袋时,一定要及时为爱踩刹车,不然结局可能是人财两空。
一网打尽四种“男人精”
女友曾遇上一位帅哥,两人一遇见就火花四溅。但不出几日,女友发现帅哥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每到要掏钱之时,就一脸藏也藏不住的小家子气。如此几次,女友心里的爱情已去了大半,随后坚决了断了这场美丽的邂逅。
虽然金钱不能代表爱情,但是仍然不失为情感的试金石之一。
我们说的“男人精”跟节俭型男人不是一回事。节俭是一种美德,而“男人精”是千方百计算计你,占你的便宜。生逢“男人精”辈出的时代,女人的确要擦亮眼睛了。
菜鸟型
在网上论坛经常可以看到条件优越的男大学生,希望找一个大姐级女友做朋友。这种男人可以说是新生代的男人精,他们来势汹汹,期待不劳而获,说白了就是未来的寄生虫。他们一般有年龄、相貌或者艺术天分上的优势,而那些母性情结比较严重或者有一定经济基础却情感荒凉的大女人,容易为之动容。
守财奴型
这种男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葛朗台。他们通常出身贫寒,小气吝啬是他们的习惯。如果你和他正在恋爱,不妨扪心自问:他的小气我能忍受吗?如果你对两个人的未来并不看好,就干脆和他说“拜拜”。因为女人跟着这样的男人也只是如同守着一个守财奴过日子,他可能很会赚钱,很会算计,但就是不会生活。
猥琐型
这类男人总是不那么坦荡。他挣钱不比你少,但总是遮遮掩掩,小里小气。每到结账时,他总希望女人能主动些,或者讲求各付各的。他之所以表现如此差劲儿,是因为他对爱情没信心。在他心里,总认为有一天你说不定会离他而去,变成别人的老婆。这个冤大头他可不想当,因此处处跟你斤斤计较。
吸血虫型
这种男人,功夫可谓深不可测,又多采用避实就虚法。这是有钱不想花或是实在没钱花的男人的独门秘笈。他们用理想、爱好、痛苦等抽象的假动作来感化女人、影响女人,基本上不仅很容易捕获芳心,还能很快让女人主动掏腰包。
这种男人最能让女人失去理智,不但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恐怕是最先进的导弹也不能阻止她神魂颠倒、飞蛾扑火。想占这种男人的便宜,那你是生错了时代!
方程式10:暧昧很近爱情很远(1)
暧昧很近爱情很远
汉语辞典中对“暧昧”的解释为:(关系)不明朗。
如今,“暧昧”犹如一股股潜流暗香浮动。它类似一种情调,又是一种*。分寸把握得当,它是男女关系感情的“滋养剂”,否则就是“扰乱素”了。感情经济学——如果梁山伯懂点博弈论情感方程式10暧昧很近爱情很远事实上我们都没有改变什么,也许我们的夜空早已缀满了星星。虽然我们渴望流星雨的出现,但同时又深谙:每一次流星的出现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只要保持仰望的欣喜就好。
已婚女人的暧昧妄想
2007年的最后几天,我、魏嘉和安妮三个人都琢磨着,选一个周末一起度过,就像我们从前那样。我们选择了12月28日。
在我们三个人都是单身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日子的每个周末都腻在一起,我们自诩为“单身女子派对”。
后来,先是我出嫁了,嫁了一个大学讲师,这很符合我中庸的个性。紧接着是魏嘉出阁,她“意外”地嫁给了一个小报记者。之所以“意外”是因为在我们眼里,魏嘉最具升值潜力。而娇小的安妮,在我们眼里应该是被人宠被人爱的女人,直到我和魏嘉结婚两年之后,才终于嫁给了一个商人。
再后来,我和安妮分别有了自己的女儿和儿子,魏嘉则一直“丁克”着。
2007年12月28日傍晚,我们在“吴越人家”吃过晚餐之后,来到工体附近一个叫88号的酒吧。
魏嘉把我们带到楼上。这里像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桌椅板凳,破旧而颓废,蜡烛在幽暗中飘荡。如果不是魏嘉说许多演员和歌手迷恋这里,我不会相信这里是北京最时髦的酒吧之一。
虽然经历了结婚、生子,但我们三个从外表上看不出太大的变化。魏嘉依然是走到哪里就照亮一片,一会儿做电视一会儿做广告公司,不停地跳来跳去;我是地地道道一个职业女性,连走路都是节奏稳定分寸不乱,而安妮则养尊处优地在家做全职太太。
三个女人一台戏。那天晚上从饭桌上开始,我们就说个不停,到酒吧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把聚会搞成了对丈夫的控诉会。
魏嘉抱怨老公挣钱太少,学车多年却一直没能开上私家车,看着身边的女人一个个噌噌地从小资跨入中产,自己却只能望洋兴叹,连夫妻生活也美而不满。她说如果让她再选择,她要先嫁经济然后再考虑爱情。我对丈夫的埋怨集中在情调上,按说我那个教外国文学的丈夫应该最懂情调,当初是冲着这一点才嫁给他的。可是自从有了女儿之后,他看我一眼的时间就缩短在了001秒之内。安妮看起来很美,日子比我和魏嘉都过得富裕,但老公不但不让她出去工作,平时对她也颐指气使的。
那天魏嘉劝我和安妮,女人即使结婚也应该保有一定的“私生活”,最好有一个蓝颜知己什么的。
当控诉会渐渐演变成魏嘉对我和安妮的开导会的时候,酒吧里开始熙熙攘攘起来。隔着栏杆,我能看到楼下的舞池里,影影绰绰地挤着扭动肢体的人们。
很久没有夜生活了,我突然感觉周围是那么陌生,同时又那么情意绵绵。
这时魏嘉说:“我们干吗在这里抱怨,我们可以改变呀!”顿时,三个人都沉默了。
这时酒吧里一个女歌手开始唱歌,不经意掠过耳际的几个词,感觉似曾相识。安妮说这首歌叫《Quizás,quizás,quizás》,曾被王家卫放在《花样年华》中当插曲。
方程式10:暧昧很近爱情很远(2)
我问安妮“Quizás”是什么意思?只听背后一个男人说:“Quizás是西班牙语,是‘也许’、‘可能’的意思,翻译成英文为Perhaps。请问三位小姐,我们可以坐这里吗?”
说话的男人瘦高,穿着黑色皮夹克,他的身后还站着两个男人。魏嘉习惯性地高挑着娥眉说:“那你得问我身边这两个美女,只要她们同意,我没意见。”男人把头转向我,我说:“你问那位美女吧。”就这样,三个男人在安妮的微笑中坐在了我们身边。
聊天中,知道他们曾经是美术学院的同学,7年没见面了。大学时曾经是“睡在上铺的兄弟”,毕业后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弃画经商,另一个依然孜孜不倦地当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