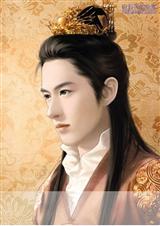狱界花-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有职业道德……”,他笑了一下,平淡的仿佛在讲述别人的生命,“动手吧,我厌倦了很久了……”空洞而迷茫的眼眸,孤寂落寞的神色,几乎让我再一次看见自己卑微而无助的灵魂……
“你爱过吗?”,他看着我在灯光下泛着猩红的眼睛,轻轻的笑着,“不相信爱情的人,往往都是被爱情刻骨的伤害过,而去逃避和背叛的弱着,一如你我……”
我冷冷的眯着眼睛看着他,带着血腥而暴戾的眼神,我喜欢他,喜欢他和我一样放荡不羁的灵魂,却格外憎恨被人窥视内心,那是我自己也不愿去碰触的禁忌,所以,我可以放任我的自私,无情,近乎残忍的冷酷……
‘和你在一起,就如同在地狱和天堂间徘徊,快乐而绝望……’这是三年前,被我亲手杀死的男孩临死前说的话,杀他的原因很简单,他知道我太多的过去,并利用那些妄图控制我的感情……很蠢吧……
他看到我的眸光瞬间变的冷冽,挑起唇角淡然的笑了一下,“我无意窥探你的感情,只是单纯的问起而已……”
“有!”,在他话音未落的时候,我冷冷的回答,看着他讶异的挑眉对我笑着……“我也是,曾经付出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有空听我讲个故事吗?”,他看着我,转头看着黎明的薄光,“在太阳升起之前……”
我沉默的望着他几乎透明的容颜,仿佛在凝视着等待死亡的自己,淡然的笑了一下,“好…”
他的故事很平淡,但是就是这种不经意的平淡中,隐隐透着破灭般的哀伤……
两个出生在普通家庭,受着普通教育的少年,两个两小无猜的朋友,一段禁忌的恋情,一个爱过,恨过,堕落过,一个逃避过,闪躲过,放弃过……却最终成为随风而逝的清烟,曾经的爱恨,迷惘,转化为深入骨血的痛楚,在心底回荡…
“他是我唯一用整个生命去爱的人……”,他这样笑着,轻轻的说,“他恨我的堕落,却更恨自己的懦弱。同样的,我也这样恨着他,恨他的软弱,恨他能笑着看我倒向不同人的怀中,却依然漠视着……恨他在我绝望的时候,拉住我的手,恨他临死前解脱般的笑容……”
“他死了吗?”,我点燃烟,做到沙发上,静静的看着窗前欣长的身影,我以为他口中的男人,就是我的委托人……
“是的……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车祸……”,他扬着笑脸说,“他对我说,‘我和你,是两条永远不会重合的平行线,我去的是天堂……,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他没有说完,不过我知道,他是要我活下来,所以……我活的很好不是吗?我让他在天堂看着,我是怎样坠入地狱……委托你的男人,只是其中一个迷恋我的人而已,我的心,不会属于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爱任何一个人……”
去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是一个寒风萧瑟的雪天,漫天的银白在空中飞舞着,我第一次感觉到雪花的美丽,一如他澄澈明净的眼睛……
墓碑上他的照片,温柔而悲伤,清清淡淡的,仿佛落在碑上的雪……在人群中我看到我的委托人,一个沉默寡言,衣着高贵的中年男人,一直静静的站在墓碑前,手中黄|色的玫瑰在风雪中不停的颤抖……
是的,他死了,我完成了委托,让他死的非常安详,没有任何多余的痛苦,我依稀记得雪白的衬衫上殷红的血迹,仿佛是新婚的胸花,妖艳而迷人……修长的身材微微的斜靠在沙发上,苍白透明的容颜上,挂着仿若等待爱人回家般温柔而忧伤的笑容……
“杀了我吧……”
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也不知为何就这样神差鬼使般举起了手里的枪,他笑着吻了我的唇,温柔而冰冷,似乎有苦涩的味道……
“我第一次,吻了除他以外的男人……”
“我也是……”
枪声过后,淡淡的话语,弥散在悲怆的气氛里……“谢谢你……”
我放下手中大束的风信子,看着洁白的团簇的花朵,渐渐的披上雪的外衣,仿佛和天地溶为一体……
“我很羡慕你……”,我轻轻的开口,却不知自己在羡慕些什么……
风信子,花姿美丽,钟状花絮,最爱白色风信子,意喻游戏人间的精灵……
Chapter 8 琉璃花
被连夜的梦魇惊醒,抬眼看了墙角的座钟,4点,索性半靠着窗吸起烟来。思绪不受控制的想起那张有些苍白的笑脸和临死前那冰冷的唇,上一场大雪的清晨,他浅笑的在我面前倒下,仿佛是另外一个自己…
他的笑落寞的有些凄厉,‘我第一次,吻了除他以外的男人……’
我自嘲的笑了一下,大约在多少年前呢?好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我也用那样落寞的眼睛看者一个人,那时侯的自己,生命里,骨血里,只容的下那一个人。
他的笑,他的宽容,他的温柔,和,他的爱,这些我满心坚信属于自己的,却原来不过是幕布上的绚烂色彩,在帷幕被撕撤开后,我只看到满目残忍的黑……,我染黑了自己的心,染黑了灵魂,可是,依然无法容入那片黑的海,我永远被屏弃在所有人的世界外,摔的好疼,好疼……
所以,我杀了那个灵魂依然纯洁的男子,只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落寞,相同的心,开枪的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他眼中的解脱,和对我的同情……
同情?我冷笑了一下,狠狠的掐灭手中的烟蒂,随手丢在地上,对手指上的灼烫没有丝毫的感觉。缭绕的烟雾中,射入房间的晨光中一闪而过的猩红,那是我才购来的琉璃花…。夜色般的叶片,黑红的曼佗罗,缠绕在一柄重金属风格的欧式长剑上,完全夺去的剑的古朴,妖艳而张狂。
那日雪霁,百无聊赖的我游荡在蔚蓝的晴空下,或许是刚下完雪的缘故,空气清爽的让我这种幽灵般适合生活在夜晚的人,也有了出去的欲望。
它就摆放在家居店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不知是价格高昂无人问津还是太廉价,黑红的花瓣上落满了灰尘,我却在第一眼就看中了它,聪明的店老板揣摩出了我的心思,勤快的把他清理的干干净净摆放在我面前。
它的确很美,鲜少收集装饰品的我,也瞬间被它傲慢夸张的展示方式而吸引,深邃的黑色,隐隐闪着魅惑的红,却又兼有琉璃的清澈,没有犹豫的掏钱买下这个不知道是否真的昂贵如斯的艺术品,在老板谄媚的笑脸与承诺下离去。
起来后煮了杯咖啡权当作早餐,打量着搁置在书桌上的笔记本,这才想起好象已经很久没有去看过网站留言,距离上一场大雪,过了大半个月有余,作为一个杀手,仿佛有些失职。
‘叮……您有十四条新留言’
挑了挑眉,耐心的依次点开,从留言的方式和地址来看,仿佛是同一个人,很急……
我扯了扯唇角,想必又是一个巴不得将敌手除之而后快的人。
“任务?。”我回了消息,刚准备起身到水,‘叮,你有一条新留言’
真的很急呢。我回身坐下,‘帮我干掉一个人,资料怎么给你?’
‘照片,姓名,住址。’
没几分钟,我需要的资料便被详细的传了过来,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少年,丝毫没有笑容的俊美容颜上,更多的是桀骜不逊的神色。
封酃,17岁,AB型血,住址为:东京XXXX
原来是封家的小少爷,我微微一笑。封家是音乐世家,家主封浩然曾经是音乐界声名显赫的青年才俊,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与他的长子封毓有过一面之缘……
‘什么时间可以动手?‘见我没有回话,对方继续问。
我皱了眉,拉回了远去的思绪,‘定金现金30万,事成之后70万汇入户头’
‘100万?’
‘……’
‘好,我要今天晚上就看见他的尸体。’
今天?我笑了一下,查了封酃的资料,发现下个星期就是他十八岁的生日,不用问也知道是涉及到财产纠纷,委托我的人,就是封毓吗?
对于他人的隐私,我从来没有打算探究,也没有这个必要,每一个CASE对这样沾满血腥的我来说,如同随手折断一根树枝那样容易。
我懒洋洋的抬手输入‘成交’
抬头看了看表8:00AM,看样子我有足够的时间订机票拜访故人…
机票很快送到,直飞东京只要一个半小时,所以我在当地时间7:38PM到达成田机场,到了封家在东京的豪宅已经是三个小时后的事情了。
我眯眼看了高大的白色建筑,依然奢华却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生气,出来开门的,是一个瘦小的老人,我报了曾经属于我的名字,只说找封毓,不一会,门开了,我看见哪个与记忆中眉眼相差不是很多的高大男子开门迎了出来,依旧如同记忆中,简单而清爽的白色衬衣。
“凉!真的是你吗?”他激动的一把握住我的手,“你……”
我淡笑了一下,不着痕迹的抽出被他握的有些疼的手,“不请我进去吗?”
“哦,外面很冷吧,快点进来!”他拖着我的手,直直的走向客厅。“山田先生,麻烦准备一杯石榴汁,不要太酸,稍微放一点糖。”
“是的,先生”老人鞠了躬准备离去,却又再次被他叫住,“一会麻烦再取一条毯子,然后你就去休息吧,不要人来打搅。”
“是,先生。”
看着老人离去,我打量起这栋漂亮的房子,很中式化的风格,|乳白色的真皮家具,浅色的窗帘,浅色?我挑了挑眉,他以前喜欢的是深蓝色系,所以他以前的房子里,全部都是深邃的兰色。
仿佛看出了我的习惯动作,他笑了,“小酃喜欢朴素的颜色。”
我没有多说话,坐在沙发上,打量着自从我进来就一直没有抬过头,也没有说过话的少年,柔和的顶灯将他的刘海在脸颊投射了温柔的影,有着说不出来的静谧的美丽。
“忘了给你门介绍,这是我弟弟,封酃”
“酃,他就是我以前给你提过的,东方凉”
少年仿佛没有听到一样,没有开口,半响抬起头来,犀利的黑色眸子冷冷的看了一眼将毯子盖在自己腿上的封毓,这才转脸看向我。
通过他倏然惊愕的表情,我知道是我的相貌让他吃了一惊,但我也无所谓他对我有何看法,端着微微有些酸甜的石榴汁,用同样淡漠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桀骜不逊的少年。
石榴汁是我曾经最爱喝的东西,酸涩中带者淡淡的甜,却不会有果肉沉淀,清清爽爽的味道。
他显然对我的不礼貌非常不满,转过脸看着一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封毓,用纯熟的日语开口问到。
“你请来的律师?还是你的新欢?”
“不是,凉他……”
少年仿佛不想多说什么,冷冷的几乎没有任何感情的开口,“封毓,你少在我面前装亲切。”,抓起方才盖在腿上的毛毯丢在封毓身上,站起身,“等我满了十八岁,你和你那个龌龊的母亲,全部给我滚出这里!”
看着少年大步离开客厅,封毓刚毅而温柔脸上划过一丝悲伤,却瞬间被他很好的掩饰住,弯腰捡起落在地上的毛毯,对我无奈的笑了一下,“很抱歉,酃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我没有多说话,甚至自己对自己的无动于衷都有些惊讶,在十年前,一次在维也纳执行任务时不慎被目标伤的很重,就是在那里修音乐的封毓将倒在雨中的我抱了回来,那时侯的我,多少还有些感激,但现在,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你还是没有变。”我淡漠的开口,但我却已经变了,我不再是那个脆弱的少年,不再单纯,也不会相信或者同情任何一个人。
“你也是。”他微微一笑,“那时侯你突然不告而别,我担心了很久,现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