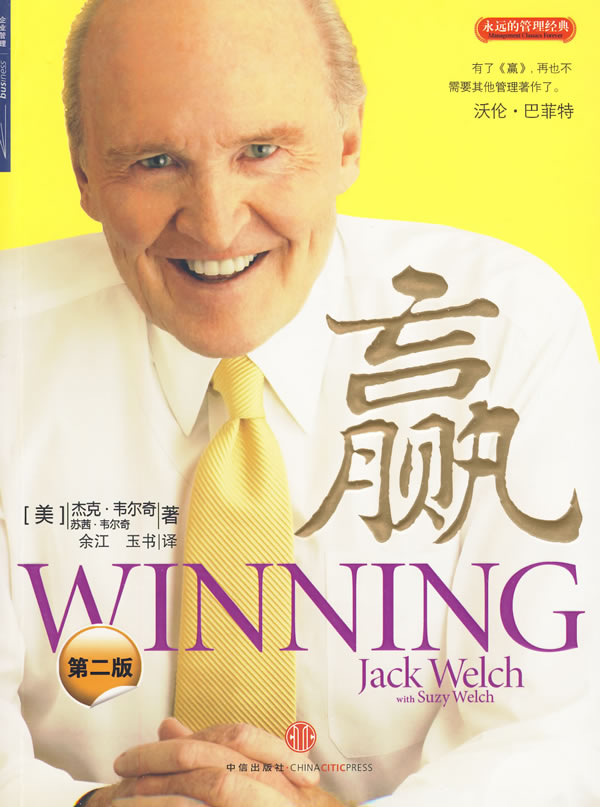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喜欢站在溜冰场门口,脚抖抖,啃啃大头菜。”
这话使我大为诧异,不禁更问道“啃大头菜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可以冒充啃鸭肫肝。”
谈了一会,他帮着我把铺盖打开。在对着门的地方有一个用土坯拦住的范围, 范围内铺有稻草,其上已有了两张铺。我便在旁边将铺盖铺好。不一会儿,大 伙收工回来。有人便和我打招呼。又看到有几个人跑了出去,在院子里商量什 么事。不久,有个人便进来对我说话了,先是寒喧一阵,接着言归正传,说晚 上要和我合被子睡觉。我说这可不行,我不习惯和人合睡一条被子。他马上露 出了凶相和我吵了起来,并且扬起拳头、摆起打架的阵势。我当然也做好应战 的架势。这时,大房间的笼头(34)过来劝架了,他假装听了一番我们的陈述, 然后貌似公正地批评我说
“大家都是苦兄,理应相互帮助嘛。”
我马上回答道“不错,理应相互帮助。但是我今天初来乍到,有这么多人没被子, 我也得看看谁好谁坏,看看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再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不 去找使你们没被盖的人,却欺负我新来的苦兄,是何道理?”
我一副拳大臂粗的样子,又说得对方无话可答。紧张的空气马上变得沉闷起来。 那笼头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原是个专业足球队员,在体委任职,却挂名在大中华 橡胶厂,算是个工人队的队员。他是因为偷废足球而被劳动教养的,能说会道, 一般说来也通情达理,所以在大房间很有威信。晚饭后,他带头唱起了电影流浪 者里的插曲,气氛立刻活跃起来。他们说这是集训队队歌。
************************************************************************
32 上海方言,意为玩耍。 33 上海方言,意为与女人调情。 34 笼中之头,指犯人中比较能镇得住大伙的头头。
*********************************************************************
第二天一早,篱笆外就有人偷偷地来看我,他们俩是我在涛城分场时的朋友, 我曾帮过其中一个人一点小忙。他们也曾在大房间关过,由于他们打了招呼, 我的处境才缓和了。后来我才得知,那天这些人既说不过我,又未打成架,原 打算第二天偷盗我的眼镜以给我个下马威的。不过比较起来那天干部给的下马 威却要更有趣得多。
管理集训队的干部是杨队长,人很和气,讲道理,是白茅岭难得的好干部。在 工地上他并不多管。倒是一个外号胖头鱼的看门场员喜欢无事生非,这种情况 到处可见,真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也。我们那天的劳动是补收花生, 工地较分散。我和孙涌霖搭挡,我拿钉耙在前,他则在后蹲着捡。不一会,打 老远跑来一个干部,走到跟前,盯着我们看。半晌不开口,然后忽然冲着我问道
“你是新来的吗?”
“是的”我答道。
“你为什么偷吃花生?”
“你凭什么说我吃花生?”他于是转而对孙涌霖问
“你吃了没有?”面对着满地的花生壳,孙无言以对。于是这位张队长又朝着 我喝道:
“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只顾自己劳动,未朝后看。”
张队长想了一想,又问:
“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不是?”
“是的”。
“你在大学里学过哲学吗?”
“学过。”
“都学了些什么?”
面对着这种挑衅,我答道:
“学的都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
“那是最基本的。”
见我不再回话,他想了一想又发话道:
“那你知不知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当然知道。”
“那他偷花生你为什么不知道?”
等不及我回答,他显然已经得意起来了,马上又问:
“你是那个大学的?”
“复旦大学。”
“你们复旦大学我去过。”
他显得有些得意洋洋
“你们的党委书记是谁?”。
“那时是杨西光,现在则我不知道。”
“你们的党委书记我认得!是咱们黄浦分局派去的。”
这时他更得意了。怀着压倒了大学生的喜悦,张大队长大踏步地走了。这就 是他给我的下马威。幸而他不直接管大房间,我没吃他多少苦头。然而,象 他这样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我在农场里并没有少见。大凡人们之间有差异就 会有矛盾,知识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愚民和穷人,反之则愚民和穷人仇视知识 分子和有钱人。轻视是错误的,但仇视则更错。一旦象张队长这样的人居然 有权管知识分子了,那知识分子就有了“原罪”非吃苦头不可。
大房间里的人一般为多次逃跑的,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能靠偷窃生活。 用他们的行话来说,扒手叫钳工,溜门撬窃叫搬运工,专事在火车上偷盗叫做 跑二条线,被捕进公安拘留所叫进了庙,如此等等。这些人的品质可想而知。 举一个例来说:有一次我隔壁小组里吃饭时闹了起来,原来那天值班分菜的人 向来分得不公平,总在自己碗里多分。于是有人看准了,在分罢后提出要和他 对调。这原是常有的事,不料前者吃着吃着却忽然大叫起来,原来他在调到手 的碗底竟吃出一条蛔虫。虽然有人帮着骂那分菜的人缺德,但大多数却哈哈大 笑,认为不足为奇。
尽管如此,但在干部眼里却有一种奇怪的看法。他们的逻辑是:这帮人固然是 社会的蛀虫,但不过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已。而所谓的反革命即思想犯则 是要将“社会主义”大厦推倒的人。由此得出我要比这些人坏得多的结论!这 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我在被关的二十一年中,始终处在被关人犯的最底层。利用 刑事犯罪分子来管理、欺凌思想犯是他们的一贯方针,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在他 们脑里,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事小,维持他们的统治权是真。 将思想犯看得比 刑事犯更坏却也并不是某些个别干部想得出来的,他们不过是秉承其上级的意 志鹦鹉学舌而已。正好象我一到农场就最熟悉的一句训辞“再不好好改造就送 你们去做肥料。”一样都是源出于他们的最高领导的。
生活在这帮人之中,特别是自己又被当局看得如此危险,他们还受到鼓励来欺 压你,日子本该是难过的。然而从我到大房间里的第一个回合来看,他们也并 不是完全不讲道理的,只是没有人和他们讲道理而已。他们本该受到感化和教 化,但并没有人感化和教化他们。大多数干部或至少当权的干部本身就不是有 品德的人,何况劳动教养政策规定的所谓教养本来就是空话。撇开我们这些纯 粹受迫害的人不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非缺乏为社会服务能力的人。如若他 们有工作做,就不至于危害社会。即使关了进来,如若能吃饱也不至于如此恶 劣。特别是那些孤儿,政府不满于基督教会对他们的收养,然而由民政局而公 安局,忽地被剥夺了做人基本的自由,整天繁重的劳动,满耳粗暴的训斥,他 们安得不跑?跑了以后又怎能不犯法?
所以,我与他们相处时,在生活上大度些,在劳动上卖力些,有事和他们说理。 日子就并不太难过去。有人说为什么劳动要卖力?我认为劳动本身就是对我们 的惩罚,并且用的是连坐式的集体惩罚。我们没有能力逃脱这种惩罚,那么你 少干就加重了别人的负担,你的日子当然就难了。当然这决不等于放弃磨洋工 的机会,对于那种讨好性的卖力气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对他们说:
“强迫劳动嘛,不强迫当然就不劳动。”
春节前不久,右派队的陈咏春也关到大房间来了。陈当过户籍警,后来以调干 生的身份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被打为右派。在右派队时他不和我同小 组,为他们组的重点对象。我这才知道我的被关只是我们这些人被迫害的开头。 他们被一个个地批斗,强迫他们相互检举揭发。这时候可谓右派发生了大裂变。 自有一帮小人为虎作伥,吠声齐鸣。队长们以为有我在,会影响他们发动运动 的效果,故先把我关走了。其实他们是太抬举我了,我并不见得有这么大的能 耐。这倒反而挑我在大房间里安安稳稳地过了一阵子。陈咏春来此也不吃苦, 他是个用功的人,反到有时间晚上就着自制的油灯练习写作了。
我既被关了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右派队动员“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然而因 为我平时接触交谈的人并不多,那些伥物也掌握不了我什么言论,所以无非是 些空头批判而已。却说有一个和我比较接近的大学生当时正探亲在沪,他写给 在农场的另一场员的信被干部拆看了,信中有称那张队长为张秃头的语句。他 得知此事,未免担心,假满回农场,正巧在运动高潮。为了逃避被批,他就大 量地检举我的言论。当时他的确逃过了这一关,可是几年以后当我再次被迫害 时,他反而被牵连而付出了代价,这是后话。他自己尝到了苦果,无需我再谴 责。我之所以不提名地写出这事来,是因为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在受到迫害时, 本该团结一致的人们却相互攻讦以求自保。这反映了人性的脆弱,抑或人格的 低下呢?在经历了如此多运动以后,人们对这种事看得实在太多了。实在令人 感慨万千。
集训队的安稳日子过了没多久,春暖时分,忽然一天我又被押回了白云山,单 独关在妇女队队长办公室旁的一间屋里。这房子一平排五间,我关在最东头的 一间,隔壁是管教队长的办公室,再过去是事务长办公室和仓库等。因为我不 听他们的约束,总站在窗口张望,他们先是派了一个人站在门外看着,管不了 我后,又不许人们走我窗前经过,后来不得不用土坯把窗户封了起来。他们将 我秘密地关在那里,似乎象怕人劫狱似的,十分可笑。我这样被关了月余,倒 并不感到单身牢房有什么可怕,只是有一天使我伤心极了。那天,场部的施助 理开门进来,递给我一小包食品,说:
“你爱人来过了,为了有利你的改造,我们考虑不让你们见面。这是她带给你 的东西。”
我默默地收下了东西,心里感到气愤非凡。“有利改造”这是什么屁话!我妻 子在寒、暑假中来农场接济过我多次,不但路途辛苦,有一次在涛城时回去还 因感染而得了肾盂肾炎,成了终生疾病。此次几个月不见我家信,本就着急, 不料还被拒之门外。这些号称改造人思想的恶棍竟然如此。若干年后我才得知, 当她来到山下铺后,虽未能见到我,但我的朋友黄建基和张亚新等还是冒险去 招待所见了她,给她以安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禁闭室闲得无聊,每天用一点方糖屑放在地上逗蚂蚁玩,又过了几天,用土 坯隔开的后半部房间里有了声响,又有人关进来了。等押送的人一走,我赶紧 敲墙打招呼,原来是陈咏春来了。这墙并不隔音,我们得以交谈。后来我们还 发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