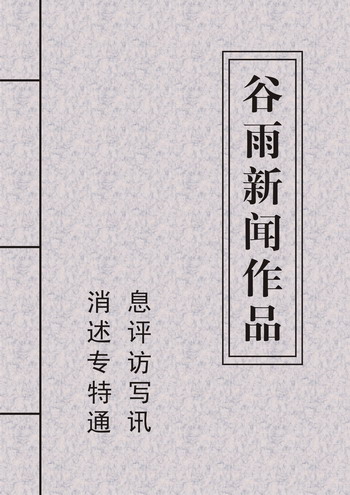于川作品集-上海闲人-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开茶艺馆的与卖壶的之间很自然地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茶艺馆的日常经营中离不开茶壶这种基本的器具,而且茶艺馆一般都兼着经营茶具和茶叶的生意,有客人喝茶喝得动了心,也想在家里摆上一套茶具,给来访的亲友们比划比划自己的茶艺时,一套茶具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于是,那些初好此道的茶客们,大多会在茶艺馆中选购茶具,虽然很多人明知这里同样商品的价格要比陶瓷商店中贵上许多,但这里的茶具比较配套,不用东一家西一家地到处去淘换,而且,在茶艺馆布置得很专业的氛围中选购茶具,容易引起客人的购买欲。所以,茶艺馆经营茶具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
陆伯年和惠文兴的相互依存,可以说是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了好处,惠文兴把一些暂时卖不出去的茶壶寄放在“聚闲居”出售,广开了销路,而陆伯年也乐得个不占资用金,而且还能从中多多少少地赚上一笔,何乐而不为呢。虽然他也像看不起他那位见了有钱人就直不起腰的连襟张道炯一样,看不起势利之极的惠文兴,但看在谁都和钱没有仇的份上,陆伯年到也从来没有怠慢过惠文兴。
“郁先生这两天没来过,好像是回北京看他母亲去了。”
陆伯年故意卖个官子,想探探惠文兴的底。
这家伙不知又在打什么小算盘,如果不是要宰郁有一刀,就是有什么要借重他的地方,不然,他才不肯出血哪!
“老陆,帮帮忙,拜托你今天一定找到郁先生,不然我不白跑一趟了吗?”
惠文兴显然有些着急。
陆伯年在电话这端不出声地冷笑了,哪有追着别人送礼的,除非你是有求于人。
“那有什么,实在不行,你把壶留在我店里,等郁先生回来,我转交给他就是了。”
陆伯年明知对方不肯,故意这么说。
果然惠文兴一百二十个不愿意。
“那怎么行,这可是我对郁先生的一片心意呀!”
“你还怕我吞了?”
陆伯年调侃着。
“不是,不是,我没那个意思。我是说,跟郁先生交往这一年多的时间,从他那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不准备表示表示我的感谢吗。还是我亲自交到他手上比较好!”
“呸!”陆伯年心里暗暗地骂,说得像真的一样,万一遇到个老实人,还真就让他给骗了。
“好好好,我尽量,我尽量!”
陆伯年懒得再和他纠缠。
郁有是他“聚闲居”的常客,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他基本上是每天必到。昨晚他和郁有还在一道喝茶,喝到半夜的时候,郁有说有点饿了,他让小姐拿了些茶点,郁有谢绝了,拉了他和王名棣跑到虹桥去吃宵夜。今晚他十有八九还会来,一个独身客居异乡的男人,身边又没个女人,晚上不泡茶馆上哪儿去呀。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给郁有打了电话。
“郁先生来吗?”
王名棣要出门的时候问丈夫,今天是她上美容院的日子。
陆伯年点点头。
“他不来我这儿,去哪儿啊?”
他很有几分自得。
自从陆伯年的茶艺馆开张到现在,郁有是除了他们夫妇以外,在他店里待得时间最长的一位了,比那些朝秦暮楚的茶艺小姐和服务员专一得多。用郁有自己的话说,他都快成了陆伯年店里的“二掌柜”了。
“也真是,一个人在上海,怪孤单的。”
女人永远喜欢同情别人。
王名棣悲天悯人地摇摇头,走了。
4
和郁有熟识之后,陆伯年曾经对他这位朋友的生活表示过不解,虽说是人到中年,可毕竟是属于衣食无忧,身份显赫的上层阶级,要说重新组建个家庭,那还不易如反掌?再说,这年头,不是都说男人只有到了四十岁才最有魅力吗?即或是暂时还不想结婚,找个女朋友也行啊,上海滩上漂亮的女孩子不要太多哦!可这位郁先生不知是生理有问题,还是心理有问题,一天到晚形只影单的,似乎把他的全部的情感都注入了茶和壶中。除了聊起有关茶和茶具的话题,他很少讲话,有时店里客人多,陆伯年顾不上招待他,他就能独自坐在那里浅斟慢饮地坐上一个晚上,不说一句话。他似乎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太多朋友,偶尔带来一两个,也都是茶道上的同好。
陆伯年曾经问他,既然选择了回国定居,为什么不回北京老家去,而要留在异地他乡。郁有总是很无奈地笑笑,然后反问他,如果有一天他的生意失败了,他还会愿意面对昔日的熟人和朋友吗?
“看看别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事业也好,家庭也好,或者是孩子吧,总是有所寄托,我能干什么呢?闲着,在忙碌的人们眼前晃悠,招人家讨厌?”
郁有自嘲地说。
“还不如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想了解我,别人不会因为我的清闲而不平,我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忙碌而惭愧,挺好!”
陆伯年无法理解,在商场上奋斗了多年的他其实是很想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过上一种清闲舒心的日子,虽然,他不知道以他这样的劳碌命能不能享受得了无所事事的清闲的生活,但那却是他的一种渴望。他羡慕郁有的生活,可以不再为生意和金钱烦恼,可以不再奔波劳碌,甚至可以不再考虑明天的太阳是否按时升起,晨昏对于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人来说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他不行,虽然他早已不会再为温饱而操劳了,但比起罗马花园中那些住着豪宅,开着名车,美女环绕,莺歌燕舞的人们来,他还差得很远。
在私立寄宿学校读书的儿子无数次抗议过,周末他或者是王名棣到学校去接他。
“别的同学的爸妈都是开私家车来接的,你们还叫出租!”
这把他气得冒火,而后又会感到确实有些对不起儿子。如果他能再富有一些,儿子就不必这样委屈了。
他很羡慕郁有。虽然郁有只比他小几岁,但却赶上了好时候,高中毕业就考上了大学,而后有出国留学。他呢,那时还在崇明岛上修理地球。好不容易熬到知青返城,原本以为凭着自己在崇明当过几年中学代课教师,怎么也能分配到学校,虽然吃粉笔灰也不是什么太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比起他最终到街道小厂当学徒可是要强得多了。可是没办法,他一没学历,二没势力,别说中学教师,就是小学也没人要。要不是自己脑子活络,早早下了海,大小经营起一份产业,现在他或许早就下岗靠救济金过日子了。
他在儿子的教育上没少花本钱,让他进了全市最贵的私立中学,光赞助费就交了三万五,还不算每学期近万元的学杂费。他这辈子失去的东西太多了,他不能再亏了儿子。
“没必要!”
郁有对他说。
“咱们小时候不都是苦日子过来的吗?别说现在这些孩子们吃的、穿的、用的,咱们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过呀!结果怎么样,不是都还不错吗?就比如你,大小自己是个老板,手底下也用着十几号人。人的机遇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就不相信,你的同学、朋友中那些上过大学的,就都比你干得好?教育固然重要,可要是一味地只强调教育,忽视了对能力和意志的培养,还是没用。我当首席代表的时候,有一次招聘员工,初试、复试之后,剩下了几个精英,由我最终面试定夺。其中有一个硕士,据前面负责考试的同事讲,很不错的。那天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就让他走人了。”
“什么问题?”
陆伯年极感兴趣。
“我问他,你怎么来的?他说,坐出租车。我说,为什么不乘公交车?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乘。我说,你可以问路啊,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我不好意思。”
陆伯年笑了,郁有也笑了。
“最起码的与人交往的能力都没有,你还能指望他干什么呢?所以,我说,教育固然重要,但是要极端到为教育而教育的话,就失去意义了。”
陆伯年同意郁有的话,但他还是依旧地过分地关注儿子的教育,有什么办法呢?现实理想之间总会有差距,如果那个去郁有办事处应聘的硕士没有硕士学历,恐怕他连最后让郁有来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为了儿子,他也不能过早地享受郁有那种清闲的生活。毕竟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中国人,上海也绝不是美国,中国人的价值观左右着中国人的行为,就像美国人摆脱不了他们的价值观一样。
注释:
②若琛杯——若琛为明清时期一制作茶杯的名家,确切情况不详,清代张心泰《粤游小识》中有“潮郡尤嗜茶……,乃取若琛所制茶杯,高寸余,约三四器,匀斟之……”。从形制上看,应与现代的工夫茶杯极其相似。
③陈鸣远——名远,号鹤峰,又号壶隐。生于明朝末年,是清康熙、雍正年间制壶大家。
④徐汉棠——1933年生于江苏宜兴,现代制壶名家,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
⑤顾景舟——(1915—1997)江苏宜兴人,现代最著名的紫砂大师,是第一批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壶艺家。
第四章 年轻的富婆
麻将让她憔悴——礼送老娘出境——情窦初开——嚼舌头的保姆——下岗的嫂子——丈夫搞上傻女人——“琼民源”和“中关村”——疯了的前夫——千万富婆陈燕欢
1
陈燕欢起床的时候,暮色已经笼了她那白色镂花的窗幔。
昨夜的一场麻将酣战到今天早上,牌友们离开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甚至连妆也没顾上卸就倒头大睡了。
坐到梳妆台前,她看到镜子中自己那张有些浮肿的脸和明显的泛出些青色的眼袋。
以后真的不能再这样打通宵麻将,太伤神,毕竟她已经不是十年前那个可以蹦迪蹦一整夜的小姑娘了。现在一场麻将下来,她得缓好几天才行,腰酸背痛,浑身上下地不舒服,她那位唠叨的老娘多少次劝她别这么糟蹋自己的身子,就算想消遣消遣,也得适度。她也每每在麻将桌上的激战结束后,对着自己疲惫的面容把牌友们咬牙切齿地恨了,却又会在不久之后听闻他们的召唤雀跃得不成。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明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却在毒瘾发作时难以抵御。
离婚三年了,麻将几乎成为了她唯一的寄托。
“除了打牌,我还能干什么?”
她总是在老娘唠叨时这样说。
陈燕欢打麻将绝不是为了赌博。她不缺钱,也绝没有以此赚钱的想法。
她只是感到寂寞,受不了独自囿于这宽大的三层的豪宅中的孤独。她需要有人来和她做伴,需要有人陪她消磨她太多太多的无聊的时光。她喜欢听朋友们天南地北地胡吹乱侃,喜欢听麻将牌在桌子上相互碰撞的声音,甚至喜欢听牌友们输红了眼时骂骂咧咧的争吵,总之,她希望在她清醒的时候,她的周围充满了人和声音,这样才能多少掩盖起一些她的寂寥,让她暂时忘记自己的孤单和小楼的冷清。
她也曾试图把老娘接来同住,但却终于在难以忍受她那张无时无刻不让她想起自己那失败的婚姻的庸俗的老脸后,把她“礼送出境”了。
“如果不是她,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她总是忿忿地对她的朋友们诉说老娘的万恶。然后,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