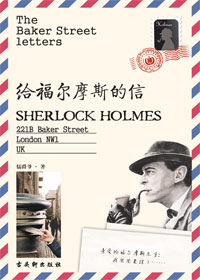红衣女孩 [波兰] 罗玛·丽哥卡-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应该往哪儿跑?我应该找谁帮忙?当我问妈妈去哪儿找医生的时候,妈妈没回答我。她只是举了一下手,很快就落了下来。旅店的门厅里亮着灯,但周围没有一个人。所以我只能跑进林子。我明白我必须得快点,不能再等什么人。“她就快不行了!”我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大声的喘气声使我听不到自己的心跳。我飞快地跑着,不想被松树的黑影遮挡住,但是黑影总是不停地跟着自己。脑子里的尖叫声越来越大,我越来越害怕。
我跑到一个交叉口。一条路往右拐,另一条路是直着往前走。是不是应该拐到另一条路上?我应该走哪条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迷惑了。
我孤独地站在那里,站在漆黑的树林中间,穿着瘦瘦的睡衣,过了一会儿,寒冷和恐惧使我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
但是我不能死,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她就快不行了!”那个声音大声叫喊道。我继续跑,拖鞋不小心滑掉了,睡衣也被灌木丛缠绕着撕破了。我还是不停地跑。
突然我在黑暗中看到远处有些光亮。我朝着那束光亮跑了过去。越来越亮了,我看到那些是房屋周边的街灯。是个村庄。
找医生!这个村庄可能会有医生!
这些屋子都没有亮灯,我敲响了进入村子的第一家家门。里面传出生气的抱怨声,一个女人把门开了一条缝,瞧了我一眼。
“她快死了!”我喘气说着。“我要找一个医生……一个医生……老妈妈!”
那个女人点点头,明白了我的意思,指着另一家门,用德语说着什么。
我跑向另一家大门口,用两只手使劲地敲打着门,“医生!我要找医生!”
楼上的灯亮了,窗户打开了,一个人把头伸出来。
“她快死了。”我累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边哭喊,边含糊地说着。他好像明白了,关上窗户,我听到他下楼的声音。
他打开大门,我冲了进去,用两只手抱住他的腿。“她就要死了!”
“至少得让我穿上衣服。”他用不连贯的波兰语嘟囔着。他正穿着带条纹的睡衣裤。我站在那儿等着他。每一分钟都是那么漫长,最后他终于准备好了,提起他的小箱子。我们沿着一条马路而不是原先那个树林回到了旅店。这条路要近很多。我们很快走到那间屋子,医生站在妈妈的床边,听着她的心跳和脉搏声。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但是她已经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了,医生说。她必须立刻去医院。一辆救护车来了,两名旅店服务生把妈妈抬上了担架,没人对我说话。妈妈的眼睛闭着,她没看我,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小声哭泣,哭得几乎喘不上气了。
在凌晨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6、没有再回头
我醒了,因为我感到很热———特别热。我看到桌子上那块绒毛边的绿桌布,上面放着一个盘子。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自己现在是在哪儿。我的床周围都是空的。突然我记起来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爬下了床,拉开厚厚的窗帘,打开窗户。中午的热浪冲进了屋子,太阳悬挂在高空。已经到中午了吗?我不知道。我对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感觉,况且我也没有手表。
盘子里的食物看起来令人作呕,所以我碰都没碰一下。我喝了口茶,扎上辫子,然后换上衣服,走出前厅,下了楼,走进花园里,在长椅上坐下来。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感觉都不是真的,像是剧院里上演的戏剧。我坐在椅子上,吊着腿晃动。太阳光直射在我身上,我好像听见妈妈的声音:“小心别中暑了,罗玛。”
一个小女孩坐在我旁边,好奇地盯着我。
“你一个人来这儿吗?”她问道。我点点头。
“你妈妈呢?”
我想了想觉得有必要对她撒谎。“她正睡觉呢。”我说。
“你想和我们一起玩吗?我们打算去散步。”这个女孩心真好。她想让我高兴些,也许她感觉到我是那么孤独无助。我又点点头。
我们———包括女孩,她妈妈和我,步行穿过树林。
现在是白天,这个树林很明亮,而且还很凉快。土地很柔软,空气里弥漫着树脂和松针树的味道。我看到前面有许多硕大的、多汁的黑莓,于是跳过去,蹲在地上,我想把它们采回去。
突然我感到周围到处都飞满了嗡嗡的野蜜蜂。我做什么伤害它们的事了吗?它们不断攻击我,围追我。我用衣服抽打它们,但是太多了,到处都是———我的头发、耳朵、嘴巴和脖子,全都是。它们蛰痛了我,我尖叫着,哭喊着,跑出了林子。
我透过薄雾般的空气,听到身后女孩和她妈妈的呼叫声和脚步声。她们想帮我,但是我根本不可能站在原地不动。恐惧和疼痛使我几乎疯狂。最后蜜蜂终于不再追赶我了,它们飞走了。
我站在那儿,颤抖着,胳膊和腿上到处都被蛰得又红又肿。我感到钻心般的疼痛。我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感觉肿肿的,胀胀的。我头发里还有一只蜜蜂,我小心地把它取出来。
女孩和她妈妈追着跑了过来。“我可怜的孩子!”她妈妈惊叫道,“快,快回去吧,让你妈妈把凉毛巾缚在被叮过的地方。”
我点了点头,感觉自己晕晕沉沉的。接着,我跌跌撞撞地回到旅店,穿过走廊,走进大黑屋子。我脱下衣服,按那个女人说的那样,用湿毛巾把自己包起来。这个过程使我感到一股钻心的痛,但是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后来,我感到毒素正窜进我的身体,就像喝了毒药一样。
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床,铺了床单,昏昏沉沉、半梦半醒地睡了过去。现实离我越来越远。
我祖母走到我床边,把她干枯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你会没事的,”她轻声说,“我在这儿陪着你。”
她来使我特别高兴,这样我就不再孤独了。
“你应该喝些水……你会好起来的……”
我喝了水,感到好热,好热。
最后我睡着了。
我睁不开眼睛,因为我的眼睛肿了,嘴也肿胀起来……
周围一切都感觉不到了,只能感觉到身体在慢慢地消失,不再属于我自己,但是思想还属于我。我知道我会好起来的,就像祖母说的那样。我只能坚持撑下去。
我感觉在这旅店漆黑的房间里,一昼夜变得好像永无休止。
门不时地被打开,我听到了脚步声、微弱不清的撞击声。有人轻轻地推开门,进了房间,移走了我还没碰过的食物,又换上了新的。他没说一句话。我只是躺在那里,感到身体内的毒素正在相互敲打,相互搏击着,不断跳动着,挣扎着。我精疲力竭,感觉自己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气力。
我努力试图挺过去。突然一个长着海马形状胡子的人出现在我屋子里。他说他是个司机。“你是罗玛·波济欧姆卡吗?”他问道。
我虚弱地点点头。
“穿上衣服,我带你去你叔叔家。”
他把我的行李拿上车,我摇摇晃晃地跟着他走出去。
没有再回头。
7、感觉到家的温暖
我立刻就喜欢上米特尔曼叔叔了。他是个医生,个子不高、人很随和。他爱讲笑话,但他对待我却很认真,不像其他的大人那样。
“你当时一定非常害怕吧,罗玛,”他说,“一个小女孩,一个人呆在那个大旅店里。在那儿,你一定很不好受。你妈妈昏迷了三天。她得了很严重的脓毒性咽峡炎。当她一刚醒过来,就立刻担心起你,让我把你接过来。你将会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直到她能再下床走路。这样好吗?”
这对我来说太好了。米特尔曼叔叔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还带一个小花园。他娶了我父亲的大姨。伯塔老姨又高又胖,有一个尖尖的鼻子。她嗓门很大,容易激动;而叔叔很安静,不爱多说话,尤其是他们俩呆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他有些怕她。但是她对我很好。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些亲戚,能有这样的亲戚真是太好了。
战争期间,他们也在集中营———因为我看到他们胳膊上也刺着蓝色编号———但是他们没说过这些。他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他们的儿子,詹尼克,死了。在客厅里摆放着他戴着帽子的照片,帽子上别着校徽。每当他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很难过。
老姨经常让我帮她给花园的植物浇水。这个花园很漂亮,里面有鹅莓灌木丛,就像很久以前我祖母的花园一样,还有鲜花,以及小红萝卜和胡萝卜的蔬菜棚。伯塔老姨还给我买了一只小鸭子。我给她起名字叫卡西娅。它是我最最喜欢的宝贝。她像跟屁虫一样,无论我走到哪儿,它都跟着,在后面嘎嘎地叫个不停。我甚至还把她带进我屋子里。
只要有可能,米特尔曼叔叔就会花时间和我在一起玩儿。他给我弹钢琴,弹了很多以前的老歌。听起来并不好听,因为弹得和唱得都走调了。每个人都很喜欢米特尔曼叔叔。白天晚上都会有病人来到他家里。伯塔老姨总是因为这件事而责备他。他们把糕点、鸡蛋、蜂蜜放在楼梯上。有人甚至曾送过一只活鸡。他把挣到的钱放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但是并没有多少钱。到晚上,他数数钱,然后交给伯塔老姨。这时她又责备他没有收病人的费用。
“但是他们也没有多少钱。”他边说边和我眨眼睛。
“如果一直这样,我们很快就经营不下去了。”伯塔老姨回答说。
当我和叔叔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聊起很多事情。他教会我很多东西。我学会了一些病名,懂得了人体结构。他知道很多短小谚语和诗词,而且总是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常常引起我们一阵大笑。我总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但他总是耐心地回答我,只有一件事他没有向我解释清楚,就是关于婴儿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
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家的温暖,体会到一种安全感。而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多年以后常出现的发呆。当我坐在床上,想到医院的妈妈时,常常会发呆。我完全沉浸其中,没有别的感觉,只听到滴滴答答的钟表声,滴答,滴答,滴答。卡西娅的嘎嘎声也不能把我唤醒,只有当伯塔老姨叫我去吃饭的时候,我才极不情愿地被拽回到现实中来。我喜欢像座雕塑一样坐在那儿。
我没有和任何人谈到过这些,甚至也没和米特尔曼叔叔说过这件事。也许我应该这么做———他可能会给我一些帮助。到现在,我明白了这种状态叫做: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