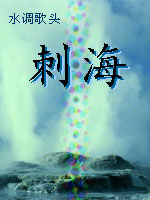锅盖头 作者:安东尼·斯沃夫尔-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操。但我明天还要看看那个录像。你还想干掉自己吗?我要去跑步,要不要一起来?”
我穿上了军靴。我们俩把各自的两夸脱水壶装得满满的,然后将它们绑在背上。从我们这边看到的营房,就像是一辆变大了一倍的拖车,里面装满了我们排里的战友,他们的嘴里都述说着头天看的黄色录像。柯汉问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去跑步,福勒则说我们是装模作样,特洛伊用有关农场牲口和他们母亲的各种各样充满想象力的脏话来辱骂他们。然后,我们便走进了酷热难熬的夜色之中。我们走出营房,营房外数百个挂式空调运作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一辆巨型
摩托车在我们的起跑线上空转待发。这是一辆看不到的、没有驾驶员的摩托车,只有前进的动力和燃料。
我们沿着基地的环形防线跑步。在沙漠里的基地被封锁起来,这听起来还真是可笑。每隔几百码就有坐在悍马越野车里的海军陆战队宪兵队进行警戒。我在想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究竟在找些什么。如果我们大叫一下,他们很可能会朝我们开枪。
特洛伊说:“我真不明白你刚刚都在干些什么,如果是因为克莉斯汀娜,那就大可不必。振作起来,她可不会为了你而去自杀。”
“与她无关,全怪这该死的沙漠。”
“沙漠个屁!浑蛋,在菲律宾群岛时,我亲自花钱给你挑了个妓女,让你开戒。别想对不起我!我才不管是什么原因呢,只要别抠那该死的扳机就行了!”
在菲律宾群岛的时候,他确实替我付了我一生中第一个妓女的钱,他认为那代表着我们俩是亲兄弟。到西太平洋前一年,他随部队驻扎在菲律宾群岛,他非常熟悉那些岛屿和酒吧,好像他就生在马尼拉(Manila),而不是密歇根州的格林维尔(Greenville,Michigan)。
但在菲律宾群岛执勤时,他从下士降级为一等兵,因为在他的尿检中发现有大麻成分。就因为吸大麻,他没有被安排到好的单位,而被送进了海军陆战队。所以他特别好战,人也很粗暴,不过这才叫真正的有士气。他喝醉了酒就大哭大叫,常常抱怨老家一个叫利萨(Lisa)的女孩:她从小学起就一直在拒绝他的求爱。
在同时通过侦察与目标捕获排培训班考试之前,我们俩就常常在冲绳岛的基地一起跑步。看过几部黄色电影,吃过一盘两美元的日本炒面,最后我们回到我的宿舍,大声喊出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吵着要免费啤酒。在冲绳喝到免费啤酒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每个星期三的中午,麦格啤酒公司(The Michelob)的半挂车都会开到基地来,以每箱五美元的价格兜售他们的啤酒。整个基地都没有足够的冰柜来冷冻锅盖头们买的所有啤酒。等你喝完一箱五美元的麦格黑啤酒后,毫无缘由地冲别人大吼就再正常不过了。冲别人大吼不仅仅是因为你喝醉了,还因为你的愚蠢、青春和遗忘。你必须忘掉你到海军陆战队来之前是个什么人。也必须忘掉将来你离开海军陆战队后,可能会变成个什么人。因为战争一来,你可能会死,那么你所有的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和预言都将只是谎言。
我们默默地跑着。特洛伊个头比我小,但跑的速度比我快。不过我总是能超过他。他试图用速战速决来使我疲劳;我打算用拉锯战来拖垮他。我们跑着跑着,就这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虽然我们在营房周围跑的是环形路线,但我还是常常会偏离轨道。我绕着所有的一切转圈,直到这一切成为圆圈的一部分,而这个圆圈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我还是没有抛掉自己的心病,这个病仍然占据着我心灵中的一部分。但它已经不能再让我弯下腰,把我的步枪枪口塞进我的嘴里;也许有一天它会再次发作,但现在我已经对付过去了。
特洛伊跑步时总会打响指,这是他的高中田径教练教他的把戏,可以给他自己打气,继续跑下去。我们的军靴拍打在沙地上,发出剧院的幕布落下的声音。我们就是在舞台上奔跑的演员,边跑边说着自己的台词。我们在向“全能的时间”戏剧的伟大导演证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上战场或是证明其他什么的。我们可以跑一整晚,整晚不停地穿过沙地,绕着我们假想的营地跑来跑去。我们听见马车在舞台上绕圈,我们就是这些马车。我们没理由这样来挑战对方,来向对方证明什么。没有什么好证明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挑战的。我们是一体的,几乎用着同一个脑袋。我们就这样跑下去,理论上可以跑到地底下去。我们绕着栅栏转圈,就像野兽绕着不知怎么下嘴的猎物那样转圈。
我的肩膀很痛,肚子也不舒服,而且跑得时间太久,连脚尖儿都跑痛了。但我们还是继续跑着。我的裆部已经擦伤,特洛伊也一样,因为他对我说:“真希望能在裆上擦点凡士林。”我也表示有同样的愿望,但我们仍然没有停下来。太阳升起来了,喇叭里照样传来起床的号声,催促那些埃及人起床作祷告。我们毫不理会,继续跑着。
也许那时我根本就不会抠动扳机。我的厌烦和孤独还没有让我走向绝望。也许特洛伊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救了我。我想到了我的姐姐,此刻她正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我认为自己是个可怜的冒名顶替者,一个念错了台词的演员。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很明显我要的不是糟糕到可以让人去死的处境。我想到了海明威,他那一枪开得多及时。他是那么的绝望,但他真的很有勇气。有人认为自杀是一种懦弱和欺骗的行为,但我认为自杀是一种很有勇气的做法。回顾自己的生命,认定自己不值得再活下去,然后做出这种恐怖的举动。有无数人生活得没有意义,却很少有人结束他们毫无意义的生命。面对着枪口或是一瓶打开瓶盖的安眠药,嘴里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世界需要我这样做,而不是活着,也不是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苟且偷生。”――这才是勇敢的男人和女人该做的事,这就是自杀。但我没有勇气杀死我自己。我还得继续做我所知道的最棒的事,也许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做一名锅盖头士兵。
特洛伊的葬礼:无言的悲伤
虽然海湾战争已经过去很久,但在沙漠上经历的一切,仍如海市蜃楼般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特洛伊也许救了我的命,但之后他却丢掉了自己的性命――退伍后作为平头老百姓的他,在密歇根找了份差事。有天早上他开车去上班,大概是脑袋不大灵光,或许是喝醉了酒,撞上了一堆黑色的冰块,然后又撞在一棵大树上。所以,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们有六个人去密歇根州的格林维尔参加葬礼。有我、阿迪克斯?拉尔森(Atticus Larson)、罗杰?瓦格纳(Roger Wagner)、桑德?维格(Sandor Vegh)、约翰?邓肯医生(Doc。 John Duncan)和道?威尔蒂(Doug Welty)。当我们到达底特律机场时,他们五个已经喝了三十六个小时的酒,我也喝了三十个小时的酒。(在大家恢复自由以后,我比他们晚回到基地,所以比他们晚六个小时知道特洛伊的死,并且还少喝了五箱啤酒。)因为我是六个当中最清醒的一个,所以由我来租车。密歇根的冬天可真是寒风刺骨。我们是在匆忙中离开高温的沙漠地区的,随身只带了一套制服和一套平常穿的衣服,没人带夹克衫,连阿迪克斯都没有带。他是个地道的威斯康星人,应该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气候。凌晨三点,我们在底特律城里兜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圈,才找到出城的路。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揣有烈酒,所以就互相交换着喝威士忌、杜松子酒、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来御寒,免得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我开着车,这时候开始下起雪来。我们都一言不发,只是偶尔骂上两句:“真他妈的走狗屎运”或是“该死的,真该死”。我们已经被伤得太深,恨不得马上死去,去和我们刚走不久的朋友做伴。我们要结束一切痛苦,很显然酒精是起不到作用的。好朋友已经走了,我们他妈的也就不在乎其他什么了。
叫利萨的那个女孩,也就是特洛伊爱了很多年的那个女孩,给我们指了去殡仪馆的路。我们到的时候,利萨和她父母也在那儿。同时在那儿的还有特洛伊的未婚妻。(当利萨让特洛伊明白她只想和他做朋友后,他开始从沙漠给现在的未婚妻寄信。)特洛伊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说服了他未来的妻子,让她加入海军陆战队。她是在我们作战时加入的。之后她告诉特洛伊他们俩的订婚可能没法实现,因为他已经回到密歇根,而她还和部队一起待在西海岸。但她还说他们俩应该等等再说。她是个好女人,聪明又坚强。作为新兵,我们在海军陆战队里和女兵打交道的时间少之又少。所以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和她相处,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战友和一位死去的朋友的前未婚妻。
尸体查验如我们期待的那样进行了很久。我们还有点迷糊,不过醉意已渐渐退去。有个人,我已经不记得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咱们别喝了,浑蛋们。几小时后还得把特洛伊抬到墓穴里去呢。”
在进行尸体查验时,我们继续咒骂着,说出的脏话和哀乐一样大声。一阵臭骂后我们安静了下来。说完“操他娘的”之后,我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们会给特洛伊穿上海军的蓝制服,还要刮掉他的胡子。他的未婚妻很生气,因为他们把胡子刮得太干净,可我倒觉得无所谓。他们还在他胸前放上些装饰品。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看上去和往常的特洛伊一样,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快乐。
我们在利萨的父母家里睡了几小时。他们对我们很友善,在
客厅里的长沙发椅上为我们准备铺盖,还要在地上给我们打地铺。但我们谢过他们之后,还是一起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
我把我的手枪射手和步枪射手的奖章别在我的海军蓝制服上,和我得到的七条勋表放在一起。而我那枚战斗勋章被放在最醒目的地方,它是红色的,红得像血的颜色。我讨厌穿上蓝色军服的感觉。但我也知道,穿着它的我看上去肯定容光焕发,就像他们那该死的征兵海报上的一名士兵,这听起来肯定像是我在给他们打广告呢。
特洛伊的母亲认为自己是个被基督拯救获得重生的人。我知道她常常不喜欢特洛伊的酗酒和骂人。我也知道特洛伊和我一样,不相信神明。但很明显他的葬礼是由他妈妈来张罗的,而不是他自己。牧师在葬礼上天花乱坠地歌颂着国度的统治者基督,将他吹成是神一般的人物,等等。我开始厌倦这一切。但我想也许特洛伊要的就是这样,即使他和他母亲有如此大的分歧,即使他和母亲为此争辩过,但是如果让他母亲看到他是以一名教徒的身份入土,也许他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这样可以让她母亲和其他人心里会得到一些安慰。不管你在生时如何伤害过或是如何辜负了你所爱的人的期望,在死后也没必要还这样对待他们。
墓穴旁边站着三个从附近的后备役部队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是来鸣枪行礼和为特洛伊的母亲叠军旗的。由于天气很糟糕――地上覆盖了一到两英寸厚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