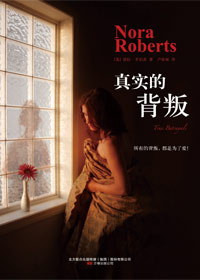背叛 麦冬著2-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说我不是刻意地要自由,我没有那么幼稚,我要的是另一种生活,可以说是哪怕随便的另一种生活,不管做什么,先出了这个牢笼再说,学校叫我象太监一样地激情,叫我感觉苍老和幻灭,这感觉很可怕,我不想一辈子都这样,我不想毁了我的青春,更不想去毁别人的青春,看着那些孩子我就觉得自己在犯罪。
“唉。”佟校叹息着摇了摇头:“你能跟我说实话,我很高兴,不过你该清楚,我死活不会放你走的。”
我看着他的脚尖说:“佟校,我不是来请调的,我是来跟您道别的,我辞职。”
“辞……辞职?”佟校有些口吃,抓起茶杯来就往嘴边送,又呸地一口吐了,水还太烫。
我说我再跟尤校招呼一声,就准备走了,场部那里,随他们去吧,他们在我眼里什么也不是。这些领导,我只对您还有些感情,可惜我不能等着您退休了。
佟校有些颓唐地说:“你真的决定了?”
“决定了,初三的课,我再上两天,也就两天了,好在赵老师搬到农场了,随叫随到,您安排吧,我是去意已决。”
佟校把手在玻璃板上重重一按:“好,走吧,年轻人是要敢闯,我不拦你了,免得将来落你埋怨——我那大小子也刚刚下海了,也照你一样,回来告诉我一声,连个商量的余地都不留,我还臭骂了他一通,呵呵,看来我这脑筋是老啦。那什么!你不能就这么走,今年你的语文考了全县第一,我还准备给你庆功哪。”
“是嘛,第一啊,没想到。”我心里有些感动似的,说不太清的一种情绪。
“庆功你怕是等不急了,得给你饯行!”
我说饯什么行,苏胖子走都没饯行,还是给桑树坪效力呢,我这一个纯粹的叛徒,还饯行?谢谢了佟校。
佟校叹道:“唉,你们两个啊,都是我想下力培养的,将来的学校还指望你们接呢,这下可好,给我落俩话把儿。”
我说还有很多人嘛,今年不是还来新人吗?
“哼,我是寒了心了,什么新人旧人的,这学校就是害人的,谁走谁英明啊,我是老梆子了,要年轻30岁,赶上这时代我也下海摸两把去,哈哈。”
我随和着一笑,坐下来开始聊闲话,佟校也不顾忌了,一嘴脏话,先说了自己当老师、当领导这些年的苦衷,又历数桑树坪这些领导、老师的功过,让他看上眼的,真的没有几个,刚骂到尤俊杰,尤校就到了。佟校打岔道:“正念叨你呢,麦麦不伺候咱这学校了,人家要下海发财去了,怎么着,晚上去你那儿喝喝?”
尤校自是意外,细问几句,又是惋惜,又是赞赏的,说了一片好听的废话。最后约我们晚上去他家里喝饯行酒,我连忙推辞,说不打搅,我知道晚上再搭上章书记,甚至康老师和傅康,几个头目心事各怀的,也未必能说几句人话。
感慨附和着说了些淡话,我抓紧回了办公室,开始收拾东西,我得给赵老师留个好底子,即使人家未必需要这些东西。想想,《雍阳文艺》的方主编那里似乎也该打个招呼,又懒得专程去县城,将来再写信吧。
上午每个班都还有我一节课,还是要上的,不过讲什么都没有兴趣似的,看来这最后一课,是无论如何比不上都德小说里写的那种效果了。我是背叛,人家是坚持,韩麦尔先生能昂扬地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我麦麦老师写什么?
“造反有理”?
“下海无罪”?
我想我还是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传出去也象回事儿。
白露下课了,看我忙活,问:“你还上课去?”
“上,当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钟嘛。”
最后,我让他们背了两堂课的古文,“好好学习”的教导也没留下。当然,我也没提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们上课的话,我相信即使我说,也不会象韩麦尔一样激动得语无伦次:“我的朋友们,我、我……”
但我会在瞬间感觉悲哀。
我会在瞬间感觉悲哀。
所以我不跟他们道别,我没有心情跟一群我还叫不上名字的学生煽情,在我的新生活里,我也不会怀念这些学生甲学生乙吧,而且我知道:他们也不会象我在真情报道里看到的那样,痛哭着恳求我留下。
在我心里只装了一届学生,我会记得高雪清、齐美云、江勇革、陶丽、毛健他们,甚至侯山、郭杰,还有,就是林三柱,这个我培养出的小英雄。我甚至闪过一个念头:应该在走前,为林三柱扫一次墓。
我知道,晚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来看我。昨天在饭馆,陶丽已经知道我要走的消息。
晚上,白露去我宿舍的时候,我正跟几个学生聊得欢呢。
白露说:“你们好热闹啊。”我让她坐,她说不了,依旧站在外面,我只好出来和她说话。
白露说你真是捉摸不定,说走就走。我说人生往往就在一瞬间改变,可那个准备的过程却可能漫长和痛苦。
白露轻笑一下:“你的围脖还要不?我想你不用了吧,到了那里,恐怕没有心情再弄五四形象了。”我笑起来:“看你方便啦——其实我在这里,才真正没有心情玩五四造型呢,五四精神出在大学,在现在的中学里却被一代代地玷污着。”白露笑,说麦麦我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很高兴,你仿佛又把我带回大学时代了,有激情有青春的感觉真好,可惜我找不回来那感觉了,唉。
我正要附和着安慰,白露又接着说:“你要记着,露露师姐会一直关注你的,希望你永远这么意气风发,不要沉沦啊。”
我突然就有些感动了,甚至想拥抱她一下。
我扶着栏杆,望着目力能及的桑树坪,一些暧昧的灯火,慵倦地开放在夜色里,仿佛将眠未眠将醒未醒的梦境。火车的呜咽声响起,让我感觉手里的铁栏都有些细微的震颤了,我知道这里的人们不会有感觉,就象我没有感觉到5分钟之前那列火车一样,他们说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而我今夜又要失眠。
因为我的感觉苏醒了。
白露和我聊了一会儿,先下楼了,陶丽他们还在宿舍里高声喧哗。毛健上了重点高中,让我也有些意外呢,林小平也将和他一起,不过他家里是交了一万块择校费的。刚才林小平还说:现在算知道知识就是财富了。
毛健的父亲要用单位的车送我,毛健说他们几个也一起去:“开开眼,也多跟麦老师呆会儿。”我很欣慰。
看看表,已经9点多了,我招呼他们先回家,陶丽说:“你走得这么急,还没想好送你什么礼物呢。”我说你们大家就是我的礼物,教过你们这届学生,我很高兴,记得我刚来时候和你们说过什么吗?陶丽说我是后来的,我们都笑。
我说:“我说过,你们将是我走上讲台后的第一批学生,我想你们的笑容我会一生难忘,我会很珍惜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希望你们也能珍惜。那样,当我终于退休了,当我老了时,我想起你们来,我会说:那是一群多么可爱的学生啊。”
“可是,你还没有老,就先退休了。”
我说我这不叫退休,叫叛逃。
/
转天上课前,我们已经离开了桑树坪。
陶丽、毛健、肖壮、林小平都来了,刚出桑树坪不久,就看见江勇革正在查车,很凶的样子,我们笑做一团。
让司机逆行着过去打了招呼,江勇哥很懊恼不能跟我们同行。聊了几句,我说得走了,江勇哥立刻跑上公路,挥手让车流止住,直到我们的车子上了顺行线,才挥挥手,一边跟我们做别,一边招呼其他车辆通行。
我笑道:“这臭小子,搞特权啊。”
走了一段儿,林小平问我离开桑树坪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回头望着桑树坪方向,已经看不见农场的踪影了。朝阳已经升起,云很稀,天仿佛是透明的了。
我收回目光说:“没感觉,我出来的时候连头也没回啊,有你们在车上,那里还有什么让我留恋?”
我真的忘记回头看一眼桑树坪了,我的心已在远方。
*****************************************************************************
…01…小说的尾巴
一年过去,月生我们在“天下第一村”经历了一段亢奋岁月后,我们的集团董事长暴毙,然后是疯狂的经济整顿,刑讯逼供、死伤莫论——“大邱庄事件”爆发了,老庄主创造的农民帝国的神话轰然破灭。我和云生黯然神伤,挣扎了几下便象落叶般飘去。我们分头走,去经历各自的喜悦与悲伤、呐喊与彷徨,一路上也都是跌跌撞撞。
在这期间,桑树坪的佟校退了休,小果当了桑树坪学校的校长,据说治校严厉,成绩有限,老师里面有一帮滚刀肉。岳元如愿地去了铸造厂,因为在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屡遭算计,大大不爽,没两年就跑出去自己单干了,有了几个小钱儿后就花了心,犯了一些生活上的错误,现在已经离了婚,米亚男调回老家了。奶品厂最终和加拿大合资,苏家栋成为中方总经理,中间因为学生奶的质量出了些问题,被人诉讼赔偿,弄得他和施展那里都很狼狈,合作也最终终止,而施展也离开教育局去跑保险,后来成了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
再后来,先是苏家栋步岳元后尘,因受排挤愤然辞职,进了雍阳开发区,现在已经是个副总级别的,头发快掉光了,可能太操心吧。这期间桑树坪做了很多努力,终于把学校这个只吃不拉的包袱塞给了雍阳教育局,教育局的条件是:只收学生,不收教职员工。于是,桑树坪那些老师们或者被企业吸收,或者下了岗。我见过小欧在雍阳城里,整天守着一爿小店,一边看书,一边照看她出租录象带的生意,据说比当老师时收入多了一大截,只是郁郁不乐的样子;傅康进了桑树坪场部,一直是办公室主任,算比较得意的;小果进了开发区;范江山在开出租,每天在农场路口蹲客;丁茂林成了倒菜大户,有了自己的一辆柴油车,跑得欢。
表面上比较滋润的是尤校,学校一散,他买断了工龄,和老婆一起被闺女接去城里住,听说喜欢上了养花和遛鸟。
如今的桑树坪农工商总公司,真的成了一个地主庄园,它所有的企业和耕地都承租出去了。附近的东湖,现在也成了一个多功能度假村,老百姓不能随便进了,据说那个曾经秃秃的湖心岛耸立起来的休闲中心是个妓院,传言而已,我没有去过。
展转奔波,几年后,流浪加奋斗的生活终于慢慢有了起色,我觉得自己有些老了似的,不愿意再在外面打食,最后回到雍阳开发区当了个自欺欺人的伪白领,本想塌实地干出点前程来,这工夫施展出事了。施展因为以假保单揽储涉嫌诈骗逃跑了,临走的时候,我送了他几千块钱上路——又是一瞬间的决定。
施展一跑,大家都知道是我送他上路的,我在雍阳总被公安局的同志请去谈话,影响工作,干脆又辞职了。赶着读研的热潮,跟各种迫于形势为评职称和长工资的干部职工一起,去九河师大上那种花钱就给本子的研究生课程班,听了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臭课,有时候真有一种冲动,想跑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