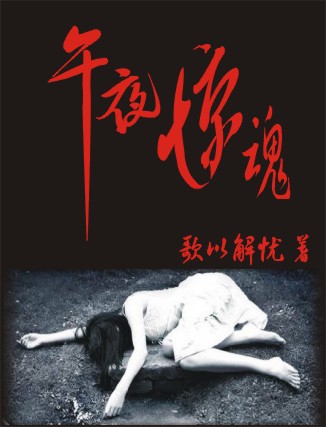巴黎惊魂 〔俄罗斯〕达里娅·东佐娃 著-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像听见有人在赞美他;季马绊上了一把躺椅;并碰掉了一个人的浴巾。我们躺到垫子上;完全不想动;甚至连报纸也懒得看。
和我们邻近的一名男子;用一顶草帽遮着脸;正在睡觉。孩子们咚咚地飞跑过来;把我们包里的浴巾、防晒霜和奥克萨娜的侦探小说踢得乱飞。他们跑到餐厅吃午饭去了。
“我不想去吃饭;”奥克萨娜懒洋洋地说;“真想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个两三天。”
“要知道;你们医院现在还正在进行手术呢!”
“管他甲状腺;”朋友激动起来;“管他激素注射和纷纷落下的肿瘤……唉! 现在是多么幸福啊!”
大约有一个小时;我们都默默地躺着;然后才起身去游泳。温暖的池水温柔地荡漾着两个胴体。奥克萨娜看着躺椅说:“这是谁在那儿坐着呀?”
“让他坐去吧;这里又没人偷东西!”
“不;我还是很感兴趣;究竟是谁呀?”
我眯起眼睛:“这是季马;只不过他买了顶草帽;正在跟我们旁边的人谈话呢。”
奥克萨娜扎了个猛子;我坐在池边;耷拉着两条腿。这里多好啊;简直就是天堂!过了一会儿;我们收拾了东西;慢慢走过去喝咖啡。看不见孩子们的身影;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奥克萨娜的钱包也不知放哪儿去了。一小时后我们回到原地;奥克萨娜的钱包躺在那儿;可是我的钱包又不见了。
“六点以前有人花掉了我的钱;而六点后他又拿走了你的钱。”奥克萨娜猜想。但这个人连动都没动呀!我看了看那个男子;他跟原来一样仰躺着;用帽子遮着脸;一条腿有点怪怪地蜷着。
太阳在移动;它的光线现在照射到了躺椅上。
不过;谁怎样打发时间都不关我的事;只要他不打搅我。我边想边躺到垫子上;进入了梦乡。
一束水珠落到我的脸上;我醒了过来。
原来是疯得正起劲的孩子们拿了个瓶子往我懒洋洋的不愿动弹的身体上洒水。奥克萨娜也在跟着乐。
“往肚子上洒;往肚子上洒。”
我巧妙地乘机一把抓住了金尼斯的手;他尖叫一声;开始用力挣扎。他手中的瓶子滑落下来;划了个弧线;扑通一声掉在了旁边那个人的肚子上。我们都吓呆了;但那个男子还是一动也不动。他还是那样仰面躺着;脸上遮着个草帽;怪怪地蜷着一条腿。
“先生;”我怯生生地喊道“; 先生;请原谅我们。”
奥克萨娜毅然走近那个躺着的人;揭开他的草帽;然后又放下草帽;以外科医生冷静的语气说:“Exitus letales。 “
“什么;什么?”玛莎搞不明白。
可是金尼斯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他拉起玛莎的手飞快跑回房间。在危急时刻金尼斯还是靠得住的。
该去找酒店经理部。门卫正在瑞森普生牌的长桌旁百无聊赖。
“你们浴场有具尸体;”我小声说。阿拉伯人从报纸后慢慢抬起头来。
“我现在就给你查;看他住哪个房间。你说‘; 尸体’先生?”
“不;只是‘尸体’;去掉‘先生’;换句话说;他当然是有名字的;但现在只是一具尸体。”
“只是一具尸体;”阿拉伯人一边翻着一本大册子;一边拉长了声音。突然他的眼睛睁得老大“; 只是一具尸体;也就是指的是死人?”
我高兴地点了点头;他终于搞明白了!门卫拿起话筒;像机关枪似的劈里啪啦说起来;嘴里飞出的单词铺天盖地。还没等他撂下电话;从一个小门里又跑出个阿拉伯人;他用非常熟练的法语问:“你们把尸体藏哪儿去了?”
真糟糕!“我没把尸体藏起来;而只是发现了他!”
第二天我和奥克萨娜被带到了警察局;回答那些没完没了、单调乏味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儿来? 怎么发现尸体的?”阿拉伯人慢腾腾地提问;他们满头大汗;自己也感到腻味。
他们高兴地说;死者名叫龙恩;弗朗西斯科·龙恩;他出生于巴黎。甚至还说出了他的住址。
警察告诉我们;杀手是对着龙恩的脑门开枪的。也就是说;杀手走近了龙恩;并在龙恩的脑门上弄了个窟窿;又用草帽遮住了他的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但要搞清楚杀手是什么时候下的毒手却非常困难;因为浴场很热;尸体当时也没有凉。警察边谈边做记录;最后又把我们送回索维瓦酒店。
玛莎和金尼斯欢笑着在游泳池内戏水。
奥克萨娜也加入了孩子们的行列;我回到房间。
眼前的景象犹如发生了卡尔卡战役;也可以说是如同发生了普罗霍罗夫坦克大战。
床铺被翻得乱七八糟;床单被揉作一团扔到地上;枕头也被划破扔到阳台上。我和玛莎的物品都被扯开;浴室的地上满是一堆堆五颜六色的碎片。不知名的野蛮人还把《时尚》杂志撕掉了几页。
我满腔怒火;转身跑去找门卫。吵闹十五分钟后;酒店经理和服务员领班来到我的房间。经理默默站了几分钟后;若有所思地问我:“您确信这是我们的服务员干的?”
“你们以为我疯了;先搞坏所有的东西;然后又划开枕头? 而且我一整天都呆在警察局;连浴场都没去过。顺便说一句;我们要是把发生谋杀的事宣扬出去;你想那要给你们酒店里的客人带来多大的惊慌啊?”
经理的脸一下子变得比脱脂牛奶还白。
“夫人;就算我求您了;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我们现在就替您收拾房间。然后送您去贸易中心;并……”
这时金尼斯和玛莎闯了进来。
“我们房间……”金尼斯的话刚开了个头又忽然打住了。
“我们的也一样。”玛莎拉长声音说。
服务员跑到奥克萨娜的房间;我跟在后面。那里同样也是一片狼藉。
自然;我们去吃午饭时的心情非常糟糕。
我们的餐桌上布置得惊人的漂亮。一瓶多姆·佩里尼翁酩悦香槟王显眼地放在桌子中央;旁边放着一只盛着色拉的冰纹美人鱼。
在餐厅吃饭的人都兴致勃勃地向这边张望。
酒店经理显然在暗暗拉拢我们。
“好极了!”季马含含糊糊地挤出一句;“你想啊;我走进房间;而那里……”
“状如二战时德军在乌克兰日梅林卡的大溃败;”金尼斯接过话茬。
“你从哪儿知道的?”季马怀疑地眯缝着眼睛。
我们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尽管满桌佳肴;这顿午餐还是吃得很不开心。
稍后我们被接到贸易中心。索维瓦酒店的服务员一个劲地重复;你们买的东西都由酒店来支付。结果我们买了许多用得着和用不着的东西;而金尼斯和玛莎还拿了一个长达三米的充气鳄鱼。
接下来的两周只有金尼斯和玛莎过得无忧无虑;而我和奥克萨娜则焦急地等待着度假的结束。终于;我们的度假结束了。早上我们开始收拾行李。
“妈妈;”玛莎问;“你买了几瓶太阳琥珀防晒霜啊?”
“一瓶呀;怎么?”
“而现在却有两瓶;并且其中一瓶还是满的。”
“那大概是奥克萨娜的。”
腿勤的玛莎立即跑到隔壁的豪华套间去了。回来时她的身后跟着奥克萨娜。
“我的太阳琥珀防晒霜还在呀;几乎快用完了。”
我们看着多出来的一瓶防晒霜。
“大概;我们在浴场时错把别人的拿回来了;”奥克萨娜说“;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玛莎说;“我自己用;不;最好还是送给奥克萨娜吧。金尼斯8 月份要去保加利亚;还用得着。”防晒霜就转到了奥克萨娜的衣兜里。
巴黎迎接我们的是阵阵冷风。逸夫在亲切地向我们招手。
“娜塔莎呢?”
“夫人她去了圣特罗别;她要在那里呆上几周。”
“家里一切还好吧?”
“狗儿们都很健康;仆人们也是。路易已经准备好了晚餐。度假过得怎么样?”
我们使逸夫相信;这段时间过得非常激动人心。
做客虽好;但总不如在家。当我打开皮箱时;我总是重复着这句矫揉造作的真理。
然后我又打开沙滩包。呆在突尼斯的两周;我一次也没有把包里的东西彻底清空过;总是拿出一些东西; 同时又塞进去一些东西……终于我的手触到了包内的塑料衬底;摸到了一个长方形的东西。我把它掏出来;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战利品”:一个大的金烟盒! 在烟盒的顶盖上用钻石镶嵌着某人姓名的头一个字母:P。 K。 ;而另一头则雕刻着“送给我惟一的弗朗西斯科。卡罗琳”。真没想到! 送的不是一瓶太阳琥珀防晒霜;而是一个可能是蒂凡尼或卡地亚品牌的非常贵重的东西。它是怎么跑到我这儿来的? 我又是在哪儿顺手拿到的?我绞尽脑汁;终于搞明白了是咋回事。
被枪杀的男子叫弗朗西斯科·龙恩。显然;我们在匆忙收拾东西时顺手拿了他的烟盒;或者是他在无意中把烟盒掉进了我们的沙滩包里;或者不知具体经过;但烟盒到了这里。不管怎样;烟盒应该还给他的亲人;这可是贵重物品。
第五章
一周后;奥克萨娜、金尼斯和季马飞回莫斯科。送走他们后;我驱车去找附近的电话亭。在第一个遇见的电话亭里;我开始翻查电话簿。弗朗西斯科·龙恩只有一个;该人的住址也与金烟盒主人的相吻合。
大街上静悄悄的;两边全是些深宅大院。
既没有商店;也没有餐馆和发廊。食品由管家负责采购;而需要理发时就叫理发师上门服务。龙恩的房子坐落在最里面;门上安装了对讲系统。我按了一下按钮。
“谁呀?”喇叭响了起来。
“我要把一个包裹交给龙恩夫人。”
不能说我昧着良心说瞎话。要知道烟盒也可以是个小包裹。
院门打开了。沿着两边种满了黄瓜的小路;我晃到了豪宅前。这个龙恩真是怪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门口用黄瓜来点缀的。
门口站着一个姑娘。个子不高;瘦瘦的;宛如一只“长腿狮子狗”。不论她穿着贵重的服装;还是戴着祖传的宝石戒指;都无济于事。她的面容苍白无色;双眼暗淡无神;稀稀拉拉的头发有些油腻腻的;还长着一对大得出奇的耳朵。我总觉得;她这对耳朵好像是从某个胖男人那儿借来的。
“我叫卢伊莎;”丑八怪用她那出人意料的动听而洪亮的声音说“; 请把包裹给我吧。”
“您是弗朗西斯科·龙恩的妻子?”
“不;是他的女儿。”
“我想跟龙恩夫人本人谈谈;是这样;我意外地成了你父亲身故的见证人。”
卢伊莎犹豫了一会;支支吾吾地说:“我妈身体不好;还是请进吧;也许她会下楼的。”
说完姑娘让到一旁;我走进前厅;那里摆满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款式的沙发和圈椅。磨破的皮面;一些地方露出来的氨纶;显然说明了这些家具从来就没换过。搁在特制花架上的花盆到处都是;我凑近仔细一看;里面种的好像是莳萝和香芹。
走过前厅;我们来到显然是为商谈事务而布置的客厅。客厅的墙壁和天花板有些轻微剥蚀;退色的地毯与客厅当中摆放的豪华白色真皮家具一点儿也不协调……
龙恩的女儿说了声“对不起”就出去了;扔下我一个人在客厅里。难道我的屁股玷污了这些美轮美奂的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