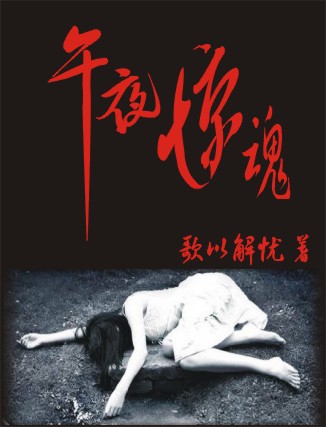巴黎惊魂 〔俄罗斯〕达里娅·东佐娃 著-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说着说着;也不相信自己的话了。姑娘看起来气色非常差;只比死人多口气。抓到那个歹徒才好呢;他把这个不幸的人变得这么难看! 突然我明白了;卢伊莎想说什么。
她双颊发紧;嘴唇无声地翕动着。我把耳朵贴在她的脸旁;竭力想捕获一丝声音。
“季马;季马。”卢伊莎低声说。
“你是想让季马到这儿来吗?”我很吃惊。
卢伊莎双眼满是泪水;她的双唇又动了动:“季马;季马。”
“我现在就去接他来。”
姑娘勉强摇了摇头。
“季马;季马打的。”
我吓得惊慌失措。不;大概我没太搞明白。或者不幸的人儿被打得头脑发昏了。
“你想说是季马把你弄成这副模样的?”
卢伊莎用出乎意料的力量点了点头:“季马;季马。”
“卢伊莎;也许你认错人了? 警察说;歹徒是从背后袭击你的。你不可能看清他。而且季马也没缘由要打你呀!”
泪水沿着姑娘的脸庞流下来。
“季马;季马打的;我看见了季马;他用脚踹的。”
病人变得异常激动起来;开始在床上辗转不安。我叫来护士;她马上给卢伊莎打了一针。过了几分钟;卢伊莎抓着我的手睡着了。她的手指冰凉潮湿;当我抽出手掌时;她的手指怎么也不想松开。
卢伊莎的主治医生是个非常严肃的年轻人;他正坐在主治医师室的电脑旁。
“我想了解一下卢伊莎的身体状况。”
“您是谁?”
“我是她要好的朋友。怎么;这种脑伤会造成头脑不清醒吗?”
“那是自然。颅脑伤是个可怕的东西。
头痛、呕吐、健忘、鼻子出血、听觉丧失———其后遗症远远不止这些。”
“会产生幻觉吗? 可不可能她现在还记得那个袭击者的名字?”
“当然可能啦;但我经常提醒警察;在询问类似受害人时要特别小心。而且他们通常会受到作用很强的药品的影响。现在她觉得什么都记得很清楚;但这类病人常常是在胡说八道。不;如果是我才不会信任这样的证人呢。怎么;你的朋友说出了某个人的名字?警察要我记下她说出的一切。”
“不;只是胡乱嘟哝了几句。什么样的诊断;才能表明卢伊莎可以逃过一劫呢?”
主治医师两手一摊:“我又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只能先治疗然后再看。今天我们有效力非常大的药。幸好;不需要进行头骨环锥术。”
晚上我忧心忡忡、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正赶上家里的人在吃晚饭。热菜上了一道血肠炖苹果。我留意地观察着季马怎样收拾那多汁的灌肠皮。留在巴黎明显对弃儿有好处。
他的脸上一副不慌不忙、悠然自得的模样。
经过美发师修剪过的浓密的浅色头发打着漂亮的波浪卷。他再也没有穿那身洗烂了的足球衫和印度牛仔裤了。在这非常凉爽的秋夜;他穿着浅驼色的古奇牌衬衣;深蓝色列维斯牌牛仔裤;脚登一双巴诺莉妮牌皮鞋。当然不是很贵;但也不便宜。而且季马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巴可·拉班纳牌香水的味道。有意思;他所在的公司给他开多少工资? 他从哪儿弄钱买这些东西?不管是我;还是娜塔莎近来都没给过他一分钱。也许是阿卡奇赞助了这个在这儿住惯了的二流子?季马放下美味的血肠看着我。
“喂;你的实习期多长啊?”我看着他的眼睛问。
“他们说还得半年。到时再看。”
“那你打算这段时间还和我们住在一起?”
“怎么;烦我了?”
“那倒不是;我只是想;万一你想租房子呢。”
“哪会呢;”季马笑了起来;“我对你们已经习惯了;甚至开始喜欢上了小狗;而且我的工资很少;我还想给妈妈带点礼物呢。您不用担心;很快我就会走的;再过一年———绝对。”
说着他津津有味地咕吱咕吱地嚼着烤的夹肉面包片。奥丽娅挪开盘子;慢慢地从桌边站了起来。
“天哪;我的肚子好难受啊。”
阿卡奇双手扶着她;陪她上楼去了。季马打了个哈欠:“我睡觉去了;困了。”
只剩下我、娜塔莎和奥克萨娜。
“看来;”娜塔莎笑了起来;“他还打算在这儿住一年。”
“那我和金尼斯在你这也不知住了多长时间了。”奥克萨娜叹了一口气。
“你们是另外一码事;”娜塔莎斩钉截铁地说“; 而季马纯粹是个什么都不顾忌的无赖。”
很晚了;差不多是半夜了;我特别想吃东西。同饥饿较量了一会儿;我轻手轻脚地向厨房走去。天气已经彻底变糟了;细细的雨丝洒落在屋顶。今天索菲娅开了暖气;走廊里暖和得让人感到惬意。只是从季马房间的门下吹来阵阵冷风。在寂静的夜里传来吱呀吱呀的响声。风刮得更大了;不知是什么东西猛地碰在一起;接着传来玻璃打碎的声音。
窗子……季马开着窗户睡着了;结果玻璃被打碎了。我敲了敲门。
“季马;醒醒。”
没有动静。我敲得更重了;还是没有反应。出什么事啦? 万一他发病了呢? 房门从里面给反锁住了;打不开;弃儿也不吭一声。
我很担心;就穿上牛仔裤、高领毛衣;来到花园。旁边放着一个较大的花园用的梯子。我把它靠到窗子上;从打碎的玻璃中爬过去;看出了什么事。
脚下潮湿的窗台很滑;当我爬上去的时候;烦人的雨滴灌进了我的脖子。冷风也直往毛衣底下钻。我浑身浇得像落汤鸡;冷极了;就一屁股跌到季马的卧室里。床上没人。
在小灯微弱的光线下;房间显得很大;但是在哪里也没能找到季马;无论是在浴室还是厕所里。而房门插上了门闩。也就是说;他吃过晚饭后爬了出去。事先在窗户旁放了一个梯子;当大家都睡着了;他顺着梯子爬下去。
再把梯子移开;去干见不得人的事情去了。
这鬼主意真不错。大家都以为他睡了。
有意思;他经常搞这种把戏吗? 他一到晚上就跑到哪儿去了;也许去会情人了? 我爬上窗子;顺梯子爬了下去;把梯子移回原处。我打算对谁也不说今晚的新发现;最好是继续监视他的行踪;自己搞清楚这一切。
早上九点钟左右;逃跑者若无其事地打着哈欠;喝着咖啡;吃着棍形面包。
“没睡好吧;”我假装同情地说。
季马嘴巴里塞得满满的;点点头。
“这鬼天气。我开着窗睡着了;夜里把玻璃给打碎了。大概风把窗关上了。”
“你也睡得太沉了吧!”
“上班很累;而且天未亮就得起床。”
“八点钟;这难道还早。”
“各有所好;我想一辈子都十一点钟去上班。”
我认真地看着小伙子。应该打听一下;他上班都是在干什么;月收入是多少。
第三十章
要想从季马口中套出请他去实习的那个公司的名称是不可能的。他总是巧妙地岔开话题。有两次我提出把他送到公司;但每次弃儿都在拉斯帕伊林阴道下了车;然后像幽灵一样消失在人群中。我也不能去跟踪他;要是被他发现可就太危险了。
经过几天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买了一份上面登有许多免费广告的报纸;在上面找到一家私人侦探社的地址。
讨人喜欢的年轻黑发女子认真地听我讲着;甜甜地微笑着。然后用事务性的腔调说;她叫马特琳;跟踪侦查季马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我不仅要支付每天的监视费用;而且还得为意外开支买单。
“我们的人坐出租车的费用、各种贿赂都将由您掏腰包。”马特琳把话挑明。
我们谈好暂时跟踪一个星期。于是刚好过了七天我就得到了一份使我不知所措的调查报告。
总之;星期一被调查的对象九点钟在拉斯帕伊林阴道下了车。一开始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十一点时去喝了咖啡吃了面包。
十二点时去了电影院;在那里呆到下午三点。
然后又胃口特好地在一家豪华饭店吃了顿午饭;就起身回家去了。星期二与星期一的没有两样。星期三季马没去电影院而是去了古币展;星期四他跑去欣赏水族馆的小鱼。星期五又去了电影院。
得出的结论为;他根本没去上班;而是在糊弄所有的人;好像他每天在按时“上班”似的。马特琳还顺利地打听到;是一个名叫瓦兹拉夫的法籍波兰人邀请季马到法国来的。
“很滑头的家伙;”马特琳皱着眉头;开始了详细讲述“; 瓦兹拉夫是三十年前作为政治避难者留在法国的。他当时对所有的人讲;他是因为抗议苏联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才被关进监狱的。
“当地侨民非常友好地接纳了瓦兹拉夫;帮他找工作;并给他弄了套廉价的房子。但没过几年就搞清楚了;这个波兰人蹲华沙监狱是因为……盗窃。
“许多家庭再也不欢迎瓦兹拉夫;但他显然不以为然。那时他已经掌控了一个小型的汽车行和一家汽车修理厂。后来两个在他那干活的俄籍机械工在卖偷来的汽车时被抓了。那时瓦兹拉夫就学会了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从那时起;他几次进入警察的视线;但他都证明了自己是无辜的。瓦兹拉夫很可能与黑社会联系紧密;只是无法证明这一点。”
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星期天凌晨一点钟左右我们的客人离开了自己的卧室;顺着花园的梯子爬了下去;打了辆的士走了……
去找瓦兹拉夫。按约定好的暗号瓦兹拉夫亲自打开房门。季马溜了进去。早上五点多钟才回到家。
当然;季马不是最令人喜欢的人。奥克萨娜好不容易叫金尼斯不要再称呼小伙子为蠢货。但弃儿在场的时候;玛莎老是撇着嘴。
但我还是不相信;他和黑社会有牵连。要知道他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家庭: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科学博士;知识分子。季马自己也念完了大学;并通过了候补博士论文答辩;且精通法语。那会是什么把他同盗窃犯瓦兹拉夫黏在一起的呢? 为什么他们只在晚上见面? 为什么他要对我们撒谎;说去那家子虚乌有的公司上班? 他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钱? 是谁凭什么给他掏腰包? 在我离开侦探社回家的路上;这些问题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家里一片忙乱。兽医来给几只狗打疫苗。贾思同先生很喜欢动物;擅长医治各种猫狗疑难杂症;只是它们不会向他表示感谢;当满脸笑容的兽医出现时;它们都胆怯地躲了起来。
所以今天还没等贾思同走进大厅;所有的动物刹那间都跑得无影无踪了。说好话、给奶油饼干都不起作用。玛莎和金尼斯绝望地把糖纸弄得沙沙响;但平时听到这种声音就会跑出来的斑蒂、斯纳普、费多尔·伊万诺维奇都躲了起来。
娜塔莎和奥克萨娜满屋子找来找去。贾思同笑着坐在客厅里喝咖啡。我思虑重重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卧室里微微散发着蜡的气味。显然;今天女仆前来给家具打了蜡。我打开窗户;寒冷、潮湿的空气夹杂着呛人的腐烂树叶的气味扑面而来。突然我背后传来轻轻地呼哧声;毫无防备的我吓得差点掉到窗外。但在我迅速转过身来之后;看见的只是空荡荡的房间。呼哧声是从床底下发出来的。克服了恐惧;我趴在床旁;看见斯纳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