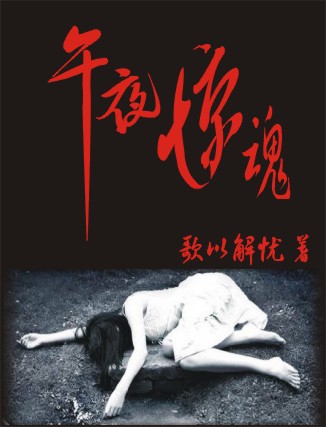巴黎惊魂 〔俄罗斯〕达里娅·东佐娃 著-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惜;一些该拿的东西没随身带来;得开车回去拿。”
“拿什么东西?”我很惊讶。
“还能有什么? 拖鞋、睡衣、肥皂、热水瓶……你没住过院? 还要拿点好茶;我病房的病人总是在喝着热茶。”
我开怀大笑:“我可怜的没见过世面的人。我们去看看;法国人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
首先我们去了病房。奥克萨娜吃惊地看着宽大舒适的病床。床上放着三只枕头;两床松软的被子。过了一会儿;她忍不住摸了一下床单说:“多好的床单哪! 而且考虑得很周全:放了台灯的床头柜、遥控电视、呼叫按钮;还装了窗帘。咦;这是什么门?”
说着她转动把手。原来是个很大的浴室和洗手间。钩子上挂着几条大小一样的毛巾。浴室旁放着一包一次性拖鞋。马桶上套着一条“已消毒”的纸条。
传来一个劝说的声音。一位年轻的护士推进来一辆轮椅;上面坐着穿着病号服、正在哭泣的奥丽娅。
“好了;小宝贝。”阿卡奇忙不迭地说“; 不要难过;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是啊;”护士接过话茬;愉快地说“; 我们这儿始终水平一流;医生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你们最好还是看看菜单;定一份可口的午餐、点心和晚餐。但早餐;可惜来不及了。”
说着温柔的话语;护士走出病房。奥克萨娜好奇地拿过一个大的皮夹子;打开大声念道:“早餐。十点钟供应。请选两道热菜。
1。 果汁———橙汁、苹果汁、葡萄柚汁、菠萝汁2。 天然咖啡3。 可溶咖啡4。 可可5。 牛奶6。 酸奶———天然;加水果7。 燕麦粥8。 熏肉煎蛋9。 烤鸡肉10。 蘑菇煎乳蛋饼11。 鱼制苏福列12。 果酱油饼、糖、盐、乳皮。”
“怎么;他们这里是餐厅?”我的朋友深感吃惊。
“我不想留在这儿;”奥丽娅号啕大哭;“我想回家。”
阿卡奇站在哭泣的妻子旁边干着急。病房的门打开了;门口出现一个大个子女人;活像一头慈眉善目的河马。
“谁在我们这儿哭得这么伤心?”她用低沉的声音亲切地问“; 谁在使自己的孩子伤心难过?”
“我不想留在这儿。”奥丽娅不停地重复道。
“为什么?”“河马”好奇地问。
“首先我不喜欢一个人睡;没有丈夫陪。”
“这没什么;我们给你弄张双人床;丈夫就可以在这儿过夜了。”
“还有费多尔·伊万诺维奇也要和我睡一起。”
“这是只小狗;”阿卡奇连忙解释。
“好啊;我们给它在墙角放个小盆子。白天它可以去花园散步。我希望;胡奇和十一号房间的猫和睦相处。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我是护士长列苇小姐。我的任务就是;这样说吧;至少要让你们一切都感到满意;而不是紧张不安。最大任务就是使你们回家时能带着两个非常可爱的小娃娃。我亲爱的;现在你说说看;是该叫个图书馆馆员来呢? 还是您自己去图书馆?”
“我自己去。”奥丽娅又打起精神。
“不;不;小朋友。”列苇小姐反对道;“千万不要独自行动。想出病房的时候;按这个按钮就行了。”说着她用香肠似的粗手指按了一下床头功能板上的一个白色小按钮。病房的门开了;出现一个年轻的护士。
“这是安列答;”“河马”说;“由她来负责照料你们。领你们去办手续、去图书馆和花园。可惜;她的工作负担很大。我们的安列答不得不一下子照料三位夫人。所以如果她有时晚来几分钟;敬请谅解。现在您请坐到这个‘轻便马车’里;叫上丈夫;我们去看看;我们这儿有些什么。”
奥丽娅忘记了眼泪;坐上轮椅。我和奥克萨娜留在病房里。过了会儿;我的朋友才恢复说话能力:“不;你听这个列苇说了些什么。护士的工作负担太重了;要照顾整整三个女人! 有意思;她怎么喜欢在早上六点钟分发四十支体温计;然后做二十次灌肠;打无数次针! 而且她们真的允许胡奇留在这儿?”
“不知道;我看未必。只不过列苇小姐是个非常出色的心理学家。同意了奥丽娅所有的任性要求。结果呢:皆大欢喜。”
气喘吁吁的阿卡奇跑过来:“不要等我了;你们回家吧。我在这儿陪奥丽娅住几天。”
家里出奇的安静;孩子们跟着玛莎全年级的学生到法国兰斯市旅游去了;要到星期一才能回来。好像想念“兽医”似的;几只狗紧紧地拢成一团睡在客厅里。奥克萨娜上浴室去了;我得去算一笔账。令人可疑的杀猪佬三番五次地托人捎来账单;要求结猪肝的钱。
我在书房出乎意料地碰上季马。小伙子正背冲着房门;在书架上一阵乱翻。
“你在那儿找什么?”我大声问。
没有防备的季马吓得一抖;手中的一本拉伯雷著作掉在地上。
“天哪;难道能这样吓唬人;像个小偷悄悄走近;然后扯着嗓子大喊大叫?”
“对不起。只不过是我穿了双走路很轻的拖鞋。我也不想吓唬你。你在找什么?”
“你看;我在准备一个专题报道;想引证一下‘拉伯雷’。”
说着他拿起一本掉在地上的书。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想起卓尔施关于那双过于诚实的深蓝色眼睛的论断。以防万一;等他走了;我检查了一下保险箱。盒子还在老地方。担心是多余的。
午后卢伊莎给我打来电话:“奥丽娅怎么样?”
“不得不住院。”
“哦;多可惜呀。可以去看她吗? 我明天没空;很高兴星期一去。”
“当然可以;去吧。我们的奥丽娅会很高兴的。”
“给她带点糖果。”
“那太好了。奥丽娅太爱吃甜食了。”
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屋子里显得格外安静。再也没有谁在几个房间跑来跑去;不再耍嘴皮子;没人一个劲地喊“妈妈”;也没谁再去缠着路易要面包……总之;无聊至极。
阿卡奇九点钟左右才回来。
“那里简直就是集中营;”他生气地说;“吃完午饭就是午休。请躺在床上别动。他们来检查;看饭菜是否吃完了。奥丽娅没有啃完油炸包子;可怕的事情就出现了:所有的人都跑了过来;顿时喋喋不休。为什么没有胃口? 胃不舒服吗? 或者饭菜不可口吗? 晚上九点半就熄灯;于是所有的人只好睡觉。
电视也不准看;书也是一样;敬请睡觉;好让肚里的孩子好好发育。今天维伦医生对她说:‘夫人;您现在只不过是个孕育新生命的玻璃试管。首先;我们要保护孩子的生命。
所以您得把自己的欲望全部忘掉;要一心只想着健康可爱的孩子。’”
奥克萨娜忧郁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我回去讲给同事听;他们谁也不会相信的。病人的饭没吃完? 那请随便;厨房这下高兴了;猪狗有的吃了。我们那儿有个名叫任娜的卫生员;就是为了能捞到些残羹剩饭才在那里干的。她有一只大狼狗;一顿要吃多少啊!”
第二十三章
星期一一早我得去上班。我在人类科技馆教俄语。我到现在还纳闷;这些法国人为什么要学俄语。如果是和莫斯科做贸易的商人倒也罢了! 但不是;这个学习班只有五个惟利是图的家庭主妇。老实说;她们给的钱很少。就这点钱我是看不上眼的;我和娜塔莎有的是钱。但找点事做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况且这差事也不累:每周两次;每次半小时。这可不是你们每周二十四小时的坐班制。
比如今天;我就折腾了半小时俄语“代词”。我的太太们全都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我也满怀着教书育人的自豪感驱车回家。
在前厅最显眼的地方摆着两只可怕的带有皮捆带的钢纸板手提箱。我盯着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怪物;感到脊背发凉。
不;前来的还不只是它们。看见我古怪的神色;或者说;看见我那张变形的脸;阿卡奇讨厌地嘿嘿笑着;他的话印证了我的想法:“诺娜总是事前不打招呼就滚来了。”
诺娜! 我原来的婆婆。更准确地说;是我的第一任婆婆。总的说来;我结过四次婚。
请您不要认为;我数次出嫁是因为我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不;只不过许多女人同她们的情人生活数年而不办理结婚证。打我小的时候起;祖母就反复强调:“结婚证不盖戳;就千万别同男人睡到一个被窝里。他一旦得手;就不想同你结婚。”祖母的策略造成了惊人的后果。如果不是我到了巴黎;我还在没完没了地登记结婚;因为就像我的教授说的那样:“不断出嫁的总是那些人。”
不幸在于我根本不知道和他如何相处。
每次结婚后家里都会出现一个巨蜥或者鸵鸟般的怪兽。你需要按时给他喂食;清洗笼子;清洁羽毛;夸奖他;使他打起精神。刚过一个月我就烦了。
这本来也算不上什么;但每次还要扯上他妈。对他来讲是“妈妈”;对我来讲是“婆婆”。如果说几任丈夫总是有点差别:列尼亚体重一百二十公斤;而任尼亚的只有六十公斤;那么几个婆婆表现得就像孪生姊妹一样。
刚过一个星期;她们就对儿媳劈头盖脸一通不公正的指责: 汤也没有;床单也没熨好;墙角还有灰。
“为何我儿子要和一个不尊敬他老妈的女人结婚!”
每次都以同样的结局告终:我收拾了东西;摔门而去。的确;每次婚姻都有赚头。首次婚姻我得到了阿卡奇。总之他也是我首婚丈夫的儿子;但在我和他爸离婚后;他就跟了我。第二次出嫁我还获得了一只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小狗。第三次出嫁造成了对雅诗兰黛阿米斯香水的反感。第四次出嫁得到的礼物是玛莎。
当时十四岁的阿卡奇大发雷霆:“如果你想收留所有的弃儿;收养个小男孩也好啊;而不是这个好流鼻涕的小姑娘!”
在我几任丈夫和婆婆的队列中;诺娜绝对是将军。如果我至今想不起来列尼亚妈妈的名字的话;而诺娜我是不会忘记的。也许是因为她是第一任婆婆;抑或是因为她独特的个性。
“糖浆里的毒蛇”是阿卡奇给他祖母起的绰号。她几乎在一所中学当了三十年法语和文学教师。她总是把学生分为优生和差生;只给那些老老实实听她说些腻人的格言的学生打五分;而给其他的人统统打两分。
自从我和她儿子离婚后;她就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亲人的感觉”只在我和孩子去了巴黎之后才苏醒过来。她就像印度尼西亚的“玛丽亚”台风;每年不期而至。
看着我的脸;阿卡奇继续嘿嘿笑着:“你看;他给我和玛莎带来什么礼物。”说着他举起一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五个皱巴巴、有点腐烂的苹果。
“这些果实;”阿卡奇学着诺娜的口气说;“生长在伟大国家俄罗斯广袤无垠的土地上。
看着这些美好的礼物;知道吗;首先应该尊敬和喜欢我;那个生下你伟大父亲的女人。”
诺娜向来是“礼不惊人死不休”。有一次她一改自己的吝啬;送了我和柯思嘉一只陶瓷花瓶。但第二天花瓶就失踪了。到新年时;婆婆又把它送给我们;但她觉得我不是很感激她;一月二号又拿了回去。这个花瓶后来在三八妇女节时还出现过一次;之后就彻底消失了。还有一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绒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浑身一抖;很不情愿地走过去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