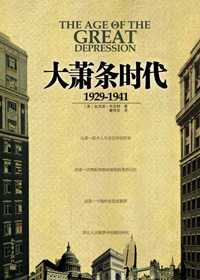29 歌剧院凶杀案-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晓得。”安西兼子摇摇头。
“她的原名好像是水科礼子。这位林先生是她的未婚夫。”
“不,我是被抛弃的男朋友。”阿林严肃地修正。“今天遇见她了。”
安西兼子吃惊地睁大双眼。“遇见她?在哪儿?”
“其实遇见她的是我。”片山插嘴。“在圣士提反教堂里遇见她,白天的时候。”
“哦。那就可以肯定她在维也纳了。”
“不错。”
“好极啦!”安西兼子说,突然避开片山的视线。“比赛冠军的纪念演奏会,不能取消的。即将逼近举行的关头了,假如取消的话,再也没有机会重新举行啦。”
安西兼子的语调有些奇特,宛如自言自语般。
然后突然回过神来似的,催促冈田夫人说:“第二幕已经开始了吧!回厢房好了。”
冈田夫人用不熟练的日语回答:“开幕之前一定会通知人家的,不要紧。”
“可是——我不太懂歌剧,我想事先阅读手册。”
安西兼子说着,率先走开了。网田夫人迟疑一下,对麻理说:“那么,待会见,玛丽。”
然后跟在安西兼子后面去了。
“有点古怪。”片山模仿晴美的语气发言。
“什么事情有古怪?”石津愣了一下,咬了第三片三文治——不,三文治体积太小了,一口就塞进嘴巴去。
“她是因着柳美知子失踪,担心之余才飞来维也纳的,怎么还有心倩来看歌剧?”
“瞧,我早就觉得有古怪了。”晴美得意地捅了一捅片山。
“这没什么好逞威风的!”片山白她一眼。
就在这时,铃声大作。
“啊,真的开幕啦。”麻理说。
观众们鱼贯着回到自己的厢房席。
“全是相同的构造,搞不清哪一间才是了。”片山说。
“你可不能满不在乎地跑进别人的厢房去。”晴美瞪着他。“除非上演香艳镜头,你来通知我吧!”
晴美好管闲事的性格可见一斑。
“福尔摩斯这家伙,跑到哪儿去了?”片山边走边东张西望。
传来“喵”一声,表示“我在这里”。
“啊,好聪明。”麻理笑了。“她好端端地坐在我们的厢房前面等着哪!”
有位老人家蹲在那儿,很有兴致地跟福尔摩斯聊天。
老人穿着制服,他是负责厢房席带路的工作人员。年纪相当大了,失去了左臂。
“他把当天的出演者和故事大纲写成薄薄的手册来卖,作为收入。”麻理解释。
最初来到时,也许随着购买手册多给了小费之故,老人十分亲切有礼,站起来跟麻理说了一些话。
“他称赞说,这是很好的猫。”麻理传话。
“福尔摩斯一定听懂人的意思了。”片山道。
走进厢房时,场内开始暗下来。这个厢房席里面也相当暗。
眼睛不习惯黑暗的话,很容易碰到左手边的大衣挂架。所谓的大衣挂架,并不是放在玄关那种日本式的简陋东西,而是紧紧钉在墙壁上的,体积很大,加上装饰品。
“对不起。”石津碰到晴美的外套,不住道歉。
“那位老伯,一定是在战争中失去一只手臂的。”麻理说。
“战争?不错,战争时,他正好是当兵的年龄。”
“欧洲的建筑物都很古老。留下无数战争的痕迹!”麻理叹息。
“在日本,什么痕迹也没留下。”晴美说。“当然,因为我是战后出生的。”
“我也是。”片山连忙强调。
掌声响起。乐池里,指挥登场了。
——第二幕终于开始了。
2急促的脚步声。
静悄悄的大堂,音乐从演奏会堂轻轻传扬出来,就如远山的回响在荡漾一般。
在歌剧上演时走出大堂的人几乎没有。
那位女性一边喘息,一边加快脚步。
下了楼梯,从大理石的粗大柱子转出来的当地,突然停下来——有人站在那儿。
那人缓缓转过身来,原来是月崎弥生。
“噫,安西老师。”弥生露出有点意外的表情。“这般气喘喘的,往哪里去?”
“弥生……”安西兼子拚命深呼吸,仿佛为了镇压呼吸上的困难。
“安西老师也是为了去三号的厢房见柳美知子吗?”
“弥生。”安西兼子怒目瞪着弥生。“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柳美知子呀!”弥生发出挑畔似的笑声。
“柳美知子——她在三号的厢房?”
“现在不在那儿。”弥生摇摇头。“我去看过了,空的。有人把那个厢房整个包下来了。”
安西兼子用凌厉的眼光盯住弥生,然后好像绷紧的弦崩溃似的,无力地吐一口气,靠在柱子上。
“找个地方坐下来吧!”弥生的语调比较柔和了。
墙上挂着尼古莱的肖像画.他不是俄国皇帝尼古莱,而是维也纳管弦乐团的创始人,作曲家奥图·尼古莱。
肖像画下面有张古老的沙发。弥生和安西兼子并肩坐下。
“你好像很辛苦。”弥生望着闭起眼睛休息的安西兼子。
“这把年纪了,刚刚飞到维也纳,马上观赏歌剧,太勉强自己啦。”
“反正我也活不长啦。”安西兼子浮现疲倦的微笑。
“老师一定长命百岁的。凡是坐上权力宝座的人,都能长寿。”
“权力?”兼子苦笑。“什么权力?只是有几百名弟子叫我‘老师’而已。”
“可是,对于音乐家而言,那就是全部的世界。世人几乎都对那个比赛没有兴趣,然而对我不一样。”
“我知道。”兼子叹一口气。“我想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
“多谢关心。”弥生嘲讽地说。
“弥生。”兼子盯住她。“你为何到维也纳来?”
“因为我觉得心情郁闷啊!”
“只是这些?”
“只是这些……怎么可能。”弥生靠在沙发椅背上,仰望高高的天花板。“这有点像抒情的咏叹调。”
“难道你——”
“当然喽。因为我想亲眼见到柳美知子。我以为胜券在握的冠军,居然付诸流水。
我要看到她不戴面罩的真面目!“
“那么,只要你出席纪念演奏会不就可以了?”
弥生似乎大吃一惊。定睛注视兼子。
“怎么可以?我若留在日本,一点意思也没有。朋友见到我,一定会表示‘好遗憾’。我不能忍受那种失败的滋味。”
“那是你的——”
“不是嫉妒哟。我知道大家怎么想,安西老师的爱徒——竟然拿不到第一名。”
“这是实力的世界,那种流言听过就算了。”
“我知道。不过,谁也不了解我内心的委曲。”弥生顿了一下。“从最初的拜尔练习曲开始向安西老师学习的弟子,只有我一个而已。”
“我从认识你父亲那天开始教你。”
“大家不会这样想。他们只知道,我是特别受安西老师宠爱的一个。从小大家都这么说。”
“事实上,你的表现最特出。”
“连我也这样想——直至这次比赛为止。”
兼子摇摇头。“没法子啊!你也听到的。柳美知子的钢琴弹得比你好太多了。”
“你若不让她演奏就好了。”弥生尖锐地说。“你错了,不应该认可她那种怪异的做法!”
“我没想到她弹得那么好哇!录音带审核的时候听不出什么特别之处……”弥生一直盯着正面的柱子,说:“我晓得了。”
“晓得什么?”
“投票时意见分歧,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她虽然弹得好,可是以那种打扮出现在舞台上,等于亵渎音乐的神圣!”
“你从哪儿听来的?”
“柳美知子和我的票数一半对一半——最后投出决定性一票的人,是你!”
安西兼子的脸色阴暗下来。“吉永先生说的吧!他怎可以把评审内容说出去!”
弥生笑一笑。“吉永先生是我父亲的好朋友。”
“原来如此。”
“老师——假如柳美知子一直不出现的话,怎么办?”
兼子摇摇头。“那也无可奈何呀!只好取消演奏会了。”
“能够那样做吗?比赛花了不少费用啊!”
“还有其他办法可行么?”
“让我取代她成为冠军就行了。”
“弥生——”
“柳美知子的应选资格有问题,等于失格。那么一来,我就是第一名了。我会当着维也纳的观众面前,作出不会令你羞耻的演奏。”
“我不能够这样做。”
“是吗?”弥生狠狠地凝视安西兼子。“这样做又有什么相干呢?老师。”
她的语句十分有礼,然而听出一种凌厉的味道。
——好厉害。片山喃喃自语。弥生在威胁老师啊!
片山在楼梯途中的大柱子后面,以半俯视的姿势聆听月崎弥生和安西兼子的对话。
他不喜欢站着偷听别人谈话。为了不被人发现自己,于是保持“半蹲”的姿势“旁听”。
假如片山是凭自己的推理跑来这里的话,就得承认他的办事能力增长了。很遗憾,在他的脚畔蹲着的,毕竟是“名探”福尔摩斯。
第二幕开始以后,限于对音乐的理解度,终于出现了困意,片山开始昏昏欲睡。就在那时,有人轻轻碰他。
当然是福尔摩斯了。片山睁眼一看,座位上已然不见阿林的踪影。坐在阿林旁边的石津完全进入睡眠状态,肯定即使问他阿林去了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