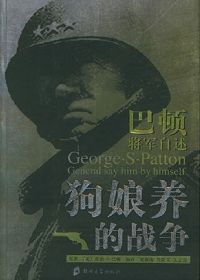将军泪 刘祖保著-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俩姐妹闲聊了一会,银花说:“三妹,一夜没歇息,到床上休息一下,我做好饭叫你和水生吃饭。”
“好吧”,桂花忽然记起什么事,说,“二姐,姐夫呢?”
“呵,他到岳阳进货去了。他呀,一天到晚,只晓得做他的生意,在外面疯跑。三妹就在这里住下,我们姐妹好多年没在一起。小时候,爹最喜欢你,什么事都不让你干,我和大姐在爹心目中却是个男劳动力。”
“二姐,别提这些了,现在我只有一门心思,好好把水生养大成人,等荣标回来。”
“三妹,你太善良了。就到二姐家住下来,姐还能养得你们起。”
“谢谢二姐!”
“自家姐妹,还讲什么谢呢!”
半个月后,银花的丈夫熊林舍回来了。熊林舍是个爱财如命的人,长年在外做生意,但银花也没见到他多少钱。有人说,熊林舍虽爱财如命,但他在城里嫖妓女却十分大方,他的钱大都塞了那个无底洞,这一切银花当然蒙在鼓里。
熊林舍推门进屋,见到桂花在剁猪菜,以为是银花,便说:“银花,我回来了。”
桂花抬起头,欣喜地说:“啊,是姐夫回来了!”
熊林舍看到不是银花,便说:“啊,是桂花,银花呢?”
“她去菜园了,等会就来。姐夫,快放下包袱,坐一会,我去给你泡茶。”
熊林舍把手中的包袱丢在一旁,坐下说:“桂花,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半个月了,给姐夫二姐添麻烦了。”
“哪里,”熊林舍口里这么说,心中却在打着小九九:半个月?莫非他要长期住在我家,我家又不是旅馆?如果真是那样,还要想个法子把她支走。但他还是虚伪地说:“我们这山里条件不好,只怕你住不惯啰!”
“蛮好蛮好,姐夫,生意还好吗?”
“马马虎虎,眼下到处打仗,人心不稳,生意不好做,养家糊口都困难哟!”
桂花从他话语里听出了弦外之音,她睨了熊林舍一眼,感到他脸上似有不悦之色。
不一会,银花回来了,两个儿子和水生也跟在屁股后面。银花没进门,桂花就跑出来接过她手中的菜蓝子说:“二姐,快进去,姐夫回来了。”
银花跨进房门,娇嗔着说:“林舍,你也知道回家呀?”
“没法子嘛,一家几张口要吃要喝,不拼命跑腿,喝西北风?”熊林舍说。
“哎呀,你在外赚钱,我在家可没闲住手脚,四个伢崽我带着,我是没吃闲饭啰!”银花说。
“算了,算了,我又没说你懒,快弄饭吃,我肚子都饿翻了。”
几个孩子一窝蜂地跑到熊林舍面前,找他要这要那。银花说:“你看三妹她儿子水生还没来过我们家,有吃的东西吗?”
熊林舍打开包袱,从里面拿出几块麻糖说:“来,每人一块,拿着出去玩。”
几个孩子接过麻糖,乐滋滋地跑出门,水生站在哪里不动,桂花说:“水生,快叫姨爹!”
水生怯生生地叫道:“姨爹!”
熊林舍把一块麻糖塞给他说:“出去玩吧。”水生接过糖,望了母亲一眼,转身跑到孩子堆中去了。
桂花忙帮着银花择茶做饭,熊林舍闷在那一袋接着一袋地抽烟。
晚上,熊林舍夫妻睡内室,桂花带着水生和银花的四个娃子睡外房。两间房只隔了一板土墙,土墙没到顶,谈话也就听得清楚。几个孩子都呼呼地睡熟了,桂花却怎么也睡不着。内房中传来了二姐和姐夫的说话声。
熊林舍问:“你妹妹要在这里住多久?”
“她也是没法子,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不帮她谁帮她?林舍,他们母子俩怪可怜的。”
“可怜个屁!嫁了个有钱人却不好好生活,又要干出那伤风败俗的事来,怨谁呀?”
“小声点,”银花轻声说,“三妹她难哪,眼下她也是无路可走,那地主婆要害她,我爹又去世了,他不找我们姐妹找谁?”
“我家可不是饭馆,三五天我没话说,要是住久了,我可养他们母子不起。”
“你这人呀,就怎么不讲半点情义,她可是我的亲妹妹呀!”
“亲妹妹又怎样,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你爹在世时都不准她进门,我可不姓李,姓熊。”熊林舍生硬地说。
这一句句话语都被桂花听到了,她眼窝中盈着一汪泪水,哪里还睡得着觉。
第二天,桂花起得很早,穿好衣服后,她轻轻叫醒了水生。她把自己的东西包裹好,她要离开这里。
银花起床了,见桂花包好了衣服,知道昨晚丈夫的话被她听到了,她跑过来说:“三妹,你这是干什么?”
“二姐,你们家日子也不算好,我们母子不打扰你们了,天下大得很,我还是走为好!”
“三妹,你这是何苦呢?你姐夫就那个德性,姐姐可没二心呀?”银花过来拉着她的包裹说。
“二姐,谢谢你,你别拦我!”
“三妹,你真的要走?”
“嗯!”桂花的眼眶内闪亮着几颗泪珠,银花不由得抱着她哭起来。
桂花推开二姐,说:“二姐,我们姐妹这次离开,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要注意身体呀!”
银花说:“三妹,你的命就这么苦”,她跑到房里,从箱子里翻出几块银元塞到桂花的口袋里,“三妹,留着用吧,你打算到哪里去?”
“我已经是无家可归,走到哪里算哪里,听天由命吧!只是苦了这孩子。”桂花泪流满面地呜咽着。
银花将她送了一程又一程,后来她好像记起一件事,于是对桂花说:“三妹,听说弟弟李醒在岳阳城里的一中教书,你去找找他,也许能帮你找一条生路。”
“好,二姐,别送了,姐夫那儿你千万别计较,他也有难处,我知道。”
“三妹,你怎么就只想到别人,唯独不想自己呢?”说完姐妹俩挥泪惜别。
“找到弟弟,给我带个信。”
“嗯,回去吧,二姐。”
桂花母子俩踏着晨露,消失在山里的雾岚之中
第二十章
一场巨大的变革使世道翻了个个儿,相思寨的人们沉浸在一片欢庆解放的喜悦之中。
吴府破败的院墙上,写着“农民翻身得解放”,“打倒地主恶霸”等石灰标语,吴府厅堂也成了村里的政治中心。城里派来的工作队驻扎在昔日的吴府大院内,每天晚上,这院内的灯火总要亮到深夜,一个接一个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吴家大院又一时热闹起来。
狗娃比以前神气多了。他已经不再干那卖发糕的小本生意,成了村里的农民积极分子和依靠对象。他成天跟在工作队长的屁股后面,走家串户访贫问苦,深得工作队同志的信任。狗娃生就一张油嘴滑舌,讲话尖刻带刺,每次村里开大会,他总是主动带头呼喊口号;斗争大会上,他第一个走上台按着批斗对象的头,诉说出他们的一条条剥削农民的罪状。因此工作队认为他苦大仇深,斗争精神强,又有一定能力,后来便让他当上了村干部和土改根子,村里的事情由他说了算。
狗娃成了相思寨红得发紫的人物,他每天出门,总要穿着那件赵队长送给他的四个口袋的灰上衣,一双手反在背后,装模作样地跟人打招呼,令相思寨村人刮目相看。
张狗娃没想到自己如今竟是这等风光。过去他在地主吴文章家做了十多年长工,成天累得腰酸背胀,吃不饱,穿不暖,谁把你狗娃当个人看?后来,吴文章被杀,他不得不干那卖发糕的生意,也是走村串户,一天跑上几十里路,只能糊口度日,连个老婆也讨不起,到如今还是孤单单一个人生活。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如今张狗娃翻了身,有吃有穿,是相思寨村的人上人,他还得要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可是自己已经是三十大几的人了,谁家的闺女还愿意嫁给你做老婆呢?“不!”狗娃转念一想,“我现在是今非昔比,在相思寨我可是一方土地,权力都在我手里,想弄个女人玩玩,想娶个堂客还怕不易于反掌。”他在心里揣摸着,把相思寨有姿有色的女人在脑子里一个个筛选。首先他想到的是相思寨的第一美人李桂花。早在几年前,他就想打她的主意,可没想到那女子一心恋着李荣标,性子也甚是刚烈,因此那次没能将她弄到手,当时他好不气恼!如今桂花远走他乡,几年都无音讯,想她有何用?即使她回到相思寨,现在自己是有身份的人,她毕竟是地主的小老婆,找她玩玩是可以,如果让她做自己的老婆显然不太合适,人家会说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狗娃对村里未嫁的女人一个个过滤后,还是觉得雪梅做他的老婆比较适合。一是雪梅是个快三十岁的老处女,年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而且俩人过去曾有那层意思,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能拢到一块;二是雪梅是佣人出身,也算苦大仇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能将她拉到自己身边当个助手,对于自己今后的工作是有好处的。至于雪梅愿意不愿意嫁给他,他自会有一套征服她的办法。狗娃心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脚步也不由得加快起来。
吴文章出事后,雪梅还是和桂花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吴家家业已败,大太太将她赶出吴府,桂花母子度日艰难,自己留在她家过日子已经多余,不仅不能帮上她多少忙,而且还多了一张口,因此她主动向桂花提出搬出那低矮潮湿的长工屋,到相思寨另一户大户人家帮工去了。当时桂花见雪梅主意已定,也没阻拦。俩人在一起生活几年,以姐妹相称,情意深厚。临走时桂花将自己几件像样的衣服送给了她,雪梅十分感激。后来,雪梅省吃俭用,用帮人做工积攒的钱搭了一个茅草屋,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家。每天她除到人家家里帮工外,早晚在家还可以帮人纺纱赚几个子儿,因此孤身一人的生活还不算拮据。
雪梅脾气也有些古怪,自从早年她和狗娃那一段单相思后,雪梅便没有再爱慕过任何一个人。她已经发誓不再嫁人,一个人平平静静地生活。前些年,给她做媒的人真是踏破门槛,可雪梅毫不动心,一一婉言相拒。十六岁来到相思寨,一眨眼十二年过去了,不大不小也已经是二十八岁的大姑娘了,为什么对那男女合欢婚姻大事不理不睬呢?相思寨的男人女人们都颇费猜疑,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在雪梅看来,一个女人心中只能装下一个男人,即使那男人负心于你,你也不能再去寻找另一个男人。由于这种正统思想的影响,雪梅已经别无选择了。她曾经爱过狗娃,狗娃就成了她心中的偶像,虽然狗娃没能和她共合枕之欢,但她的心已经属于他了。因此她这辈子不希望有任何一个男人进入她的生活空间。
前些年,她还在等待着狗娃的变化,可后来听说狗娃暗地打着桂花姐的主意,之后又干了一些损心败德的事情,雪梅那颗心便为之冷却了。从此雪梅对他没有任何的非份之想。
解放后,狗娃当上了村干部,成了相思寨的大红人。村里土改运动闹得轰轰烈烈,几天就要开一次群众大会,每次都是狗娃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雪梅坐在群众中,望着慷慨激昂的狗娃,心中不禁纳闷起来:这狗娃如今真的变了!坐在她身旁的女人见她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台上,便捅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