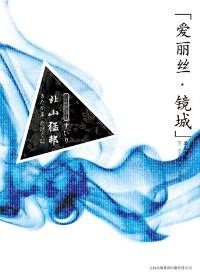029_第三部分:论_关于顾城诗歌的价值与意义-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经一度被认为诗意“朦胧”难懂的《弧线》也是这样。诗人在鸟儿飞翔、少年捡拾分币的动作、葡萄藤延伸的触丝、退缩的海浪的形状中发现了事物之间的看似无关的关联。这些“叙述”可能与所谓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内涵没有多少关系,但是却相当细致、真实地记录了诗人“灵魂前进”的步伐。对于读者有相当的感染与启发的力量。顾城与一般诗人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他作为一个“人”的自己的眼光打量事物,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这种独特的感受。他的诗语总是出人预料,而又自然妥帖。
他说“世界”是“宽大明亮的”,“人们走来走去”,“围绕着自己”,“像一匹匹马/围绕着木桩”(《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他说“小花”“用金黄的微笑/来回报石块的冷遇”,“最后,石块也会发芽”,“在阳光和树影间/露出善良的牙齿”(《小花的信念》);他说“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够了。顾城绝不像闻一多那样的诗人,为艺术而写作;也不同于徐志摩那类诗人,为生活去写真;当然也异于北岛、舒婷的为特定时代、民族命运的呐喊、歌哭。这里,我只想强调他们的区别。顾城属于那种用灵魂也为灵魂浅唱低吟的诗人,是纯粹的性灵的写作。他的诗歌安静、舒缓、抑郁、沉着,又不缺少生气和活力。
而顾城诗歌的这些优异之处,恰被文学史家的书写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
我宁愿相信是无意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关于文学体裁的理解与叙述。
现行文学史大都重小说,轻诗歌。这不仅表现在叙述篇幅的多少上,更主要的在于对不同文学体裁的特殊性的把握上。
自近代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当成“载道”的工具以来,人们就格外看中小说的社会功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态度仍与之相去不远。文学史家极易在小说中抽出它的“思想”来,相对来讲诗歌体裁由于偏重抒情,抒写诗人细微的心灵感悟,不易便当地抽出史家所需要的“思想”、“观念”等材料,尤其是在顾城之类的“纯粹”诗人那里。我想,这就是陈思和的文学史不谈论顾城诗歌的原因吧。绝不是篇幅的问题。冯友兰讲“譬犹图画,小景之中,形神自足。”不要说“形神自足”,“小景”何在?
我们一般的文学史仍然沿袭着一种老的思维模式,在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不同的文学体裁中抽取大体同一的“思想观念”,而忽略了不同体裁文体差异,也即很少重视对文学之所以为艺术的“本体”问题的研究。这是文学史书写的致命伤。大略回顾一下文学史的进程便不难发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和形式演变的过程。一个作家、诗人创造的价值和意义恰恰表现在通过他的探索和努力提供给这种特殊的艺术体裁和艺术形式不断发展,乃至臻于成熟的新的因素和契机。
我想,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只是把不同体裁写作的作者统归一起就算完事,而应该探讨不同作家、诗人在这一体裁上的特殊性。就新时期诗歌创作而言,顾城的特殊性在哪里?他对新诗的贡献,对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演变提供了怎样的新的因素?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对诗人负责,对文学史负责,对文学受众负责。
周扬曾经讲过,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学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从四字一句的《诗经》,到汉代五言诗,到唐代的律诗,到宋词,到元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演变的轨迹;从“作诗如作文”的胡适,到强调“三美”原则的闻一多,到打破外在音律,遵循内在情感变化的戴望舒,到疾呼诗歌散文美的艾青,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代代诗人为新诗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巨大贡献。
毫无疑问,朦胧诗派的诗人们使新诗从五、六十年代的扭曲、空疏的政治口号的状态下复苏过来。这是那一代诗人拯救新诗的共同的劳绩。具体到顾城,他对诗歌体裁的复位与发展的特殊贡献在哪里?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尘埃落定的今天,顾城诗歌的独特魅力不但没有与日减退,反而愈来愈显得与众不同。
我认为,顾城的诗歌之所以魅力无穷,在于他的艺术感受的方式超越了他的时代,直接中外诗歌的优秀传统。他虽然强调自己从小受到普希金、泰戈尔、惠特曼、埃利蒂斯、洛尔迦等西方诗人的影响,但也毫不讳言庄子、屈原、李白、李贺、苏东坡、辛弃疾等传统诗人的艺术熏陶。他说:“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空气里”,“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他们”⑺(P400)。顾城没有中断他与诗歌传统的筋脉联系。而是在传统的滋养下不断成长,并通过自己使得传统得以延续和更新。我觉得顾城对于现代诗歌在当代发展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从庄子、李白那里,从惠特曼、洛尔迦那里拿来了自由的艺术精神和真诚的生命意识,并且把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轻盈、自如的诗歌语言上。
“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草变成了树木//我的心荒凉得很/舌头下有一个水洼”(《分布》),看似自由自在的言说,其中隐含着对于自然、人生秘密的自觉与自得;“在陌生的街上/有许多人跳舞”,“使我无法通过”,“由于长久的等待/我变成了路牌/指向希望的地方/没有一字说明”(《在陌生的街上》)⑻(P20),即使是对于沉痛的人生经验的叙说,顾城也决不显出剑拔弩张的气势,而是表现得平和与包涵。因为诗歌不是给人展示身体的伤疤,而是拨动读者灵魂的琴弦。所以,把诗歌语言变成灵巧的无处不到的纤指,变成静水流深的源源不断的江河,是顾城卓越的艺术才能的体现,也是现代诗歌的传统在顾城身上生长、挣扎,最终开放出来的奇异的花朵。可以说,这就是顾城对于现代诗歌发展所做的显著贡献。
所谓文学史家的观念是想指出,当下具有个性化的文学叙述的阙如。
首先表现在大部分文学史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一人主编,多人或几人分头写作。当然,这其中有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的因素。比如,著者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很难见到像胡适之、郑振铎、司马长风、刘大杰等前辈,倾一己之力,花数年之时,精心创制的文学史专著了。抢时间,赶任务,占山头,树旗子,粗制滥作,自然不能出精品。当然,应该肯定文头提及的几部文学史虽说问题不少,但已是近几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的上品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其改进和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史家”的胸怀与眼光。尤其是史家独特的判断力。阅读不同的文学史著作,常常感到在对同一问题的叙述上有“雷同”之感,很少发现独到的见解。哪怕是有失偏颇的。上述三部文学史,讲到朦胧诗派,都把舒婷放在首位(当然不是说不可以),给予相对较大的篇幅,顾城都置于次要位置。这种因循的“集体”叙述极易造成误解,使普通读者以为客观上存在一种统一的甚或是唯一的文学标准,顾城诗歌的位置是“注定”的。
有没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文学史的叙述,比如从诗艺的创造上评价顾城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及其深刻的影响。不要把诗歌与时代、社会、人民、祖国、未来、理想这类“既定”的观念硬扯一起,诗歌应该是宇宙、自然、阳光、海浪在诗人心灵的折射,是读者从一个新的文本看到的世界和人生模样,像孩子从三棱镜上看太阳的反光。文学史家应该有这样的眼光与责任。不是让公众的舆论影响文学史的写作,恰恰相反,是通过文学史的个性化写作来影响、引导公众。
当代文学史对于顾城诗歌“节略”的评价,不得不顾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顾城之死。在很多人印象里,顾城在道德上是有伤的。这也成为文学史家的一块心病。当然,我们很难把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和作为个人的艺术家分开。问题是文学史并不是刑事判决书,文学史家也不是道德家,我们只需知人论事,探究诗人对于诗歌艺术的劳绩。如其不然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徐渭徐文长、西方哲学史上的叔本华,都要因了他们伤妻仇妇的罪责而遮损其艺术和思想的光芒。
最后,我不得不指出文学史家所要具备的勇气和胆量。秉笔直书不仅是诸如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精神和品质,文学史家同样需要。我认为几部当代文学史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极大影响的诗人采取的近乎一致的叙述态度,表现了作为当代文学叙述者的眼光的短浅、个性的委顿。当然,这对于故去的诗人不会有丝毫损失,损失的只能是广大的读者,也包括叙述者自己。